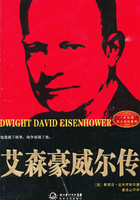从记事起,家,就是一楼和二楼之间的亭子间。六月不知道自己生在这里,还是被母亲抱着来到这里。
七个平方,放了床,衣橱和小桌。除了床边过道,还有一块空地,用来开关房门。
两扇窗,一扇朝北,一扇朝西,窗外一式一样的两堵墙。红砖墙,棕色门窗,斜坡顶上开着老虎窗。这一带都是这样的房子。有着几十年历史。从前的一家现在分住着五六家,当年那些住户没有人知道去了哪里,有的更好,也有的,大概沦落了。
六月在亭子间里学会走路,说话,到了三岁还是经常摔跤,一身跌出来的乌青块。她的头发是黄的,软软地贴在头皮上。做医生的邻居说小孩子可能缺钙了,最好吃点鱼肝油。她看到过那种药丸,透明滚园,吃过有一种很浓的腥气。母亲是不可能有钱买给她吃的,不过医生讲多晒太阳也能达到鱼肝油的效果。四岁多一点,六月已经会照顾自己,每天下午出来晒太阳,安静地坐在小椅子上。六月,踢球去了。趁大人不在家野出去玩的小孩回过头叫她。她只是摇摇头,笑着看他们跑远。她的脸因为太阳晒得太多黑里发红。经过的人看到她大多会说,六月,象个小江北了。他们笑着,也过去了。弄堂里的太阳渐渐斜过西去,直到被楼房的阴影覆盖。她搬起椅子,踏着漆黑的楼梯回家。
除了睡觉,她们从来不关门。没有人会进来,她也可以有活动的地方。她极喜欢这块属于她的地盘,深褚色的条木地板平平整整,散发出松木的香味。她很喜欢这个味道。到弄堂口小店帮母亲买盐或者酱油,偶尔得到一分钱。积到一角可以买一包松子。和地板相似的气味。坐到门槛边用钳子敲开松子坚硬的壳,剥出里面油润柔软的肉。很难得有的快乐时光。
母亲在门上挂了布帘,碎花,和她棉袄的花纹差不多。因为这样可以挡风,也可以挡住她们太狭窄的空间。只是掀起门帘之前有时她会突然停顿一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听说战时有人死在这里过。她很害怕这幢房子,黑沉的墙壁,黑沉的楼梯。梦魇一样黑暗和压抑。
晚上五点,楼梯开始热闹起来。过道里亮着昏黄的光,不时有人上下,从房间到底楼灶间,五户人家共同的厨房。一双双腿从帘子底下经过,楼梯接连不断被踏出空洞的声响。每个房间都有说话声,空气里除了陈年霉味,还混合了油煎带鱼或者葱烤鲫鱼这类小菜好闻的味道。
这个时候母亲是不会下去的。她们坐到门口地板剥毛豆,理小青菜。母亲一向动作利索,而一理菜就马上慢腾腾起来。她们是整个楼里最迟吃晚饭的一家。
常有邻居喜欢趁烧晚饭和母亲说话。从番茄洋山芋多少钱一斤,这个月的自来水费,问到她的由来。这也不能怪她们,对于她和她的母亲,邻居们实在很好奇。这一家两个女人,没有男人。六月自己也很好奇,包括她的名字。黄向华,她户口本上的名字通常没人叫的。邻居都和母亲一样叫她六月。她生在一月份,为什么倒叫了六月。她问过,但和这里的住户一样,只得到母亲含混不明的回答。母亲不爱说话,也不太会说谎。通常笑笑,不愿意多说什么。
邻居其实也知道她们这么迟吃饭是有意要和大家错开,不过这一层意思压到心里,当着面什么也不会说,烧饭的时候照样嘁嘁嗟嗟小声议论,或者不声不响交换一个含义复杂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