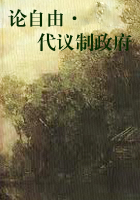去那幢楼看看的念头是突然生出来的。
那么多年了,她只知道那里不是她去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一次。这一天,她拣完小菜,两个邻居都回家了。她换了件羊毛开衫,黑的直统长裤,平跟皮鞋,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出门了。
陶秀英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呼一大口气一样。几年前,周菊舲走那天,她跑着追出来还在眼前,——她看着自己跑得头发披散,就像看着电影里的人。
没人拦她,她走到电梯间,除了一只又大又高的铁皮信箱,梯间里空荡荡的,按了上去的箭头,看着数字剥剥地往下跳着,她简直想转身逃走了,电梯叮的一声已经下来了。
电梯里倒是专门有人开电梯的,是个剃平顶头的男人,问她去几楼。
“顶楼。”陶秀英说。看着电梯门关了,慢慢地爬上去,咣哧咣哧响着,这电梯是有点老了,这楼也有点老了。
升到十层,陶秀英吱吱唔唔地问开电梯的知不知道一个周菊舲的人,住在顶楼,眼巴巴地望着他。
开电梯的说他不知道,漠然地把头转到一边。稍过一会,又说,“你去问问A座,那家在这儿住的时间最长。”
电梯升到顶层停了。陶秀英走出去,心别别地跳着。楼道里打扫得很干净,墙壁雪白,陶秀英找到A座的牌子,按了门铃。门开了,探出一个头发雪白的头颅,脸也是雪白的,透着红,小孩一样顽皮地看着她。里面传出一个不高兴的声音,责备他说,“谁来了啦?也不看看清爽就开门。”
陶秀英急忙说,“对不起,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周菊舲的人?”
“周菊舲?”老头子笑着说,“你找他呀,他搬出去好多年了呀,原来就住对过。”
“那,你晓得他搬到哪里去吗?”陶秀英急得走上前一步,怕这个老头突然消失不见了一样。
“谁啦?”一个女人啪啪地拖着拖鞋,站到老头身旁边,生着雀斑的鼻子大理石一样高傲地挺着。
“寻老周周菊舲的。不过,”老头看着陶秀英说,“你是他什么人啦?见陶秀英不说话,自顾自热情地说,“老周去加拿大了,同他老婆儿子一起去的。他儿子现在都在那边工作了。我算算看,七年还是八年了。”
陶秀英千恩万谢地谢了白头发老头,转身望着对面那扇门。栗色的门紧紧地关着,黄铜把手是暗的,看不见一丝光。这里的人家光是在里面的,是藏起的。想到周菊舲从她那里回来,就是来到这里,从这里走进去,陶秀英微微地笑了一笑。
在公园里陶秀英坐着仔仔细细地回想了好一会,才想到周菊舲那一天原来是同她告别的。他真的是出国了。他来同她告别,却什么都不告诉她,还骗了她。真滑稽。是怕她哭闹吗?怕她不肯吗?就算她不肯又有什么用?难道还拦得住他吗?
还跟我说什么一夜夫妻一百夜恩呢。周菊舲呀周菊舲,你也算是狠心了。
打牌的人收摊吃饭去了。中午的公园很安静,——放在那个时节,她的确是要狠狠地哭闹一番吧。他是聪明的,不给她机会。让她在漫长的时间里死了等他来的心,也让她恨不起来。可是她不是仍然想着他吗?她夜夜不锁门,还是在等着他来看她呀。陶秀英吁了口气,抬头望着眼前高耸的雪松。她现在已经知道他的下落了,加拿大。她想着,一步一踱地回家。经过垃圾桶,看见上面露着鲜红的一角,她拎住那一点点红往外一拽,拽出件红绒线衫。
“又是一件绒线衫。”陶秀英抖开衣服看了看,“还有八成新呢,就不要了?”
陶秀英把绒线衫一卷,塞进拎袋里。回到家里泡了肥皂水,搓洗了几遍,又过了好几遍水,直过到水里干干净净,一丝泡沫也没有了,用网袋装了,晾到天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