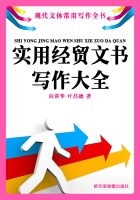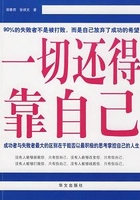一天上午,她休假,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剥豆,周菊舲来了,她咦了一声,问他,“今天怎么这时来了?”只当他老婆又去香港了。倒了开水,抹了身,给他也倒了水,自己避到外间,隔着纱帘,看见他卸去外面的衣裤,擦那腿间的物件。等他好了,她端起水倒掉,回到里间,他已经拉开被子躺下去了,看见她来,掀起被子。她挨过去闭起眼睛,好一会才分开,头并头地躺着说话。周菊舲说他要去外地开会去,去的时间会长一点。陶秀英问他几天,他又不说了。只是伸出胳膊,把她揽在身上。
陶秀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只说,“有空给我打电话。”
“也不一定有空。”
“我说有空,万一有空的时候。”
周菊舲没有再说话,含着笑看着她。
台钟敲了十点,周菊舲穿好衣服,静静地在吃饭的桌子边坐着。因为陶秀英叫他等一等,她昨天烧了一锅银耳莲子羹,拿到煤气灶上热一热,他吃点再走。
太阳光伸进房间,在他的额上落着指头大一块光斑。他的脸依旧年轻光润,他们在一起之后,她总是晚上看见他,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脸被太阳光照着的样子了,很迷恋和他面对面地坐着,看着他用调羹一口口舀着很有滋味地吃着,吃掉了满满一碗。吃完了,像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着,看着她。她的头慢慢低了下去,一直低到他膝盖上,人整个地滑了下去,任他的手在她的头发上一下一下抚着,她有点想流泪,想着他记着她的眼泪,说不定一回来就来看她,又觉得这没有多大可能,而且她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流眼泪,他真在面前了,又流不出来了,由他抚着,也不知道到底抚了多久,几乎要睡着过去了,听到他说,“起来吧,我走了。”
周菊舲穿好衣服,拿着帽子走到门口,又回头朝她看了看。
“好啦。就是去开会,又不是不回来了。”陶秀英嗔怪地看着他说。门开着,万一让人看见总归不好意思。
周菊舲走出门,下了两级台阶,站在那儿戴上帽子,很当心地把帽檐扶了扶正,又回过头来。
估计他每次出去,都是站在这儿戴上帽子。“假正经。”她笑着,摇了摇头。
周菊舲好像知道她在想什么,微微一笑,很深地看了她一眼,下去了。
周菊舲走了好一会,陶秀英仍旧依着门边站着,甜滋滋地回味着周菊舲看她的那一眼。今天他对她很好。他这是舍不得她呢。她愉快地望着楼梯。这楼梯早磨得退光了漆,只有第一级被她房里的光照着,白绒绒的。第二级以下她就看不见了,全部伸进了幽暗里。
楼下的邻居在水槽里刷着家传的白铜痰盂。
“小弟,回来了!还不回来!”对过那家又在喊弄堂里玩弹弓的孩子回来吃饭。炸雷一样的响声。暴躁而不耐烦。
陶秀英陡然感觉到不对,不祥的念头从心里窜出来,拖着拖鞋就下了楼。跑到弄口一看,没有。再往两边一看,还是没有。她顿了顿,一直跑到这条路同别的路交岔的地方,还是不见他。日中的马路干得冒烟一样,到处都是蓝莹莹的。他早走掉了。她想着他今天到底怎么了,人仍冲冲地往前,又走了一段路,蓦地发现再走就要走到那幢楼房那儿了。这房子这样高,离得越近,越觉得高,墙面上每块玻璃都射着刺眼的金光。
五年来,她从来不走到这里。不靠近半步。虽然周菊舲并未说过不许她来这里。这里不是她应该来的地方。陶秀英怔怔地立了片刻,朝上望了一眼,扭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