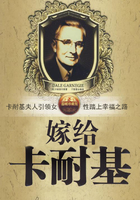即便是纪秋还远在东几列岛的家里那几年,他也没让自己发生说不清楚的事情,他在这方面的保守,说起来还是对女人抱有警惕之心吧。看看那些在家里和外面疲于奔命的男人,为了两边摆平,煞费苦心,简直自讨苦吃嘛。他怕麻烦。他也没有什么想牺牲掉的东西,他想,感情是不好控制的。但是,纪秋和孩子来了以后,那是一个反证,证明了他心里的缺口并不跟他们有关。
跟纪秋的龃龉最初就是为了工作的事。纪秋想让他出面找人帮忙关照一下。在她心里,这很简单,也理所当然。洪武觉得纪秋还是不理解他,为了家里的人去找人说情,在他是一件难以开口的事。但是要他一口回绝纪秋那同样也让他为难,所以,到了纪秋那一边,他就是答应了却迟迟不办,结果还是纪秋自己找了一个同学的朋友,落实到一个给招投标中心当办事员的工作。表面上,她没有说什么,每天很乐于似的从事新的工作了,内心当然是不快的。后来频频在他上班时间打电话追查他的下落,甚至直接闯到报社去,证实他没有说谎,多半也是这件事引出来的。
让自己在下属面前下不了台的,偏偏是自己的女人,洪武渐渐就有了一份无法跟人启齿的羞愤。
纪秋是他的大学同学,他毕了业,家在北方的纪秋也跟着他到了东几列岛。他们当时结婚的房子只有三十几个平方,那时的他们,只要有一张席子大的地方便心满意足了。
纪秋对他的不满是随着出生的孩子一同一天天往大里长的。为房子小,为水开了他没有及时冲,没买对菜,心思放到了别的女人身上,两口子打架。
生气的纪秋不知道多少次在他脸上留下指甲印子,他憎厌她,便是那时开始的吧。尤其是一接近家就听见她因为讨厌孩子缠磨的斥骂声,那种尖利的嗓音让站在门外的洪武不寒而栗。他尤其讨厌的还是打过架的第二天,出了门遮遮掩掩不敢跟人照面,一整天都像一只丧家犬似的。可是,不回纪秋那儿,他又能去哪儿呢?他最终下了决心离开被纪秋讥笑成一辈子不会有出路的东几列岛,不仅是为了让纪秋,也是为了让自己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
为了平息纪秋满脑子的怀疑,洪武不得不学习别的同行的做法,没看完就签署发稿的意见,尽量和喜欢把自己弄得香气扑鼻的女人保持距离,同时尽可能推掉一些应酬,下了班早点回家陪陪纪秋,小心维持着家里和睦的气氛。只是他没有想到,离开了东几列岛的纪秋,没有了他那边的亲人,发起脾气来愈加的肆无忌惮。往往他从家里冲出去,还没有来得及开总编室的门,狂轰滥炸的电话已经让整层楼的人都为之侧目了。
洪武正苦于“真不能这样下去了”的感叹,恰好朋友筹建了一个投资公司,问他想不想去,他当即答应了,正好借以逃避纪秋。有了不在办公室的理由,洪武理直气壮了好多,但是从下属半遮半掩的言谈里揣摩出纪秋又来找他过了,一个人坐着总还是会深深的叹一口气。
细想,纪秋指责的没有错,不想说的是他,不是她。她从老家带来的消息没多久他就听厌了。不仅是和纪秋在一起,对要开的会,要见的人,要请吃的饭,还有没完没了的陪同厌倦极了。和朋友谈天觉得没有意思,看过去喜欢的翻译小说,也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儿子读的是学费昂贵的寄宿制学校,四百多平方就他们两个人,他总嫌大了点。摆设的东西放的多了,更显出人的小来,走来走去只听见自己的回声,尽管灯火通明,四处望下来只觉得家里只灯影壁似的一片黯淡。
可纪秋要宽敞。
这幢有一个圆弧天台的两层小楼建在市内闹中取静的地段,他们刚搬来那会纪秋每周都要请两次客。
有求与他的,还有想和他打打交道的,打听到纪秋的这个嗜好,支使身边的女人来做他家的宾客。虽然他们常常见不到晚回家的他,或者匆匆打个招呼借故离开,纪秋也并不以此为忤,似乎深谙作为纪秋的丈夫,来客基本上都是女人的场合少说话更显得男人秉性温厚。
明明是回家了,恍忽之间却以为又走进了另一个场子。女人们精心打扮过的脸就像漂亮的脸谱,从他面前闪过之后便永久的销声匿迹了,给他留下点花好总难月圆的欠缺感。
时间久了,经常来的总是那么几个人。
为闵予的事和他闹别扭的不自然当然落进过那几个人灵敏的眼睛。有一阵纪秋请客是明显的少了。
须得借助别人,才能得出自己生活幸福的结论,仔细想难免荒谬和可悲。可他辛苦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纪秋和孩子吗?他像一条狗一样守在人家家门口,就为了低声下气的等一个有意回避他的人,不就是为了让纪秋和孩子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吗?他心里也是希望纪秋请客的吧。如果不请客,纪秋就得怏怏不乐的一个人过掉那么长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