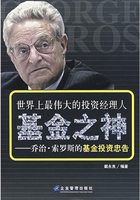事情发生得很快,四天不到,石雨春一家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
“岗厦14号在哪儿,如果你能找到,也让我见识见识。”当时他站在离父亲一米远的地方。说话的是个年轻女孩,脸上带着不屑。她站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口说,“我还以为自己是岗厦人呢,可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父亲似乎矮了些,讨好的表情还没有褪尽,晾在脸的原处。几页皱巴巴的信纸被甩到台面。其中的一页轻轻地弹起,差点落在地上。那是当年岗厦村的回信。前一封是告知要找的人搬走了,去向不明。后面的则是个公函,意思是您的来信收悉,无法联系到相关人,最后一行是欢迎海外及港澳同乡回来投资。
石雨春没等父亲,快速转了身,走出拆迁办大厅。光辉房产中介的门牌刺了他的眼睛。石雨春从眯起的眼缝里看到,正有人从座位上站身,向他微笑,准备出来拦住他说话。他加快了脚步,离开了这一大片金色。他不想让人见到。更关键的是不想他们知道眼下结果。为了争取到赔偿的代理权,三番五次找他,还送了一幅大芬村油画和一份生日蛋糕。又走出几米时,见到新贴出的告示。旁边是几个人说话,还有人拿着机算器算账。红纸上是签约拆迁户的姓名,物业面积和赔偿面积或金额。担心有人跟他打招呼,石雨春低下头,快走了几步。这时,熟悉的音乐和讲解声在身后响起,在您的大力支持下,岗厦将被改造成为中央配套功能区,成为深圳特区又一创举。想到这片城中村很快将变成高楼大厦,与他们一家再无关系,父亲从此没了话题,没了寄托,还有他和弟弟渴望的奇迹,将永远不能出现,石雨春鼻子酸了。他不知围着岗厦街走了多久,才意识到脚已经疼了。
之前他就对父亲所谓的老房子赔偿半信半疑,还说过打击的话,可现在想法不同了。如果不是因为穷,在东北两个儿子都没工作,没出路,父亲不会动这根筋,打这份歪主意。电视里说,深圳要办大运会,岗厦村拆迁,许多居民一夜间成了亿万富翁,连一些海外的华侨也回来,认祖归宗。父亲说过他这辈子都在等这一天。搞到当年材料,就能拿到一大笔钱。石雨春觉得父亲样子鬼鬼祟祟,聪明人一眼便能看出破绽。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石雨春突然觉得自己必须懂事,真正地承担起长子的责任,不能再按着父亲的思路,想事做事了。否则人生就被彻底耽误了。
很快石雨春就听见了不远处的声音。是父亲把放在口袋里用于庆祝的酒,喝了半瓶,没出办事大厅他就已经醉了。是保安把他赶了出来并拖到了大街上。他抚着岗厦的那棵百年老树站起身,踉跄着走到了满是油渍的大排档前,对着吃饭的人高声说,“去过东北吗,天又高又蓝,四季分明,白菜是白菜,猪肉是猪内,不会像这里热得要死,雪也不下,青菜怎么做都不好吃。”说话的时候,汗在他的脸上趟出两条小沟,沾了些灰土。石雨春见了,吓出一身冷汗。他快速闪进人流,准备早一点逃回家中。
平时石雨春宁愿跑到楼顶发呆,也不想回家。所谓的家,在文化大厦后面的岗厦村。除了没有离开的本地人,这条街住满了租房客,包括开出租的攸县人,四川帮,关中汉子、各种手艺人,修鞋,补衣服、买水果的小贩和摩托仔们。还有一些做那种事的女人。她们像是刚醒过来的精灵,闪着发亮的眼睛,活跃在午夜街头。石雨春父子的出租屋便在其中。每月四百,不包水电费、卫生费。在关内,除了清水河一带,这里的房价应该最便宜。石雨春不喜欢回到这里有原因。平时少话的三个男人,挤在同个房里很是尴尬。光了大半个身子,会发现彼此的丑。先是父亲见了弟弟蓝色的纹身和两根被打断的手指,想叹气又不敢叹的样子,心里很烦。过去弟弟长得还算英俊,手指因打架断了之后,像是变了个人,脾气爆燥,就连相貌也发生了变化。弟弟经常死盯着石雨春的大腿和胸部,让他不自在。时间久了,自然会生出事端。好在石雨春什么事都忍着,不发作。平时他就有点怕弟弟,主要是弟弟阴郁的神情。本来石雨春还有个地方可以睡觉,只是这两天,弟弟像是发现了什么,也可能是对房子的事有预感,烦躁不安。石雨春有些怕,只好回来住了,就是白天也不太敢去那个地方,毕竟隔壁住的是阿文,他不想给她带去麻烦。
原本是间仓库,用于放些节日时用的灯笼和彩旗。石雨春收拾整理过,放了一张能睡觉的铁床。一墙之隔是间大房子,里面有三张双层铁架床和几台电话。平时关紧了门,看不出具体做什么。第一次被那种声音吵醒的时候,以为在做梦,再后来才听清是女人的声音。那个下午异常安静。窗外伸进一长一短两根树梢。阳光洒在地上和一盆花上,让他有了美的享受,似乎也有了深圳人的感觉。后来听见了隔壁的声音。开始像哭,然后是笑,哭和笑掺在一起似乎有韵律,一声两声,身体迅速有了反应,瞬间变得无比雄壮。在这种声音里,他放纵了自己。
阿文是这间声讯台的领班。
那一天,没有太阳,连云彩似乎也离人很近。这样的时间里,他认识了阿文。他使劲说笑话,想让她笑。尽管阿文不笑的时候也很美。这是他一贯的作法,即使是心里在哭,嘴上也能讲出笑话来。他还能模仿赵本山,范伟,赵丽蓉说话。他拿自己都没办法。“你这是没有安全感。”胡玉则这样评价石磊。他听了,半天说不出话。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这样了解自己。
当然在家里他不会这样。他只会愁眉苦脸,或沉默不语,一句笑话都说不出来。他不愿意见到父亲那双深陷的眼睛,总偷偷看他,似乎有话要讲。被他盯过的脸,如同被马蜂蜇过,发紧甚至是痛。有几次石雨春甚至发了火说,“你不能看电视啊。”他指着正播放减肥器的电视机继续说,“总是看我干什么,我脸上又没长钱。”
“我没看啊。“父亲闪开眼睛的同时急着辩解,脸还红了,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全是变态佬!“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对于这个家,石雨春一点办法也没有。
见到阿文当晚,他显得闷闷不乐。反倒胡玉则心情很好,主动给石雨春按摩后背。即使这样,还是觉得胡玉则的声音有些做作和刺耳。激情后,眉头留下两条皱纹,直到出了门,都还没有消失,包括那些小动作也显得与年龄不符。
心里有了阿文之后,他变得小心谨慎。胡玉则的眼睛无处不在。除了担心阿文受到牵连,他更害所丢掉眼下这份好工作。
快进家门时,胡玉则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不想接。他猜想这个女人又空虚了,需要慰藉,或者知道了房子的事想安慰他。他不需要安慰,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为了结束这段关系,早在几个月前就减少了与胡玉则的见面次数。结束担惊受怕的生活后,内心里,他对生活做了安排,大大方方追求阿文,然后在阳光下恋爱,享受属于自己的深圳生活,。他甚至有预感,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总之他的内心因为阿文有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内心变化。他开始变得现实,包括不再扮酷,多数时间不再去梦想一夜间变成富人。他还能到街上拣些便宜货,比如快收早市的肠粉和前一晚的面包。两块钱买三份,全家的午餐也有了。运气好,还能碰上有肉或有蛋的。
再次是外表的变化,他的装扮已恢复正常,不再像电视里的香港人深圳人,把自己搞得有别与常人。
他觉得与深圳已接上了地气,不再陌生和客气,
石雨春想到深圳发展,除了老房子,还有一个理由,那便是,他不喜欢东北。东北已经没什么可以留恋的。现在谁不向外跑啊。海南云南威海深圳广西,哪好向哪去,哪远去哪,中途也不停下。父亲厂里的烟囱被吊车拉倒、拆掉之后,他的小城像是没了坐标,让他找不准方向。他觉得自己投生错了,应该生在富庶的深圳,而不是已经萧条落寞的东北。在东北,用他的话来说是猪狗不如,活得窝囊,抬不起头。他越是不喜欢东北,便越想成为深圳人。当然,他指的是有户口有房子,落地生根那种,而不是和他一样漂着的打工仔。这样想的时候,连脚上也迈出了深圳人的韵律。见到本地人,竟有种说不出的亲和说不出的喜欢。从心里喊出一句,“你好,我都系深圳人。”对方瞪着他,扭了头,跟同伴骂了他一句,“七兴!”。
他听了,也不生气,而是友好地笑笑,在心里喜喜地补上一句,“我想同你们好啊。”他用的是深圳普通话。听见自已短促的句子,回荡在空中,石雨春内心非常愉快。想事做事,也有了感觉。
为了让自己像个深圳人,有一阵子石雨春想把名改了,弄成石阿什么的,南方味十足。他觉得即使深圳的农村也好过东北。后来打听过,有难度,只好在口头上改了。“你们叫我阿春吧。”
改了之后,说话做事也渐渐找到感觉,就连人家的冷眼和排斥也会觉得好,是讲文明。过去他多么自卑啊。父亲做不了深圳人。自己却可以经过努力变成深圳女婿。这样一来,父亲与深圳还是能够有某种联系。有了这样的计划之后,他不断学习白话、客家话,除了是跟本地人沟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稀释自己口音中的土味。为此他把电视上学来的江浙话、四川话湖南话也放进来,只要摆脱卷舌、大楂子味就行。除了粤语、客家语那种韵味让他着迷。他喜欢深圳人那种无所谓的神情和生活习惯,比如喝早茶,吃宵夜。
石雨春根本就不把自己当东北人,装束和言谈举止上便能看出来。从小他硬着舌头学深圳话,最后也说得有模有样。进艺校后学了不少粤语歌,用电视上深圳人的服饰来打扮自己,看见街上来旅游的深圳人也特别亲,总想上去攀谈几句。有一次还差点被两个温州人骗了,只因对方说他们是从深圳来的。不少人看不惯他的作派,不愿意跟他玩。认为他不务正业,行为怪异,爱装,尤其是模仿电视上的香港人和深圳人装束、语调。街上有几个小流氓看不上他,不喜欢他这样出风头,总想找荐打他一顿。弟弟知道了,自然要和人家对打。他这么做并非为了支持石雨春。为了证明讨厌石雨春的表现,他不仅很少和石雨春说话,也不跟别人说,更不要说与人打交道。
对于石雨春的打扮,父亲倒是很开明。瞥了一眼儿子那张秀气的脸和脖子上的项链,开脱道,“就是有点娘娘腔,不算大事,身子还是男的。坏就坏在小时候他妈妈给他穿花衣服,梳小辫害的。他这么折腾,只是想扮成我们深圳人。”父亲长得瘦小枯干,没有精神,只有说到深圳的时候,才像是缓过神,话多得没完没了。他总是对人说,“早晚得回去。老子的大屋还在深圳呢,那种房子结实,能住几辈子。”父亲这种话多了,谁都不再相信,包括儿子。正是父亲这张嘴,兄弟俩才让街坊邻居看不起。“那你咋还不去发财啊,待在这儿干啥,也没人想留你。”
父亲红了脸答,“快了快了。”本来他不算爱说话的人,可是,只要一说到深圳和老房子,他就像变了个人,滔滔不绝,从早晨到晚上,从日出到日落。除了这个,他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关心。石雨春不同,他不仅喜欢说话,还能把深圳的事说个头头是道,连深圳的人也被他弄得一楞一楞。
有人觉得石雨春活得这么拧巴,与他这个做老子的虚荣有关。十岁之前,父亲总是拉住他和弟弟讲深圳故事,每次说到香蕉,马拉高、烧鹅、肠粉三个人的肚子同时响亮地叫起来。父亲最常念的是,“我是深圳人,街上有个集体饭堂,里面十多个四方形的小窗户,外面是一排刚吐嫩芽的小树,吃饭的时候,能看见三面红旗在飘扬。”除了这,还经常说到,“我妈拿蕃薯去上沙换大米、花生油,有时候还要帮人磨成粉。我爷爷穿绸缎马褂,腰里还别着盒子枪。好日子没过几天,天就变了。老子只能逃跑,不跑就得死。谁也想不到,老子因祸得福了。
那可是最好的年代。东北让我成了工人阶级,有了户口、老婆和儿子。”他总说自己是个地道的岗厦人。土改的时候大家一起逃港,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被抓了,最后结果是都没了命。他在海里游了一半,被浪冲回岸上,躲了一夜后跑到广州,再爬上货车到的天津。在码头、车站都干过。去了东北还是担心被人追赶,就连名也改了。半年不到就做了修路工人,也有人逗他,你瞎跑什么啊,要不然你都成亿万富翁了。这个时候他会变了脸说,“那年月,谁不跑啊,个个都像蚂蚁一样,连命都保不住了。被打死的文金胜你认识吗。”听的人一边笑一边摇头,好象父亲是从古墓里出来的人。
石雨春听腻了。青春期的时候,做梦也会见到自己拿着枪,四处追杀一个吹牛的男人。醒来时,见到父亲半睁了眼自言自语,口水流到枕头上。多数时间,他认为父亲是在编瞎话骗人,就是为了让别人关注自己,给他介绍一个老婆。他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来找他。邻居会会拿这家人举例,千万别学他们,三个男的没个正常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女孩绝不能嫁给他们。
最初,父亲提到深圳时,还讲不清住过哪个区哪个街,非常笼统、含糊,只是说,老家那个地方离海最近,站在土堆上就可以看见海上的渔船。直到中央台播了岗厦拆迁的新闻,才发生了改变。也有不怀好意的凑上来,说,“电视上说的深圳是你那地方吗,再晚了钱可就拿不到了,还不快回去啊!”
石雨春看见父亲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嘴张到一半又合上,说不出话,非常可疑,与法治栏目里那些骗子差不多。说话的人摇着头走了,到了后半夜,父亲摇醒石雨春,说,“就是岗厦,岗厦14号没错,全想起来了。”石雨春眼皮抬了下,又睡着了。父亲瞳孔睁得奇大,笑声也瘆人。猜想父亲又打歪主意了。对父亲来说,这么做已经不是第一次。撞大运,见者有份的思想他从来都有。没权没势的人,做梦都想着发财。他理解父亲用心,不是为自己。毕竟兄弟二人都到了成家立业,娶老婆的年纪,可连个影都还没有呢。
东北不能待了,再待下去,石家就要断子绝孙了。父亲在一个深夜,对着石春雨说。仿佛天已降大任于他。
所有的事情都预示了石雨春终有一天会来到深圳,为父亲也为自己找条出路。堂皇的理由是找回老屋拿回赔偿。对于石雨春来说,真正的原因是他讨厌东北而喜欢这个新地方,即使没有赔偿这档子事,他也想来,通过努力变成一个深圳人。
石雨春提前了半年到深圳探路。作为家中长子,他的计划是三年闯出一片天地,然后接父亲和弟弟到深圳享福。连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仅找到了活,而且还非常体面。如果没有父亲和弟弟这个负担的话,这个收入也够他用。弟弟在家里惹了事,对方不依不饶,非要赔钱,还不到半年,父亲和弟弟只好到深圳与石雨春汇合了。
对于处理结果和父亲的表现,石雨春早有准备。这些年,他从没有放弃过对父亲的怀疑。他猜父亲即使是广东人也未必是深圳人,是深圳人也未必是岗厦人。尽管父亲的话他能背下来。有什么用呢,再去对人说那些,只能是笑话了。这次没有成功拿到赔偿,父亲又想回东北了。
只用很短的时间,他就把这件事想明白了。如果回去,没脸见人是其次,能不能吃上饭都是回事。想做苦力也找不到地方。即使死,也要死在外面。石雨春认为人要有志。人走了便是泼出去的水,蒸发了,再也回不到原地。想明白之后的石雨春一身轻松。
从办事大厅回来,石雨春不仅没有责备父亲,还买了一瓶洒和半只烤鸭。想与父亲喝两杯。是种表态,也算是一种解脱。大意是,即使没有老屋子,没有财产,父亲仍然是父亲,儿子还是儿子,别把亲情想俗了。作为儿子不怪这个老子,要怪只怪他们又穷又没活路,才想出的下策。一切都过去了。没有对与错。他想好了怎么说,用一种小品的语言,轻快,幽默把话说完。让这一段历史划上句号。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祖宗宅基地。他要用山东块板的方式表达。借助自己的双手,让一切重新开始。顺便也说说自己的事。每次想到可怜的阿文,就会心痛不已,甚至会有泪水。连自己都奇怪,从小到大,他还没有这样心疼过别人。也许之前受的苦太多了,人已经变得麻木。只有一墙之隔却不能说话,除了担心被胡玉则知道,更担心伤害阿文的自尊心,毕竟她干的不是一个体面的工作。在深圳,每个人都有不愿说的事,不能公开的秘密。即便对方手上很有权,也未必愿意帮助任何人。石雨春的父亲早已经成了一个上访户。
“不要随便问人家的工作。“父亲在胡玉则丈夫面前表现过亲热,对方并没有理他。他跟父亲说,事到如今,不要提房子的事,都要改变话题。自己会配合他把戏演到底,。
父亲并不领情,喝了一口酒说,“你本来就是演戏的。”石雨春听了,没有生气,甚至有点高兴父亲这么讲。演戏就是文艺工作者,而不是大街上走的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整个人软塌塌的,没什么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