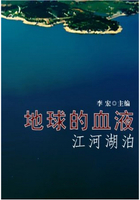三年前在大昭寺门口,听见一个摊子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陈楚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这一次在哲蚌寺外,听见维修工人住的帐篷里,传来不知哪个歌星一遍又一遍贱兮兮的哀鸣:“如果我没有钱你还会不会爱我?”
尽管从萨嘎达瓦节到西藏解放六十周年纪念这段日子,很难在拉萨街头看到老外,然而拉萨在有些方面看起来似乎无异于某个普通四川城市,一个沐足馆比比皆是且绝不比北京便宜的喧闹城市。寺庙里的诵经与寺庙外的流行歌分庭抗礼,唯有到夜深,八廓街成千上万匍匐磕头转大昭的人们,才令市中心变得肃然沉静。朝圣的游魂会穿过一幅居委会悬挂在巷口中央的“雪域高原唱响红歌”的标语横额,穿过一个音像店——白天那里震天价响售卖各种唱碟,从韩红到迈克尔·杰克逊应有尽有,还有一张叫做“夜游魂”的“汶川地震迪斯科”光碟,用伪藏歌混搭迪斯科舞曲,配以汶川地震抗灾励志画面——这张雷人的唱片正好显示出圣城如今的另一面:一个炫酷劲爆的国产山寨后现代坎普(camp)之都。
整个藏区,以及中国所有的机场书店,乃至中国所有的边远国道上,如今都充斥着千篇一律的伪藏歌。一台巨大的“藏歌洗衣机”日夜不停旋转轰鸣,只要随便扔进几匹神马几朵浮云,随便扔进诸如草原、高原、母亲、月亮、远方、思念、卓玛、白塔、圣洁之类的词,就可以瞬间搅拌出一首新的藏歌,并硬邦邦地包装成“汽车专用发烧天碟”,专门用于清洗你老人家被汽车废气喷得乌烟瘴气的肺叶。
通常伪藏歌都用汉语演唱——以中央民族歌舞团和中央电视台共同钦定的晚会民族歌曲经典模式——道理很简单,这些在主旋律和流行歌之间翩跹翻飞的伪藏歌的受众主要是汉人。昌都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出版的同志告诉我:如果不译成中文不唱成汉语,音像出版社都不愿意给我们出。于是一套囊括了昌都锅庄、芒康弦子、丁青热巴的昌都非遗歌舞艺术DVD,只好可笑地搭配上两张主旋律精品伪藏歌CD。
有一家叫作“爱琴海”的公司专门生产藏歌洗衣机,如同“达芬奇”不是意大利的,“爱琴海”也并不来自希腊,他们的路子更流行,在治疗汽车自驾游强迫症患者的同时,也为藏民提供心灵鸡汤——这样的歌往往汉语藏语杂糅,并且往往是DVD而不是CD,很多藏民喜欢这样的歌舞MV。这是被游客和藏民双重映射的西藏镜像,如同西方人为自身调制出一种中国情调,久而久之中国人也会渐渐迎合这种西式中国情调,自觉不自觉将西方人眼里的刻板中国形象,真的当成了自己的真实形象,而藏人也学会在汉人走马观花的目光中,炮制一些可供复制和稀释的简易标签符号。一切,已经做作得越来越自然。
这往往是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一种扭曲的关系。
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然乌湖被捧成“小瑞士”而越来越吸引游客。然乌镇有条美食一条街,藏民通常不吃鱼,然乌湖也不许捕鱼,但为了帮助贫困户,政府特许个别藏民捕鱼卖给饭馆,于是鱼成为四川人开的饭馆的一大特色。在一家四川鱼馆,我默默观赏了一帮广东广西口音驴友被驴踢了脑袋之后表演的一出好戏:十多个人,一个个举着相机或摄像机或手机或爱疯,一边拍一边指挥一帮藏族小孩列队唱歌,孩子们唱完藏族儿歌后,又被要求唱《在北京的金山上》,可孩子们不会,带头的脑残驴友于是要求老板娘出来唱,被推脱后这哥们干脆高喊“让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下孩子们都跟着合唱了。每唱完一首歌,就会有人犒赏文具或蛋糕饼干,并且一边发,其他人一边跟拍,弄得就跟检阅藏族儿童仪仗队似的。令人发指的是,孩子们最后被要求对着相机摄像机齐声高喊“谢谢叔叔阿姨!”。
这帮看上去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文化人,回去之后每看一遍视频,他们估计都会被自己的大爱感动得屁滚尿流,这辈子都不舍得洗裤子。面对他们施舍般的爱心,这些孩子连感恩的语言和感恩的方式都是被指定甚至被指挥的。
驴友通常满足于在美丽的然乌湖边摆几个文化苦旅兼大爱无疆的pose算逑。但只有住进山里,才知道偏远藏民大多还在用录音机听磁带。我住在雅泽村,每次当地村民骑摩托车经过,都会停下来,问我要不要顺路搭他的便车(当然是免费的!)。有一回,响遏行云的歌声随一阵摩托轰鸣而来,但摩托没有停下来,一对小两口冲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要搭车也没位置了。摩托车上挂着一个录音机,直到他们消失在喜马拉雅山顶,歌声还像炊烟一样在山顶上不绝如缕。关于音乐,这是我此生遇见的最美好的情景之一。
那首歌可不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或许是“在喜马拉雅神山上”吧。
金山还是神山?这是个问题。
对从前的藏民来说,“北京的金山”意味着遥不可及的,革命与宗教混沌不清的幻境。而今天,“北京的金山”已从一个红色世俗政权的象征变成一首钱柜或天上人间的怀旧嗨曲——它重新指代了一个金钱拜物教的黄金时代。
甚至喜马拉雅神山也金光闪闪,藏民像挖金币一样狂挖虫草。然而虫草总有挖竭的时候,山上被破坏的植被可能百年难复。旅游开发,虫草经济,加上气候变暖,令冰山和草场严重退化,牧民最终的代价可能是离开自己的家园。到了虫草季节,很多小孩都不再上学而上山干活,藏民不得不被裹挟进一种功利短视的狂潮。公益组织于是纷纷行动起来,欲从环保卫生和教育入手去改变,如今公益慈善确实需要想象力和新思维,也确实需要发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反而容易在雪山上火上加油。
比如与政府合作开发,大搞每人收费一万五千块的所谓“冈仁波齐慈善环山赛”。去冈仁波齐那边搞慈善很好,登山更没问题。但能否别拿冈仁波齐——那是藏传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的神山,那是宇宙的须弥山,宇宙的中心——来冠名?我还想搞耶路撒冷哭墙慈善攀越比赛呢!搞个环中南海自行车慈善赛,环天安门广场竞走慈善赛,环主席纪念堂狗拉雪橇慈善赛也很酷啊。我只是想说:对宗教,请多一点尊重。那不只是一张可以买回去挂在床头发小资之幽情的唐卡。有开发公司公然将神山和圣湖揽为己有,当成其上市计划的最大资本,也令有的藏民疑心冈仁波齐迟早有一天要修观光缆车,尽管这不大可能成为现实,但在高铁时代,也拦不住有人非想着如何加速通往无间地狱。
宗教在汉文化中,总是被士大夫搞成哲学和美学,被民间草根搞成拜物教——如今则更进一步沦为金钱拜物教。在成都的庙里,市民一到新年便掀起“投第一炷香”的狂潮,成千上万人涌向寺庙,抢着上香——与其说是上香,还不如说是投香,看谁能准确投进香炉。绝大部分香当然投不中,寺庙一时狼烟四起,于是和尚和警察一起一边扫香一边喷水以防火灾。
当佛庙成了投香赛场或博彩投注站,当转山道变成慈善赛道,我只能恭祝诸位痛痛快快花上一万五千块钱,在冈仁波齐找到自己那颗冻得像奶酪或者红得像猪肝的爱心。
归根到底在于:无神论的世界如何看待、如何对待有神论的世界。从唯物主义到拜金主义,在极权与“极钱”双管齐下中已然千疮百孔的无神论的世界,是否非要把有神论的世界也打个稀巴烂?
2011年6月6号,我随澜沧江母亲协会考察队寻访澜沧江源头,在可可西里东部雪原上迷路。焦头烂额之际,路边一位藏族老太太突然手指一个方向说——“扎西曲洼!”——那正是藏人对澜沧江源头的命名!沿着她指的方向,我们果然最终找到了那三口泉眼,千百年来藏人认定那就是澜沧江神圣的发源地。以严重高原反应头痛欲裂浑身打颤为代价,我踉踉跄跄终于走到那块碑石跟前。
事后一位朋友不以为然:你们被骗了!科考认定的澜沧江源头还在几十公里外,你到的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源头!
朋友说的没错,可惜我不是方舟子。我并不信教,但是我相信在科学之外,始终有一个无法完全用科学去解释和僭越的世界,我去的,是澜沧江另一个源头,历史与传统的源头,神话与信仰的源头。
在北京的金山上,你不得不偶尔抬头,遥望青藏高原的神山。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