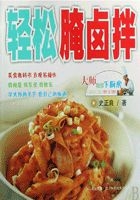后来的日子里,我从大人们的闲谈中,知道了外太太曾经做过的一件绝顶的傻事,就是在她55岁时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卖了一回。这件事情让她的人生有了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色彩。
那是1958年冬天的事情。当时整个陇东地区都弥漫在大饥荒之中,树皮草根成了美味佳肴,外爷一家人都饿得全身浮肿,不知道天一亮有谁会醒不过来。一天夜里,突然听到外太太的屋里有人说话。外奶奶就说:“听。你娘的屋里有男人进去了。”外爷说了声“放屁。”就翻了个身又睡觉去了。外奶奶伸长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突然惊恐地说:“听,你老娘要卖人。”外爷没有再搭理。
第二天早上一看,不见了外太太的踪影。而且小外爷也不见了,外太太的烟锅烟袋也不见了。地上却放着满满的一羊毛口袋麦子。外爷于是跑到门外去找,看到地上有驴蹄子印,就顺着蹄印往前找,一直到了村口。外爷向村口的人家打问,他们不吭气,目光却像刀子一样瞅外爷。有的人忍不住了,就说:“你装得挺像一头蒜的,你把你老娘卖了你不知道?”外爷听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原来昨个儿半夜里,村里看管粮田的人,看到南山里做贩运生意的潘脚户,赶着毛驴驮着一黑羊毛口袋麦子进了村子,没过多久又拉着毛驴出村口了。毛驴背上没有了粮食,却坐着外太太。外太太坐在驴身上两条腿朝一个方向吊着,一只胳膊抱着小外爷,一只手上掌着烟锅。
外爷哭哭啼啼寻到了潘脚户的家里。进屋一看,外太太盘腿坐在炕上,正伸着咬在自己嘴里的烟锅跟潘脚户嘴里的烟锅对火,怀里坐着哼哼叽叽的小外爷。外太太看到外爷跪在地上哭泣着请她回去,就高喉咙大嗓门地训斥外爷说:“你老大不小的怎算不过帐来啥?我老了也没啥用场了,给潘脚户做个伴儿,省了屋里的粮。”外爷却不停地哭喊着说自己没娘了。
这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村里的狗不明不白地叫了一夜,一大早又看到乌鸦盘旋在村子上空哇哇乱叫。早出挑水的人发现,外太太满身是泥,淹淹一息地爬在村里的一棵老榆树下,手中紧紧捏着一只木勺。原来潘脚户突然暴病死了。办完后事之后,他的弟弟潘二却提出来要分家当。外太太就拖着小外爷牵着毛驴,驮上粮食家当,连夜朝外爷家赶。走到半路上,潘二带着家门户族的人追了上来。二话没说就是一顿棍棒拳脚,打得外太太扒在地上吐血,而后牵着驴和驮在驴身上的粮食返回去了。外太太当时死死地抱住小外爷不放,潘二就朝她胳膊上捅了一刀,把小外爷扯走了。嘴里骂说:“要你这个小杂种就是来顶门立户的,哪能说走就走咧,几口袋麦子不就让狗吃咧。”
外太太被村里人从地上扶了起来,又叫来了外爷,一起抬着往回走。到了家门口,却见外奶奶提着一把菜刀横在门口死活不让进去,手指还指着外爷的鼻子骂道:“你老娘上了潘脚户的炕了,死了也是潘家的鬼了。”
一辈子都活得像一头蔫驴一样的外爷,除了呜呜地哭再没有第二个本事。天寒地冻的,为了救命,帮忙的人就只好把外太太暂时抬进大门旁边那个装柴草的破窑。随后找来一只破门板当了床,凑伙着生了火搭了灶,暂且让她安下了身。没有人供口粮,她就跌跌拌拌地到处拾捡羊粪豆,交给生产队里换点工分来养活自己。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