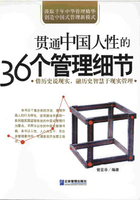那段日子一直在持续着混沌不清,作息时间任由自己,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却未曾做任何看上去有些许意义的事情。是一种放纵。经常的时候晚上只能荒芜地发呆,无法入睡,也发不出声音。
时间的概念早已模糊,只是记得二十三号,一月二十三号即将离开北京,这座早已熟悉了的城市。我曾经费力且自然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却忽略了这里没有供我生存的土壤,有的只是一片水泥钢筋的生冷嘈杂。
我对朋友们说,我要回老家了。可是话说出来却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胃里一阵痉挛。可我属于哪里呢。我想或许我从未打算停滞,那个叫葵的女子一直都在以出发的姿势等待一种召唤,等待着感知,所以一直走在路上无法停息。
我说,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亦不明晰哪里才是我的家乡。
桑道,所有回不去的地方,都叫做家乡。
我与桑的见面,只有一次。
我是葵。那时还在北京。
到超市去买了很多食物,装了满满的两个大塑料袋,包括吐司面包、酸奶、薯片、话梅以及各种花花绿绿的膨化食品,还有几盒泡面。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床,睡觉,躺着或是坐着发呆,不停地听摇滚,聊QQ,打游戏,看电影,浏览各种网站,一直都蜷缩在被子中。其实很宅,也很懒,更是很疲。疲于外界的繁琐喧嚣。在画室里学习美术的时候,曾经对一个喜欢动漫的女生说,其实我是干物女欸。她白了我一眼说,小萝莉,不要装成熟。
很多时候懒到一定地步都不肯跑去音像店买光盘,尤其是在那气温骤降的一段时日,于是便依赖上了用虾米网听摇滚,枪花儿,战车,谢天笑,痛仰,扭机……也上网找一些电影来看,顺便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电影的相关资讯。又看了一遍很早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宫崎葵主演的,叫做 《 现在 只是爱着你 》,老套的桥段却足以渲染,是温暖人心的小东西。陆续地又在凌晨2点左右观看了 《 玻璃之城 》等老电影,然后无意间发现看的这些电影都有一个相同的人曾经浏览过,叫做曙桑的女子。
后来和桑在QQ上聊得情投意合,她说她失眠她焦躁不安她敏感但她对外界淡然惘闻。当然这是在和她熟悉了许久之后的话了。但在最初的时候,我进了她的空间看了她的文字,就坚信她是这样一个人。她用她的文字在肆无忌惮地做她自己,肆无忌惮,这个词很好。但她不像我,她还是在乎很多的,所以她比我容易受伤。
我们看到对方的内心像看到自己,但在对方的眼中又彼此神秘。不知道网线的那一端的女子有着怎样的面孔,什么样子的社会身份,又因何造成这种孤僻的性格。我们彼此从未问过,好像无关紧要。但那是多么吸引人的呀。终于我想约定与她相见了。
鲁兰说过,她最喜欢的一个词是奋不顾身。鲁兰不是什么名人,就只是我彼岸葵的朋友。她同我同桑不同,她把所有的利益得失都看在眼里记得明白,又活跃异常善于笼络人心,永远要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我曾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本子上写着“打倒彼岸葵”几个大字没来得及翻页。鲁兰总是会在没有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翻看我的本子或是文章,再去思考怎样超过我。她让我觉得可憎且可悲。可她确实也是把我当作好朋友,即使不会像五年前初识的时候形影不离,不会再说那些知心话,不会再一同牵起手走在夕阳下,不会一同唱歌读书感伤,但我们还是好朋友,互相不会说话的好朋友。
一些东西一旦有所改变,选择放在心里尘封保存而不把前后相联系,也许是最为妥当的办法。
很长一段时间里喜欢站在高中艺术楼的顶楼,曾经无数次与鲁兰一同吹风沉默的地方。时光荏苒,剩我一个人站在这里,看着天色慢慢暗下来,夕阳晕染出长长的一片暗红笼罩住城市边缘,一座状似灯塔一样的建筑上,灯光忽明忽灭。傍晚的风冷冽却清醒,有种长驱直入心肺的悲凉与决然。纵使我们曾是那样的如胶似漆,我们还是各自坚持自己不肯妥协。
家门口前的一条街上有很多酒吧、串吧或是咖啡馆,其中有一家叫做The runaways的pub尤其喜欢。逃亡,记得这是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的名字。我喜欢它的名字,喜欢里面播放的摇滚,喜欢他苍灰色的砖阴绿的爬藤,喜欢它昏暗但却温暖的设置,喜欢它的主人,那个叫做睿的男子。
每次都是坐在角落里,二十多一点的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马克杯的浓缩咖啡。沙发很缠绵,但麻布窗帘却没有一点暧昧,睿大多时候都会坐在吧台后用一些奇怪的工具颜料做出一些奇怪的装饰品,鬼魅的色彩和奇特的创意大概是共性,他做得按部就班,我看得很有耐性,通常一下午的时间就会这样度过。
后来那天我在QQ上对桑说,我们见面吧,就在一家叫做The runaways的pub好不好。
我终于想约她相见了。但是桑说,葵,再过些日子吧。她说她喜欢夏天,她希望我们可以在那个季节炽热的阳光下相见,可以看到明晃晃的阳光在彼此发丝上跳动,多么美好。
多么美好。于是我就这样妥协了。
在几年前这样的日子里,那家叫做The runaways的pub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财富,我愿意津津乐道,因为对象是鲁兰,那时的我们是那么愿意互相分享。
每一个在The runaways的午后或是傍晚都留在记忆中成为凝滞而粘稠的时光,看着男子旁若无人地制作着自己的工艺品,为之乐此不疲。也有乏味的时候,或是起身用干净的手指更换唱片,或是擦擦他的杯子,时间在那些时候总是缓慢下来,平静流淌有条不紊。
男子在他的咖啡店外卖棉花糖。很奇怪的组合。但睿说那里面都是快乐。
某一年的11月22日,睿拿着一杯加冰威士忌放在我的桌面上,说,生日快乐。
我抬头,满脸惊诧,你怎么知道我生日?话未问完顺着他的目光就已明白了真相——我把鲁兰送的生日卡片放在了桌子上。
我笑得很不自然:“谢谢,不过——”
“——不过你从不喝威士忌对不对?”睿笑了笑,继续说道,“你每次都是点咖啡的,而且偏爱爱尔兰,不过今天是生日呢,而且你放心,我在里面放了很多红茶。”
这是我与睿的第一次对话。这之前,我们在同一间屋子的不同角落各自沉默;这一天,他请我一杯红茶威士忌并且谈天。于是终于,豁然洞天。
那时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拥有鲁兰,拥有睿。或者说是拥有我对他们的情感,如此而已。从一开始我就是珍惜的,我小心翼翼而锐不可当,两个知心的人,在我的心中那么重要。
他曾复读两年终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却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把它撕碎,来不及阻拦和错愕,睿早已转身离去。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背离了那些束缚那些规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那么好了,他选择四个字留给大学、学历、工作、升职、薪水和尔虞我诈:恕不奉陪。他背离了许多,甚至所谓光明的前途和一直以来父母的期望。对于后者他是不忍的,可是他走向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热爱,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他去走向自己了。一场忍痛的背离,终于毅然决然不再回头。没有什么不好。
他愿意和我一同谈天或是沉默,他愿意抛下小店陪我逛街、照相,他会开始在每个晚上九点送我到住所的门口。我,是一个叫做葵的女子。这样简单。这样简单地我对他产生某种依赖。一个人的孤独寂寞总是如此轻易地暴露出来,仅仅是一杯威士忌,和递过来那杯威士忌的那双温暖的手。
直到现在,直到现在我彼岸葵依然记得叫做睿的男子他的笑容、他走路的动作、他说话的神态、他点烟的样子、他绘画的认真表情。可是现在,可是现在那些我所记得的,都已成为我的曾经。
此时我距北京569千米,这是一座节奏缓慢的小城,街上随处可见小店的标牌,一个挨着一个,密集而做工低劣。小店的店主们都将自己的商品摆一部分出来在属于自己门口范围的人行道上,使小街看起来拥挤而混乱。沿街随意地停放着些车辆,从货车、面包车、商务车一直到私人轿车、出租车,甚至载人小三轮和摩托车样样齐全。行人徐行,用羽绒服、帽子和口罩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一切有条不紊。
很少有这样凝滞的时刻。我赤脚站在阳台上缓缓吐出几个烟圈,懒散的小城一角此时被收入眼底。我不嗜烟,只是某种安谧的时刻平静的方式。几天来没有任何活动,在这座城市中穿行生活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为我所熟识。此时正是下午一点十分,彼岸葵穿着宽松的睡衣,乱着头发赤脚站在阳台上。很多时候我都怀疑这日头快要将自己烤到沸点了,可楼下街上的人们却是寒冷瑟缩。这阳光耀眼得像是一个谎。
还不适应这样的生活,一切过于平静,一下就惊慌起来感到自己与理想脱了节,背离得越来越远。一下明白了睿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未来的付出,也许从开始便是与理想相背而行。可是明白自己有很多的不可以,葵是葵而不是睿,她必须现实而无法潇洒。可是她感激当她处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在这条陌生的路上一切无法依赖时,她终于发现了自己,还有属于自己的曾经。
彼岸葵的曾经,是几个连缀而成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穿在一根细线上,不敢轻易触动,生怕碰到其中哪一个叮铃作响,便会在心里产生波澜而久久无法平静。
她轻轻地在心里读着那些名字,知道自己即将与从前割裂并开始新的自己。然而,在那个全新的运转轨道铺开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有时候她干脆想把这整个世界连同所有的经历都当作是一个假象。比窗外那些耀眼的阳光更大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