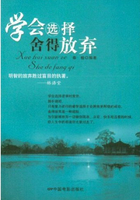沙城的夏天依然如火如荼,即便已是季节的夏末。9月中旬的好几天里,办公室的窗帘被我紧紧拉起,而我持久地坐在转椅上,晃着身体细致筹划接下来这场幸福的分配,在筹划中感受内心充沛的喜悦。分配的三大方向是确定的:父母、妻子和妹妹。按平均分配的原则,三者分占的钱数大约五万。设想一下把五万块钱同时交给三者,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妹妹也许刚好够,我可以把这份钱作为一笔基金,另开一个账户存起来,余下的几十年里,在她旧病新病发作时,取出其中的一部分应急;妻子的那份也设成一笔基金,时不常地给她买一件相对贵重的礼物吗?那又能买几件?这一区域好像用五万块远无法填满;父母,我最想看到的,是他们住进一套像样的房子,可沙城近年来房价涨得飞快,现在,就算交付一套小户型的房子,别说五万了,就是乘以三——把整个这笔钱几乎全拿给他们,也不见得够。筹划的结果最终是失败。喜悦的感受终究化成了沮丧。在9月中旬的那些天里,我反反复复地游走于喜悦与沮丧之间,终于喜悦的感觉烟消云散,只有沮丧稳稳地矗立在那里。
如果能把心、肺、脾,一切,全部卖掉就好了——据称一个心脏可以卖到六十万、肺三十万、脾比肾也要稍贵些——那很可能使我一时间有超过一百万的钱去支配,可一次卖肾行动使我深刻地认清了自己,我不会有那个勇气再去卖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件了,尽管我那么有意将它们统统卖掉。
竟然只是做了一场无用功——我意识到,刚刚换取的这笔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原先困扰我的精神疑难。我需要的是一笔真正的巨款,而不只是十六万。用十六万去向我的亲人们施爱,远远不够。
在9月下旬业已进入生活的时候,我陷入深深的抑郁,一如我先前因那个课题引发的精神困顿那样。失去一个肾,暂时并未使我的健康状况出现异常,说明我还年轻着。拆线后的伤处,除了一条明显的疤痕之外,并无其他不妥。有时,我用力摁压那里,感觉不到明显的疼痛。但因了比他人少了一个器官,我总觉得自己现在是残缺不全的。这种认识加剧了我的抑郁,使我一时间有些慌不择路。
有个在深圳工作的网友从去年开始就竭力鼓吹我炒股,对于他的好意,我一直表现出充耳不闻的态度,真实原因是那些时候我手头根本没有像样的炒股资本。从去年开始,直到这个9月,股市持续上扬,每次在网上碰到这个网友,他总替我惋惜。有一天中午,我再次在网上碰到了这个人,他一如既往地再次游说我进入股市。这一次我被他说服了。现在我有理由被他说服。没作深想,我把十六万块钱全部买成了股票。
我想说的是:即便是10月都快来到了,我都没有想过要去跟踪那个男人。我一直想用自力更生的方式去实现心里业已巩固的那个宏愿,并不想危害他人。如果寻求幸福需要先剿杀他人的幸福,这种寻求并不可取,这我知道。可要是幸福来临的途径只剩下了剿杀他人幸福这一条途径,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股票突然大跌了一次。我醒觉是在用自己的血肉进行一桩风险莫测的买卖,吓得赶紧把所有的股份都退了出来,不过两三天,十六万就减少了一万。我瞪着仿佛失而复得的这笔钱,心有余悸。
13
男人五十四岁,身体矮壮、大腹便便,未开口先笑,笑时一只眼睛不自觉眯起来,又审慎地隐隐睁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一年四季穿着那类板正的中山装,纯黑或咖啡色,从里到外,他都与我们通常定义的贪官的样子极其吻合。确信他是个贪官的依据,除了以上列举的情形之外,还有他同样具有贪官特色的家庭组构:他的妻子在市房管局身居要位,唯一的女儿这个夏天才从英国一家三流金融大学学成归来,目前刚刚去沙城一个政府要害部门上班。在不久前的政府要员竞选中,他的大幅照片一度占据了沙城日报的主要版面,有一天晚上,在沙城晚间新闻的录像中,他低着头,表情呆板地宣读一系列让人无法记住的套话——他的嘴角长着一粒黑色肉痣,两根粗黑、长过三厘米的汗毛随着他嘴唇的张合醒目地颤动。倒不是因为他近段时间在电视、报纸上频频出现使我对他印象深刻,致使我决定对他下手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恰好认识他。去年的某一天,他与一群随行人员来沙城医学院视察,到过我的办公室,为了表示他的和蔼可亲,那日他当众给我发过一张名片。后来有一次,我一位家住沙城的学生很想去他管辖的一所医院工作,我曾自作聪明地带着那个学生去他办公室见过他一次,虽然那学生的工作最终在他老到、狡诈的敷衍下告吹,但总算使我与他有了些微实质性接触。对有所接触的人下手远比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下手要容易些,原因来自心理,对于那些完全空洞的人,我们总是心怀更多的畏惧。
沙城10月的气温有所下降,但夏天还正襟危坐在那里。来自海上的风小了些,阳光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我从已经变成十五万的十六万块钱中拿出一万块,作为近期使父母和妻子惊喜的小小道具,时不常地买件把两件东西犒慰他们。那段日子,我的家庭生活前所未有地愉悦,令我信心倍增。妻子到底还是发现了那条长过五厘米的伤疤。我记得那夜她发出了一声尖叫。这是怎么回事?她高喊。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东西?我赶紧装疯卖傻,说,这东西从来都在我身上啊,怪就怪你到现在才发现。妻子少有地冷静,她责令我侧卧在那里,方便她好好地把伤疤研究一下,过后她又扯去了我的所有衣裤,要看看我身上到底还有哪些她不曾发现过的隐秘。她把台灯拉到床上,使我精瘦的裸体一览无余地陈列于她的眼前。你什么时候学会说瞎话了?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再也不能装傻了,这个时候误导更有效。我让自己阴下脸,反戈一击。我说,你还好意思问我,我上个月被别人捅伤了,有心跟你叹叹苦,你倒好,成天骂骂咧咧的,不给我机会,让我一个人承受苦闷。你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妻子一愣,当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她史无前例地比我早醒了。你应该告诉我才对,夫妻间有什么话不好说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家不败了吗?现在好了没?有没有伤着里面?什么时候你也学会跟人打架了?是这块料吗?我穿上衣服,摸着她饱满光洁的身体,柔声说,小事一桩,早没事了,要有事还能躺在这儿吗?男人嘛!身上有条疤,也是种性感,对不对?妻子撇嘴,乐了。以后自己小心点。她快速出门了,留下我一个人躺在寂静的房间里。10月是安静的,同所有的沙城时光一样。我心里空洞无物。
14
医学院老师的身份为我接下来的谋杀计划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9月到10月期间,我和学院一个叫吴斌的药剂学老师兼我的同乡走得极近。我请他吃了两顿饭,培养与他的感情。为了使我的接近显得不那么突兀,第一顿饭我是以同乡会的名义请的。饭局设在临海的粤菜楼。那顿饭效果不错,往常的同乡聚会都是凑份子,像这种一人出资的情况很少有,因为少有,作为独资者的我在这次饭局中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一个劲地与吴斌胡吹海侃,一扫我往日的木讷与矜持。第二顿饭就是我与吴斌单独面对了。男人的友谊来得那么快,警惕心并未在他身上出现过,他对于一个一贯被大家认为清高的人的示好极为受用。第二顿饭的那个周末,就是他主动请我了,我们去城北的烧烤店吃了顿自助晚餐,为了证明我们友谊的水涨船高,他最后还主动帮我吃掉了一块冷掉的牛肉和一条鸡翅。夜晚因男人间的亲密无间变得炽热和躁动。我顺势让预谋中的邀请出场,拖着他去了一家发廊,再次独资,让他享受了一次身体狂欢。两个男人到了共同去找小姐的地步,就变成一个人了。叫吴斌的同乡接着每天晚间饭后到20点30分这段时间都打电话给我,邀我一道去散步、打球或去各自的办公室讨论学问。我们谈许多关于世情、生计、学术的话题,变得形影不离。在10月上旬即将结束的一天,我故作无意地跟他去了他的实验室。在我的鼓动下,他彻底放松了警惕。我们要了两箱啤酒、几种袋装小食品,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胡喝,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双双醉倒在地。半夜里我挣扎着爬将起来,睁大空蒙的双眼,去药物架上找到了几盒胰岛素。连同我早先从其他科室窃取的一副注射器具,我将它们锁自己办公桌最里面的那格抽屉里,静待那个官僚落入我的手掌。
在与吴斌套近乎的那些天里,我同时完成了对那人的密切跟踪,完善了这次谋杀计划。那男人住在高新住宅区十幢三楼,有一个专职司机每晚10点之后护送他回到住所。司机一般将他送到楼下,目送他上楼,两分钟后开车走人。那小区的保安检查并不严格。如同很多小区的保安一样,出于审慎的考虑,他们一般不轻易拦阻那些看起来气宇轩昂的进门者——这小区住着相当数量的显贵,保安们总怕因盘问而开罪某个显贵或他们的家属。我要做的是,让自己进大门时尽量显得倨傲无礼。他们一般不拦我,有一次,有个保安作势欲阻挡我的进入,我冷冽地瞪他一眼,他临阵退缩了,任由我大步走了进去。
但谨慎一点的话,我不应该将谋杀地点选在男人的家里,一来你无法控制他家人的去留,何年何月才能等到他单独在家的时机呢?二来我老是进出这小区,必然会给保安们留下印象,一旦男人暴死,他们很快会追想到近期频繁在小区出没的这个神秘男子。更不可能选在他的办公室,那个地方是真正戒备森严的,我根本无法在不留痕迹的前提下踏入一步。最妥善的只能是,在熟悉他的行动规律后,抓住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哪怕只有他与司机两个人也行。
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类人远没有普通百姓那么懒散,况且他们是那么的忙,绝少有单独游逛的时机。10月变得极其地漫长,在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焦虑。我的课题还没完工。事实上,自从我躺到手术台的那一天之后,它已经越来越被我漠视了。这世界确实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课题,而我,现在似乎也已经没有足够的理由重视它。它无疑要草草了事了。这种漠视,给我带来的好处之一,是我慢慢走出了它给我带来的精神困顿——说实话,先前我也并没有进入得太深。现在我的念想全部集中在这桩计划上去了。我走火入魔般专心于对那个男人的跟踪和研究。有些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关在洗漱间,打量身上那条日益与肤色接近的伤疤,有那么几次,我深深地后悔了,觉得如果早想到现在的这个途径,就远没有必要如此残暴地对待自己。也有犹豫的时候出现,我担心这次谋杀最终失败,非但不会令我如愿,还可能事情败露,到那时,我不仅人财两空,还会累及家人,这是很可怕的。唯一的办法是开动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博士的脑袋,使这一行动天衣无缝,不求上天保佑,唯愿自己严谨和周密。
15
中年男人喜欢吃菠萝蜜。这是一种据说甜得发涩的上等果品。在沙城的巷子里,随处可见附近的果农将它们硕大的身体堆放在三轮推车上,行人经过时,他们懒洋洋地用土话献媚地叫卖。我从未吃过这种东西,它们闻起来太臭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臭味。不要说吃,就是让它们摆得离我近一点,我都无法忍受。还有榴莲,也是奇臭无比。但很多人喜欢吃这些水果,菠萝蜜、榴莲,甚至一种专门长在岩壁上的不知名的坚果。这证明人的口味是千奇百怪的,神秘莫测,与死亡的诡异如出一辙。10月初的一天,我曾经走到那男人的家门口,听到里面一阵似是而非的争执。男人的妻子高声控诉他不该在她数次提醒的情况下带回一瓢菠萝蜜——她也厌恶这种东西,真想不到我与这个陌生的女人还有同好。更多关于菠萝蜜的争执没听得太清,我很快警觉地奔离了那扇门。
男人竟然也有孩子气的一面,这样一个常人眼里的达官显贵——谁没有一点孩子气呢?即便垂老的暮年人——我数次看到他回到他家那幢楼的楼底时,在车里停留几分钟。越过半开的窗户,我遥遥看到他急切地伸出手来,接过驾驶室里司机递过来的一瓢黄澄澄的菠萝蜜。它是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顺便买来放在车上的。我望见他飞快地吃完,用随车的纸巾潦草地抹一抹嘴,接着心满意足地爬出车门。那样一幅画面拉近了我与这个政客的心理距离,在跟踪完毕回去的路上,我有时甚至会觉得他有点可爱。
我再三分析,觉得最能促成这场谋杀的时机,就是那男人走入混乱的小巷聊解口舌之欲的某个时候。问题是那个英武的司机基本上与他形影不离。通常,都是他们把车停在接近巷道的一条大马路边,司机的手插进裤兜里,摸索着零钞走进小巷,而后大步流星地托着一块菠萝蜜走回来,那男人一直仰坐在后车座上。也有例外。司机有时在停车的当儿,恰好手机响起,或者他可能要趁着停车的空当去上个厕所。也许他还是阳奉阴违的,很多司机都这样,装作有事不下车,由着领导自己走入巷子寻觅美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有接近两成的时候,那男人会亲自走下车去。反正,不管谁去觅食,那个时候我总混迹于人群和人流中,与他们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