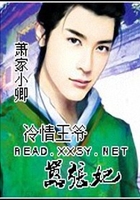我闪进书房,锁紧门,让自己逃进那个艰涩的课题,同时给予她缓冲情绪的时间。结婚两年来,我总在说服她,向她灌输一个孩子对家庭和人生的必要性。我是喜欢孩子的,至少我觉得孩子很美,可以使沉闷的四角房间欣欣向荣。这个夏天我忽然背弃了原先的意愿,觉得去生下一个必将由他(她)自己去承担死亡命题的孩子,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世界上的孩子那么多,我就不要再去添乱了。那个下午我从书房里站起来,撩开窗帘眺望这片住宅区远处的一座高峻的水塔,觉得沙城出奇地安静。我把手机拿出来,翻查到那个手机号。看着它,我心里一阵一阵地打怵。
并不复杂。我是说接下来的电话协商。手机号不是假的,我那个挚友素来办事缜密。由手机另一端那个条分缕析的女声判断,号码背后的团体是颇讲章法的。他们竟然主动向我提出签订合约。我以为这种私下里的交易是不需要这种法律文书的。电话里的女人说,该有的程序还要有,主要是给双方一个心理上的保障,大家都需要信任,签字画押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肯定可以使人心里踏实。最主要的是你,你需要获得心理支援,有一个合同在那里,可以保证你躺上手术台时至少不会那么紧张。
合同先用邮寄的方式拟定。他们要我进行一系列的体检确证我身体健康并将体检单传真过去后,即刻给我发来一份电子版合同样稿。我酌情修改,用邮箱返寄给他们。如此再三,很快我们将所有事宜协商确定。我打印两份定稿,都签上我的名字快递给他们。三天后他们就将一份盖有章印的合同寄达我手中。合同正式生效,这事启动了。这是一个国际大型人体器官交易网络上的一个小小分支,办事效率奇快。最后商定的肾价十六万,合同生效时预付两万,手术前付八万,尾款术后即付。营养费自理。手术定在即将到来的9月8号,在此之前,他们会紧锣密鼓地在世界各地寻找身体可以与我的肾匹配的买主。9月初的一个早晨,我躲在书房里,取出他们先期打来的一沓订金,悄悄将那份英文版的合同在书桌上铺开,感受着来自身体的一次又一次的轻微震颤。
9
我后悔了。这是我想到又没想到过的局面,证明我做不了一个特别能驾驭自己的人。在9月初的那几天,我多次跑进洗漱间审视自己的身体。出人意料的是,我竟至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是美的,一种由坚硬、沉着、简约组成的美。这是成年男性的美,美不仅只由嚣张的状态呈现,有时候,朴素也是美的。我找出一只新的剃须刀片,试着用它抵住我的胸大肌。我看到刀刃与肌体之间出现一条凹线,这是弹性:弹性,生命力的体现。我也是有弹性的,一种柔韧的弹性,它始终蛰伏在我卑微的体内。所有的身体都是美的,它们由一个个饱胀的细胞构成,还有水,人的身体都是生动的。我怆然将剃须刀从胸口移开,抚摸着刚刚出现的那条红印,不知所措。
我一动不能动地卧在一堆钢筋水泥的下面。饿了,我就强迫自己睡过去;醒来,我就要求自己不停地说话、唱歌。我知道隔着上面这块塌方的钢筋水泥,就是我妈和我弟的尸体,我不能去悲伤。只有一个念头,等下去,直等到有人走过这里。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我不断对自己说。
墙上的某一段字迹深深地望着我。我由此想到,生命就算不必珍视,但也是非珍视不可的,因为珍视是人的一种本能。本能是多么强悍的一种力量,它随时可以歼灭人精心设计的方案或计划。
妻子在书房外大力敲打门框,叫我赶紧出来去超市购物,她刚刚发现一个月前放到床柜里的一整袋卫生纸全用光了。我哗然打开房门,颤动着双臂抱住她。身后一大片的阳光越过窗户印在妻子的脸上。我看到她吃惊不已地推开我。我心虚又诚恳地向她求欢,她拒绝了。我并不恼,拿起钥匙窃喜着去了超市。
电话里沉稳的女声还是那么沉稳,所不同的是,现在它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自称该国际人体器官销售网络的中方代表一字一顿地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反悔。她举出几条理由:一、他们已经在这项业务上投入了人力和财力,比方说,他们刚跟沙城一家正规医院定租了一间手术室,预付了订金;接收我的肾的寄主,也已经物色得差不多了,同样已跟他们确定了交付肾的时间。二、我们是签了合约的,一旦我毁约,他们就要严格按合约向我索取赔偿,合约就是法律,我不能违规。她竟然提到了法律,令我洞悉这支队伍的高深莫测。我乱了方寸,挂掉了电话。手机马上又响了起来。我满脑空白,关掉了手机。等第二天早晨我战战兢兢地将它打开,它准确无误地响了。难道他们专门派了一个值班人员来对付我的临阵脱逃?我接了。还是那个女人,还是那种沉稳、练达、坚决的声音,还是那一套刻板的恐吓。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口。我终于下意识地问,如果要赔偿,价钱是多少?女人说,五十万。
大概数十年前那些被抓进毒气室的犹太百姓就是我眼下的样子。我感受到了,千真万确,我感受到了那种生命被他人之手扼住的窒息。如果我把手机卡销毁,将手机扔进水里,埋到地底下,他们能不能找到我呢?我恍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鉴于对他们的无所不能已深信不疑,我想到这是行不通的。什么都行不通,只有俯首称臣,缩紧身体等待一副冷飕飕的手术器械轰然降临。我用水冲自己的头,想使自己变得足智多谋,结果我的脑袋越来越空洞。我去学院高大的教室里讲课,发觉自己竟然自卑到细声细气的地步。本该被我俯视的学生们现在组成了一座坚硬的钢铁森林,我有向他们呼救的冲动,但知道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耻辱,我只能故作镇定。
神!无所不能的神!我想到这句颂词。现在它是那么的经不起推敲。生命终究掌握在人的手中,通常这个掌握的人是自己,当这个自己一步走错,它便成了别人手里的棋子。我无从揣测那个掌握我的人此际的心态,这证明我的课题是可笑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个魔域,他人无法抵达最实质的细枝末节。我瘫软如泥,感觉整个沙城都被掏空了。
10
庆幸的是,平静还是到来了。在预定的取肾时间到来的前一天,我获得了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卖肾成功后必将出现的许多美好场景激励着我。我想起那句话: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如今我将要成为这句话的忠实践行者,幸福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家人,这不是我起初一再想到看到的结果吗?刑场已准备就绪,静候我去剪彩,该做烈士就去做吧。
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应该铭记的日子:2007年9月8日,我一贯静态的生活鼓声大作,我躺在沙城西部的那家医院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身体部件。我记得那天早晨,我特意坐在电视机前思绪纷乱地观看早新闻,以缓解一波接一波的紧张情绪。天气依然热得不行,这地方一年中有半年都是夏季。中东地区还是战事不断,沪深股市一路疯狂飙升,新增股民层出不穷,享誉世界的歌唱家帕瓦罗蒂的葬礼,于他家乡莫纳德的教堂举行。在一个叫做沙城的炎热的中国小城,那个叫覃伟的年轻谢顶男人将惶惶不安地卖掉一个原本属于他的肾。有什么不妥呢?没有,所有正在发生的事都是有依据的。我特意穿了一件长袖衣服,大汗淋漓地将身体扔到了阳光下的马路上,紧接着又将它摆进那家医院的手术台。
一个人我都不认识,还好没有外国面孔。从医师到护理人员,甚至那个负责当日事务联络的器官公司的业务员,看起来都是本地人。一大堆的本地面孔转移了我的部分恐惧,令我稍稍觉得,这一天和任何一天没什么不同。进入手术室的一瞬间,为了标榜我的清醒,我刻意向身边的护工问了一个不必要的问题。我说,我的外衣搁哪儿了?麻烦帮我存好,不要待会儿我出来的时候没衣服穿。我惦记着衣服,说明我不想让任何熟人知道我的这次卖肾行动,要知道,几个小时后,我的腰部将多出一个口子,如果需要我自己回去,光着上身走那么长的一段路,难保天机不泄露。
护理员只是象征性地笑笑,把我的话当成一种闲聊。稍后,麻药的劲上来了,除了脑袋,我的身体几乎都失去了知觉。有一阵子,我听着刀具切割肌体的有节奏的沙沙声,有点恍惚。我宁愿相信这声音来自别处,隔壁或梦境。后来,完成手术的医务人员解散,先前的那个护理员把我推进准备好的单人休息室。接下来的三天里,我躺在那间几乎密封的小房间里,醒过来睡过去。在此期间,那个龅牙的器官公司业务员来过两次,一次是来询问我的银行账号,另一次是来向我展示已经将尾款存入我账户的存款凭证。我给妻子打了两次电话,一次是在术后,我告诉她我刚刚抵达北京,另一次问她需要我从北京给她捎回什么礼物。这么突兀的一次失踪,是需要设计的。妻子麻木不仁,对我连续三天的失踪不加怀疑,她从来都只关心她自己。
11
妻子对他人的漠视由来已久。在我们认识的起初,我对她的这个毛病简直无法容忍。不要妄想她记得你的任何倾诉。有一次,我正犯着严重的胃病,之前我郑重其事地向她转述医生对我的嘱托,说我这段时间忌吃辛辣食物,但那个周末她兴师动众地打车走了不下十余里地,要我陪她去城西新开张的一家湘菜馆吃饭。她并不是个爱吃辣的人,那次只是心血来潮。因为你已经向她倾诉过这种禁忌了,再重复一次,总是伤脑筋的。通常情况下,你只能选择不再倾诉——我想,稍有全局观的人都会这样做。只好奉陪。这其实是小事,胃病正盛时,吃点辣的也并无大碍,关键她总是这样,让类似的疏忽充斥了我们的生活,这样我就得日复一日地承受那些细小的委屈。悄悄地承受,她永远蒙在鼓里。
我的母亲是不喜欢穿杂色衣服的,她常年只穿黑、白、灰三种素色,妻子却经常冒出灵感,给母亲带回一件花里胡哨的东西:一条斑纹围巾、一双红袜子、一只少女才有资本戴的毛茸茸的镶珠头箍。母亲每次都只好故作欣喜地笑纳,过后将礼物塞进衣柜最底层,趁她不在的时候跟我揶揄。我记得我应该向妻子透露过妹妹如今的窘境的,大而化之、很含糊的那种透露,但每次她同我提到妹妹的时候,总一副嫉妒的口气,好像妹妹是个六亲不认的达官显贵。也好,反正妹妹这么好面子,是绝不能容忍不够亲密的人知道她过得一败涂地的。
好就好在,在妻子对他人熟视无睹的性格的另一面,是她开阔的胸襟,不记得有人恩宠过她的同时,她也不会想到也许谁正记恨着她。所以我对她的所有不满都会在她一以贯之的嬉笑怒骂中自行风化。从这个角度说,我与她的生活,总体是融洽的。我没有办法不爱她,她也爱我,这一点毋庸置疑。
这个夏天的9月,我最急于要掩饰的,是腰部那条新鲜的伤疤,这种掩饰极具难度,特别在一个与你朝夕相处的人面前,那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周旋。最复杂的周旋在床上,我只能向一方侧卧,以防止伤口的碰压,还不能光着身子睡,不能洗澡,原本周期频密的做爱要戛然而止。这些都是值得妻子警惕的。谢天谢地,她麻痹大意的个性降低了这一难度。
妻子轻轻打着鼾,睡在床的里侧。有时她会在梦里发出轻笑。她总以为我和她一样睡得很沉,会在睡梦间猛地将腿搭到我的腹部,不知轻重。我不得不尽可能地往床边挪,以减少突发的撞击和挤压。也并不是我需要对她保持警惕才不敢深睡,失去一个肾给我带来的新鲜体验令我的思绪一刻不能停歇。我变得特别有精神,尤其听觉,倍加灵敏。窗外的木棉树、椰树,以及那丛茂盛的三角梅,在有风吹过时,枝叶互相擦撞,连这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夜深人静时分,我常坐起来,比往日更长久地凝视妻子的身体。刚刚过去的这场称得上壮烈的行动提升了我对自己的认可度,现在我觉得,眼前的这个身体再过丰美,我也是可以匹配的。
还是被妻子觉出了异常。9月13号的夜里,她在入睡前突然瞪大眼睛问我最近几天是不是在瞒着她做什么坏事,否则为什么老是神神鬼鬼的,而且总深更半夜才回到家里。我举出一堆事先准备好的理由,如课题正进入尾声需要全力以赴,她有所怀疑地沉默了一刹那,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你有外遇了?这个时候她的轻蔑对我非但不是打击,还是种救助。我让她对我的自卑一目了然,黯然说,我这个样子,想有也有不了啊?她心满意足地倒头睡去。
可总是要做爱的。离预期的拆线时间还差五天的17号,她忽然来了兴趣,情绪高涨地爬到我身上。往日,我的旺盛使她从不必在这种事上主动,我几乎不曾见识过她主动的样子,这夜的她令我觉得新鲜而刺激。豁出去了!最终我对自己说。需要捂着紧裹在上身的背心,并努力维护伤处,才能完成这样一次两情相悦。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我使她得到了应有的满足。这一次的体验,使我因失去一个器官而陡增的惶恐减弱了大半。但为了防止这样的挑战在拆线前再次发生,我用心编织了一套谎话,搬到办公室去住了几天。
12
撇除因失去一个肾而带来的诸多怪异情绪,这个9月我称得上兴高采烈。十六万人民币像一块沃土,令兴奋从我心田源源不断地滋生。我从未拥有过这么一大笔钱,对我来说,它无疑是笔巨款。在我过往的生活中,资金存额高过一万的情形都不会出现。通常我的工资刚好可以用来维持日常的家用,稍有余头,很快成为妻子实现物欲的可怜工具。不出意外的话,平时我能支配的钱不会超过五百块。十六万与五百块相比,是多么宏伟的一种落差。现在这笔巨款可以任我随心所欲支配了,幸福、踏实、笃定的感觉铺天盖地浸漫在我的身体里,使我一刻都坐不下去。我瞪着那张为此次交易专门开设的银行卡,往往喜难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