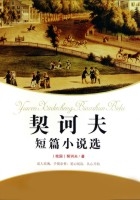冒臣没必要在阿龙这样的富翁面前装有钱,他这一刻很坦率。大概觉得这段谈话已变得需要策略,策略需要时间,阿龙建议冒臣跟他去茶餐厅的办公室聊。冒臣没有异议,他们便步行去了。
一年了,冒臣还是第一次走进阿龙茶餐厅的办公室。房客与主人要保持适当距离,冒臣有自知之明,所以即便阿龙多次邀请他来这里喝茶,他都婉言相拒。
阿龙把功夫茶具推到桌中央,呼唤外面的服务生拎过来一壶茶,之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展示他的沏茶技术。他将主茶杯置于茶具底盘中央,又将两只小茶杯捻进主杯,接着拎起茶壶向里倒水。热腾腾的水汽迅速袅袅升起。阿龙张开右手拇指和食指,伸向已泡进沸水里的茶杯,两指快速捏合在杯沿,使之在水里旋转。冒臣看得瞠目结舌。阿龙完全领略到了喝功夫茶的精妙,他是在享受其间的每一个步骤,包括洗杯子。冒臣却觉得这些前奏是多余的,甚至用那么小的一只杯子喝茶,也是不科学的。他是大口喝水的人。看来阿龙比他更注重形式。也许他是在享受制造形式而得到的内心的安逸。
“我真的住不了那么久。”
“不谈这个了吧。喝茶就喝茶。”
冒臣很欣赏阿龙的淡定与深沉。跟这种大智慧的人打交道,就像沐浴一场春雨。以冒臣对阿龙的了解,他最终会用他的委婉让冒臣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冒臣知道阿龙其实永远是成竹在胸的,只不过他深谙人与人交往的艺术,这不是狡猾,而是一种涵养,况且,阿龙是不强求结果的,他看得更高、更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舍弃某些小利益。那个被曝光的旅店,以及没有被曝光的同样的旅店,他们的主人稳坐屏幕前,洞察着每一个房间里的一切,但通常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销毁,最终被他们深邃的记忆消化掉,对那些画面的想法从来都没出现过一样,最终销声匿迹,他们永远平和地笑对客人。阿龙的消化能力无与伦比,想必如此。只要冒臣装装傻,阿龙不会强求他一定要在那高档客房住多久。问题是冒臣觉得在聪明人面前装傻会使对方在心里轻看了自己,所以他还是自觉点好。
“要不我就住一个月吧。你吃点亏,算是帮了我一个忙。”
“你想住一个月,就住一个月。喝茶,我们不谈工作。嗬!”
很简单地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谈判。聪明人和聪明人在一起,就是省事。冒臣一点都不想装,告诉阿龙他不习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茶,还是叫服务生给拿个大杯子来。他用大杯子喝,阿龙独斟独饮。
“大口喝有大口喝的好。抿有抿的好。都好。”
他们安静地对坐着,水流向茶杯的声音、进入喉道的声音、在茶中荡漾的样子,成为房间里的主要内容。冒臣心里惦记着要去给茹晴协调“演出”的事情,有点坐不住,但跟阿龙这样的人打交道,说走就走,是有失分寸的,他决定在这里坐一个小时。但心里却慢慢就焦躁了。接近傍晚了,从茶餐厅外面的马路上传来更琐碎的市声。冒臣望着阿龙的笑容,竟然脑子就变得空灵。
有那么一会儿,冒臣的神经质又犯了。他望着宠辱不惊的阿龙,突然就想起了那些从未曾搜查出来的“摄像头”。他和阿龙的异同之处也许在于:他们都有非凡的领悟力、洞察力;但阿龙兼具强悍的消化功能,冒臣这方面的功能还欠火候。
冒臣不由想象阿龙可能日复一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眼睛一眨不眨地观赏冒臣所有的私密行为:他裸睡到忘我时四仰八叉的样子,跟自己生闷气时错位的五官,甚至他愤怒而烦闷地寻找摄像头失败后的沮丧表情。冒臣想,如果阿龙真的看到过他那些不能示人的弊端,而现在他又在看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冒臣,那么他的淡定真是太恐怖了。阿龙现在正感受着的,是不是一种观赏猴子表演时的欣快感觉?冒臣突然觉得自己很虚弱,很没有底气,并对阿龙满心排斥,对自己亦心生厌恶。
6
冒臣给茹晴打电话,详述他正在筹措的方案。茹晴如释重负。但她心里还是不踏实,不是对接下来的“演出”没有信心,而是由于内疚。这场蛮横的躲避行为,促使她反思自己四年如一日对父亲的欺骗。她觉得自己活得太阴暗了,对父亲太残忍了,她必须用某种方式给父亲补偿,否则她的内心将永世不得安宁。怎么补偿呢?她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等稳妥地见到父亲后,火速带他去医院,好好看一看他的病。这就涉及钱的问题了。那得花多少钱啊?看来她比从前更需要钱了。
她在电话里唠唠叨叨地跟冒臣说着这些,令冒臣欲火焚身。她无疑是在暗示冒臣在最近的时间里多帮衬她几次生意。由于某次巨变的发生,去年以来,她已经很难有机会去做生意,而冒臣绝对成了她的救命稻草。他是她如今最稳定、最可靠、最大的收入来源。她必须依赖于冒臣。
去年五一黄金周,当时还在做着正常小姐的茹晴跟一个本地客人出台,客人自驾车带她去东部沿海疯玩了五天,回到广州后,茹晴就失去了继续做正常小姐的可能。真没想到,这个表面和善的中年男人竟然是黑道上的。这一次长时间的交易使他迷上了茹晴。他不由分说要茹晴当他的固定情人。茹晴起初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觉得这人长得丑,心里不愿意就拒绝了他,继续做她的正常小姐。这之后她的生活就被钳制了。那黑道男人当然不会真正把一个小姐当回事,他当时是喜欢茹晴,但能让他喜欢的小姐多着呢,愿意向他俯首称臣的小姐也有的是,所以他把对茹晴的喜欢转化成刁难、折磨,也只是分分钟的事。他很快向茹晴发出通告:你不是嫌弃我吗?那好,我不要你了,就是以后你跪下来舔我的脚指头我也不会要你,但同时你也别再想干这一行。他跟广州所有暗中设立异性服务的娱乐场所、酒店、宾馆、饭店一一打招呼,让这些地方都不敢接纳茹晴。考虑到茹晴可能会离开广州,去别的城市发展,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彰显他的能量,他威胁茹晴:你就好好给我在广州待着,哪儿也别想去。我想搞你的时候,你就马上给我爬过来;我不想搞你了,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别动。就这样,茹晴再想通过男人赚钱,已经很难。遭遇钳制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茹晴想到过要趁机痛定思痛,去做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可她试了几个月,发现自己先前大学里学的专业因为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实践,已经完全荒废了,她成了一个根本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出于周全的考虑,她一边在一家小公司打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以便慢慢学习、积累生存技能,与此同时,她暂时仍在伺机寻找男人。现在她寻找客人的途径很有限,一方面去网络聊天室瞎聊,另一方面就是去娱乐场所穿梭。两方面都有难度。在聊天室,聊成生意的概率很低,那些虚无的男人好像更沉缅于聊天的快意,真叫他们出来,却打着哈哈不见了;有些聊友已说好跟她在哪里见面,等她在约定地点等了半天,连个鬼影都没等着。在娱乐场所穿梭,成功的概率就更低了,你怎么知道哪个男人想嫖,哪个不想?他们脸上又不刻字。更何况黑道男人像个符咒悬在她的心里,她根本不敢在那些地方久留。
这就是眼下茹晴在广州的命运。她第二次和冒臣交易的时候,就把这些事告诉了冒臣。那一次冒臣迅速想起了初遇她的那一天她被那个男侍者拦住、他们激烈的交谈。想来她如今的小姐事业的确阻力重重。茹晴说,她现在为了每月获得足够寄往家里的钱,简直是勒紧了裤腰带。有些时候,她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于,在好些个月末或月初,当庄瀚财发觉她寄钱的行动越来越拖沓后喝令她回烟城时,仍未攒足“月供”的茹晴不得已去向以前的姐妹借钱,到上个月,她身上已经背了将近两万的外债。
了解茹晴境遇后的冒臣心中戚然。他本来就陷在茹晴的身体里无法自拔,她的这些背景都快使他爱上了她。他认真而小心翼翼地为她考虑,最终决定每月至少找她五次。按他自己的生理需要、对生活的规划,其实最多一月找她两次就可以了。
他一次按市场价的较高额度给她六百,也只能这么多了,否则他承受不了。其实就是这样月月付出,他也已经有点撑不住。他现在月薪四千多,加上偶尔干点私活,平均一月也就挣六七千,把收入的一半扔到茹晴身上,对他来说确实是种极大的负累。但他不想让茹晴看出她成了他的负担,他从来就在她面前表现得很阔绰,说起来这真有些奇怪。
有几次,冒臣几乎要对茹晴说,要不然,你就嫁给我算了,这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你就不再有经济困扰。但他还是自知地把话咽了进去。让茹晴嫁给他,这对她来说,是个过分的要求。她其实是个十分独立的人。尽管身陷绝境,那些理想还闪烁在脑海中。她要是现在突然放低自己,先前对自己的出卖就变得既滑稽又盲目。
听完茹晴的唠叨,尽管冒臣身体里满是冲动,但他克制了自己。已经是周一了,这是工作最忙的一天,何况他还要尽快协调好“演出”事宜,做那种事情不能不分时机。
“我明天找你吧。明天、后天,都找你。”最后他用一个承诺平息茹晴的焦虑。
“那谢谢你了查哥。我等你电话。真的,我特别特别地感谢你。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
冒臣听出茹晴的声音里有哽咽。或许还有凄楚。
上午开工作例会,主任宣布总部的通知,说接下来公司要开始研制一种新型橱具,这表明这一周冒臣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画那些没劲的设计稿,也许还要加班加点。冒臣抽空给几个在广州混得还不错的白领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助他一臂之力,竟然没有任何收获。他只好把那个事暂先放下,安心去做工作上的事。
入夜回到住处,冒臣看到庄瀚财已经早早上床睡了。茶几上有一盒撕开吃掉半盒的饼干、一只喝空了的牛奶袋,庄瀚财今天可能没有出门。冒臣轻悄站在庄瀚财房门边,借着厅灯的光亮打量庄瀚财。他背对门蜷曲地侧躺着,无声无息,像一个人被遗弃的问号,孤独、僵硬。冒臣深深吸了两口气,小心关上房门,兀自去卫生间冲凉。
等他用毛巾擦着头发回到客厅,一种异样的感觉莫名其妙地令他感到压抑。先前开着的厅灯不知怎的灭了,整个屋子里没有一盏亮着的灯。黑暗使房间变得狭小。冒臣第一个从心里蹦出来的意识,是那些可能在别的空间里窥视他的目光。现在那些目光的主人已经不满足于空洞的窥视了,他们钻进了他的私密空间,又在倏忽间遁身而去。也许他们想用这一行动诱使冒臣去想象一场灵异事件,从此他的精神世界不得安宁,直致失常。
冒臣感觉到心跳加速。他摸索着走到庄瀚财的房门外,拧开门,定神凝视床上那团沉寂的身影,转身走到自己的房间。
那些面色沉静,却设法使自己洞悉一切的出租屋业主,他们的脸闪动在冒臣的脑海中,面容糊涂,目光深邃。他看到了被迫成为AV演员的那对可怜夫妇。还有多少人曾经扮演了这种角色,却要终生蒙在鼓里?某个监视器、针孔摄像头,它们是否真的存在呢?冒臣的心神再也无法平静。他数次从床上坐起来,惊惶地抬眼审视卧室四壁。没有针孔摄像头应该发出的微红的闪光。冒臣在电子商品市场见过那些被称为针孔摄像头的东西,它们再小,也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那么这屋里显然没有他所见过的那种摄像头了。可难道冒臣不是个对摄像产品一知半解的人吗?没有亲眼看到证物,就说明它们真的不存在?人们总会因为没有亲眼发觉自己正被观察的证据,从而沾沾自喜,就像庄瀚财,总是误以为在他一刻不停的粉饰之后,他就成了人们眼里的强者,事实上生活山重水复,他蒙蔽着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别人蒙蔽着。总有一些你并不能发现的眼睛,在不知名的异度空间里盯着你。难道不是吗?
有一会儿,恐惧、不安、疑虑彻底攫扼了冒臣,使他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房间突然变得空落起来,仿佛他被抛掷到了旷野之上。他毛孔收缩,觉得四周寒气逼人,必须马上进入躲进一个狭小的空间,这才安全。他跳起来,一个猛子扎到了床底下。
似乎真的安全了。头上顶着床垫,旁边还有两个他的包拥护着他,使他视野狭窄到最低限度,由此心胸倒顿然开阔了。他轻吁着气,感受着终于到来的平静。
在那间阁楼里,他很多次用这种方式平复心情的:躲进最狭小的空间,床底下、衣柜里。有一回,他竟至连着一周都睡在床底下。十七年来,他其实一直在自己的私密空间里藏匿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效果往往是明显的:他之后不再草木皆兵。
渐渐冒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躲藏是多么不必要了,理智回到了他的身体里。像从前每次的结局一样。他在心里自嘲着,回到了床上。但是并不能就此沉沉睡去。他只得空躺着,权当闭目养神。
半夜里,冒臣被一阵尿意弄醒,迷迷糊糊地去卫生间。打开灯他霍然看到庄瀚财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与往常冒臣与他目光相遇后他必然变得矫饰不同,这个夜里庄瀚财脸色虚青、神情落寞,甚至于还有几缕仇恨在他眼中摇曳。他终于放弃装蒜了,是病痛复发了?还是身体里的病魔和女儿的顽固躲避终究瓦解了他的意志,他不再把逞强当成人生的必须了?
“怎么起来了?庄处。”
冒臣满腔同情地望着这个自行放弃了伪装的人,想到这种放弃对他来说应该不啻于一场地震。
庄瀚财像个聋掉、哑掉的人,对冒臣的善意问询置若罔闻。他就那样纹丝不动地端坐在漫漫长夜里。
“睡去吧。别干坐着了,坐坏了身子……”
冒臣都快要说出自己对他病痛的洞悉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把更多、更温暖、丰富、深入的安慰之词说出去。
庄瀚财被点穴了一样,仍怆然坐在那里。等冒臣从卫生间返回,发现他改坐到了地上,却依旧是一具如同被掏空的躯壳,只是更加萎靡。
“我们不用想那么多,只当是什么都不知道。烦恼就是因为想得太多……”
冒臣欲言又止。
庄瀚财突然抽搐了两下,接着身体的每一处都疯狂地动了起来。他箭一般从地上射起,像被狂风刮开的破了膛的干八爪鱼,舞动着四肢,发出一声大叫。
“龟孙子你瞎扯啥子啊?信不信我揍你。”
冒臣猝不及防,下意识后退,旋即安心了。他终于变得暴跳如雷,这说明他恢复到了他的常态,那么他就不用担心他在“演出”来临前做出什么傻事了。让他泻泻火吧,这对他、对茹晴,对大家都有好处。冒臣笑盈盈去搀扶他,将他往卧室推。庄瀚财打掉他的手,气势汹汹回到自己房间,用脚踹闭了房门。冒臣把耳朵贴到门上,等不再听得到里面的动静,这才放心离去。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