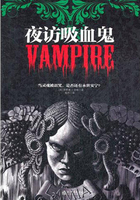正说着她,安霓穿过闹哄哄的食客们向这里走来。那男的并没有跟她一起来,这多少印证了刚才子澈对她的判断,也符合他们对她固有的设想。安霓的外表始终有股霸横之气,在这个下午,她那份气势看着比以前更笃定了。不过走近后他们看到她脸上的肉比以前还坠得厉害,下颌全掉下来了,与下巴几乎形成一条直线。这种坠势,通常只会在四十岁的女性脸上出现。真不知道她是遗传基因出问题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安霓用一种极标准的寒暄语言不留空隙地快速同他们每个人说上只言片语,轮不上他们五人插一句话。很快她回去了。
那个下午从T县回来的车上,五个人变得很沉默。尤其子澈和晓晨,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这数月以来,他们一直很沉默。表面看,谁也看不出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但仔细看就是有问题。你要说有什么问题吧,看着又不像,俩人打量彼此的眼神还是像以前一样温柔。反正他俩的关系有点怪异。
子谦不知道在那个下午车上其他人是不是也在想着安霓,据此观照自身。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是在思考她。他从安霓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影子。尽管他和她性别不同,但同为单身者,他和安霓多少会有同一性。他认为该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了。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大家都必须依据自身的情况,来修正生活轨迹,以便使个人的轨迹与世界和谐共存。
从T城回来的晚上,子谦再次遭遇那个说不清是不是梦的惊险事故。这一次,那种瞬间向下坠冲的感觉更为强烈,即便事情过后的几天里,他也能清晰感受到那种坠落带来的惊悚。他没有上次那么幸运。这次他碰到的是腹部,疼得死去活来,还去医院做了放射,在确诊没造成内伤前缝了六针。后来好些夜不能寐的日子里,子谦对夜晚的恐惧使他忍不住想开着灯睡觉。但他觉得一个男人害怕夜晚是可耻的,就是再怕,他也不能找晓晨或别人来陪他,不能整晚把灯亮着。他要同自己对抗到底。但他又总是会想,要是哪天我撞到的是头怎么办?无疑他很可能会立刻死掉,因为那种撞击力大得不可理喻。
子谦感到力不从心。偶尔他将夜晚的奇遇讲给褚颖虹他们听时,他们开玩笑说,他已被灵异附身,最好去寺庙求个佛像挂在床前。那显然是无稽之谈。他比谁都清楚,他遇到的是精神上的困顿。能够解救他的人,只能是他自己。他需要把他夜晚的颠乱当做他的人生首要难题,尽一切办法歼灭它。
5.他们的设想之外
晓晨带回安霓的一个坏消息,这消息使他们大吃一惊。安霓去了T县后,就只有在市晚报当编辑部主任的晓晨能直接获知她的消息。但五年前就不一样。五年前,他们五人,加上安霓,都在一个剧团工作。那时褚颖虹在剧团唱青衣,比褚颖虹大一岁的安霓唱老旦,子澈是全团最有灵气、最年轻的花旦。他们三个男的里面,只有徐峻是演员;晓晨是编剧;子谦干的是边角工作,每当有演出活动,他先行将消息用各种形态的美术字公之于众,即所谓的美工。那年M城文化口发生了一件大事,说它是大事,只是针对他们这些底层岗位上的小兵小卒而言的,在他们这层之上,那是件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情。其实无非只是文化局换了个新局长。这人是上面下来的,下来的目的是在基层这口五味俱全的火锅里涮上一涮,镀一层基层岗位领导经历的金,接着他再回到老巢升职。他只当了一年局长,第二年就走了,却把文化局所属几个院团搞得鸡飞狗跳。这局长一上来就抓些无足轻重的事,自以为很有创意,对于剧团,按理说他一个间接领导不该去管那些细节,但他明文要求每个人都要按时上下班。这个要求极其不切实际,剧团的事都是一单一单的,怎么按时上下班?比方说某段时间下乡演出,一演就演到晚上十二点,演员再从乡下回到自己家里,都两三点钟了,你能叫大家第二天按时上下班吗?再比如章晓晨是个编剧,写东西的人必须被赋予自由,这样他才心态放松,你让他成天惦记着哪个点准时去上班,他写个屁啊!
有个情况那局长没想到,那也是他的愚蠢之处,稍微体察民情的官员都应该想得到那种情况的。什么情况呢?就是剧团很多人根本不在乎这个饭碗。如今戏剧不景气,像他们那种生僻剧种更面临生存绝境。那时他们的月工资五百来块,比政府补贴那些下岗工人的补助多不了多少,演出一场加十块钱演出费,一个月正常收入不超过七百,想活下去的话,大家都得去自搞创收找外快,事实上许多人也正是这么干的。这只饭碗实在是形同虚设、轻若鸿毛。被那局长折腾了几次后,子谦和子澈首先辞职,子谦在M城四个区各开了一个打金店,子澈自费去星海音乐学院读书,三年后毕业回M城当音乐老师。晓晨身出名门(他爷爷几十年前是M城初建市时的市委领导人之一),原本他是因为在剧团干编剧,任务少,行动自由,有大把时间供他搞热爱的纯文学创作,他这才待在剧团的,那局长那么一搞他就很快疏通关系调到了晚报副刊部。只有褚颖虹和徐峻没动辞职的心思,他俩太爱这个剧种了,从某个角度说,俩人对艺术有种神经质的爱慕,这种精神层面的挚爱所形成的共同语言也是他俩棒打难散的原因。而安霓呢?在这个剧团,只有她是个最不称职、最无戏剧前途、最笨的演员。但作为一个来自乡下的姑娘,她走到这一步,说起来也是干部编制,这已相当不易,所以这饭碗对她来说极其宝贵。她坚定地待在剧团,直到后来团领导一致决定把这个女混混开掉。
那次晓晨带回的是安霓得病的消息,说半夜里安霓突然不行了,救护车连夜把她送进了市医院。他们推测过安霓的种种发展可能,相信她的未来绝不会跳出他们对她的断想,但就是忽略了她可能会生病。先前他们对她进行设想的动力和依据是她讨厌的性格,忘记了她是个凡人,有着和大家一样渺小、脆弱的身体。平常谁会把急病和一个正当壮年的人联系在一起呢?
安霓得的是急性肾小球肾炎,这是他们随后探听到的。她就住在M城最热闹的医院里。在晓晨告知他们这件事时,她已住院三天。
天知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五人竟不约而同地建议,去医院看望安霓。褚颖虹甚至紧张而内疚地瞪着其他人,说,是不是我们经常骂她,把她骂病了?阿弥陀佛!真是罪过罪过,菩萨保佑她吧。子澈也叹了口气,说,我们以前对她太那个了,毕竟她曾经做过我们的朋友,毕竟人活着都不容易,毕竟大家都是小人物,毕竟——唉!以后说她的话不能太损了,都得注意点,听见没有?至于他们三个男人,心里其实并无太大波动。子谦用搜索引擎在网上查过了,肾小球肾炎不是什么绝症,在医院躺几个星期就会康复,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时值仲夏,M城热得要命。这不打紧,天气还干燥得叫人胆战心惊。子谦甚至觉得可能要地震了,因为M城郊区就有一家地质公园,向人们昭示亿万年以前,这里曾是一个火山口。也不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刚刚过去的一年,这个地球上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海啸,死去之人数以万计。这当然是子谦自己吓唬自己,只能证明他太容易浮想联翩。五个人花了两个多小时,四处选购探望安霓的礼物,在很快到来的后一天中午,心情沉重地来到安霓的病房。
安霓抱着两臂,倚坐在床上,两只眼睛紧紧盯住自己的脚尖,一看就让人觉得她在盘算着什么。这个样子和她在他们记忆中的一贯形象特别吻合。见他们五个人来,安霓身体没动,却夸张地笑了。嘴咧得特别开。子谦看到了她一大列鲜红的上牙床。一般情况下,肾病患者的眼泡会浮肿,她竟没有。你们来啦!她用一种听不出感情色彩的语气笼统地给五个人打了一句招呼。褚颖虹上前摸摸挂着的吊瓶,手顺着橡皮输液管撸下来,最后搭在床帮上,一屁股挨着安霓的脚坐到床上,开始用一种前嫌尽释后的热烈语气向安霓嘘寒问暖。其他人也没话找话,尽可能安慰她。安霓总是言简意赅地应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没事。“我没事儿,你看我像有事儿的人吗?”“我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儿,我要是有事儿那多不像话啊!”他们听得出她刻意而为之的幽默,她尽力想使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类似电视里那些讲着流利北方方言的小品演员的俏皮劲,只可惜她只能克隆那类小品演员的腔调,却无法使自己的“幽默”像金子一样掷地有声、特别地有质感。聊着的中间,安霓客气地怪他们给她买的礼物,声称她的胃那么小,怎么撑得下那么多东西,不如他们待会儿拿回去好了。不多久她先行切断了聊叙,另一只没插吊针的手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听得出来,她在使唤别人做什么。给一个人的电话里,她说过这么一句:“你怎么回事儿啊?不就叫你办个事儿吗?你他妈的给我快点。”给另一个人:“呦!没看出来!您架子还挺大的嘛,我得找辆凯迪拉克去接您?”第三个:“当然啦!你看着办行吧?我这儿还有一堆人呢,咱就这么说。OK?”
在接下来半小时之内,来了三个男人。一个二十三四岁,一看就是司机之流;一个矮胖子,也不超二十五岁,笑得特别没有分寸,也就是说,他的嘴从头至尾都会咧得开开的;还有一个年纪比较大,三十五到四十之间,拎了个公文包,不怎么会讲普通话,很谨慎和礼貌,显出一种让人摸不透的谦和。
等三人都到齐后,病房里出现一种奇怪的气氛。首先他们五个人对这三个陌生人不知道说什么,于是他们这五人不再说话,纷纷坐远。这样那三人和安霓组成了一个与他们五人界限分明的小团体。但那三人竟然互相并不相识,彼此间也笼罩着一股尴尬气氛。他们五人无法确认那三人和安霓的关系。反正接下来的时间变成了安霓的独角戏。她拿起年纪最大的那个男人提来的饭盒,打开了一边吃一边远远告诉大家,她最喜欢吃的就是手上这份烧麦和北方花卷。吃完了指着他们五人先前放在桌上的礼物,翘着兰花指说,他们给她买的营养补剂什么的,她是不爱吃的,她又没七老八十,吃那些玩意儿干什么?要不给那两个男孩分分算了——她声称那两个年轻些的男孩是她“弟弟”。
到此他们五人才发现,安霓除了习惯性地发挥了一通她的小精明之外,更主要的,是在向他们示威。她想用这三个好像“招之即来”的男人告诉他们:她呼风来风、唤雨来雨,过着特别滋润、幸福、快乐的生活,以此证明她比他们五人——至少比那两个名花有主的女人要强。那天从头至尾,安霓没看过子谦一眼。
几天后他们五人又在一块打保皇,徐峻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安霓的新情况。徐峻说,安霓根本没得肾病,只是偶感风寒而已。太不巧了,负责给安霓看病的那个医生恰好是徐峻的小学同学,这个消息是徐峻无意中从那小学同学那儿得知的。那同学说,他最近有个女病人特别好笑,可能和单位领导发生点矛盾,就称病来住院,其实最多只是感冒罢了。又说那女病人找她开单,显然是想报销的时候多报点医药费。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安霓,她什么时候都不忘记要多赚点小外快,连装病的时候都把这惦记着。这个道听途说并没有最后确证的消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但稍加思考后,又觉得这相当符合安霓的做派。
五个人都像吃了苍蝇,对安霓的厌恶加重了,继而确定:安霓,这个无可救药的女人,和他们不是同类,他们必须彻底把她从他们的生活中,甚至他们的嘴里,删掉。扑哧!像抹一粒粘在嘴角好久的食物碎屑一样,说抹掉就抹掉。
6.相克?相生?
子谦夜晚的癫狂越来越惊心动魄。那种坠落感时常于深夜降临到他身上。有天夜里,子澈的手机大响,机屏上显示的是子谦的号码。由于已睡着,她没接到这个电话。第二天她回电问子谦找她什么事。他一头雾水。“我找你了吗?”子澈说,“是啊,你昨晚给我打的电话。”他颇不解。“我给你打电话了?”子澈很吃惊。“你要没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上怎么会有你的来电显示?”“不得了!出大问题了,”子谦惊恐地想。现在看来,夜里他会做一些自己无法意识到的事,诸如梦游之类。他和子澈一起回想他们祖上有没有出过这种怪事。就想起,曾经有个堂爷爷是个傻子。难道遗传基因开始在他身上发挥效力了?这么想过后,连子澈也惊惧难当,有两夜彻夜难眠。子谦开始陷入一种持续的惊慌之中。白天还好,有无所不在的市声和各种事情淡化这种惊慌,到了寂静的晚上,他彻夜难眠,被那种惊慌弄得几欲崩溃,且这情形有愈演愈烈之势。他甚至想到看过的那些惊悚电影,他真的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之外,有一个X维空间,它能够将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在最为脆弱的时候吸进去。只不过他每每即将被那空间吸去时,精神中某种潜在的自卫力量及时把他解救了回来。可万一有一天他连这种潜在的自卫力量都丧失了呢?那该如何是好?他实在说不清楚这夜晚的一切。子谦的生活陷入一种隐秘的绝境,夜晚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白天因长期缺少睡眠萎靡不振,满脸憔悴。
唯一可替子谦释疑解惑的,也许只能是医院。他详细、周到地将发生在身上的情形描述给医生听。医生用一种惯用的宽慰病人的语气告诉子谦,依照他的理解,什么事也没有。如果真想得到什么解释的话,他认为,这是一个精神过度紧张的现代人身上发生的一桩常事。他又说如果信不过他,可以去作些相应的检测,机器会揭示所有的秘密,但他认为没必要浪费这个钱。他伸出拳头轻轻击拍子谦的胸脯,开玩笑说:“像你这种正当年的、好脾气的壮男人,要真出什么问题,天理难容。”
姑且相信这个医生吧。为了防止真的被X维空间吸进去,子谦睡前找了根绳子将两手两脚固定住。这样一搞睡得特别不自由,更难睡着觉了。但他坚持运用这种自疗法。情形似乎有所好转,至少他再没撞坏过自己。
当然,他夜晚的这些事情,不是迫不得已,是羞于告诉他人的。这事除了子澈,子谦甚少跟别人说。最多他只是将它扩散到他们的“五人帮”。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子谦夜晚的异状,他首先就要被唾沫淹死了。话说回来,谁没有点个人秘密呢?没准很多人都像子谦一样,困厄于某种私密的烦扰中。只不过在白天,大家都忽略了隐匿于身体里的秘密,或故作正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