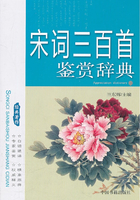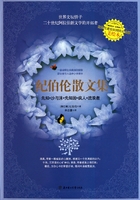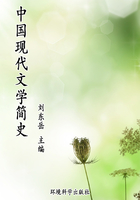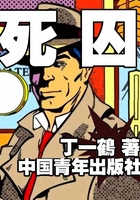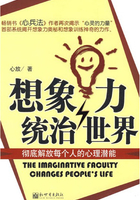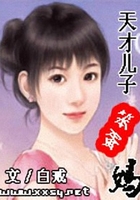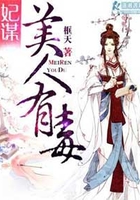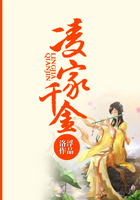$第一节 印度海外作家与海外移民
当代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diaspora。该词源自古希腊语,由表示“通过”的介词dia和表示“撒播”的词spora组合而成。牛津英语词典认为,diaspora是指公元前538年犹太人被放逐之后散居世界各地非犹太人中间。它也可引申而指世界上任一民族离开母国向他国的迁徙。目前国际学术界往往将一些国际移民群体或某地、某国移民海外的群体称为diaspora。因此,diaspora用来表示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海外移民群体已成惯例,例如,可以把中国的海外移民群体及其后代即海外华人称为Chinese diaspora,把印度的海外移民及其后代称为Indian diaspora,把日本的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称为Japanese diaspora。有的学者认为:“总之,diaspora强调了一种移民对祖国或家乡(包括祖先家乡)的强烈依恋和归属感,体现了一种终极的情感乃至身份的皈依和认同。这一点在犹太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在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身上体现得也比较充分。实际上,所谓diaspora(或diasporic)情结是从犹太人身上挖掘出来,并推广或套用到其他国际移民群体上的。”
中国学者王宁认为,diaspora一般译为“流散”,也可译为“离散”或“流离失所”,对流散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他说:“时至今日,流散这一术语已经越来越带有了中性的意思,并且越来越专指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所造成的‘流散’状态:从边缘流向中心,然后又从中心流向边缘,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石海军认为:“‘流散’的含义并不是从边缘向中心的移动,也不是将中心文化的价值向边缘地区输送,它是从里到外、从外到里的双向渗透。在小说创作中,拉什迪经常使用‘渗透’(leak into)一词,表示的正是自我身份的杂交状态。”有的学者认为,diasporic writers应该译为“离散作家”或曰“流亡作家”,王宁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流散文学”这一称呼非常贴切地表达了海外作家的外位视角,因为,流动和散居状态正好有助于他们从外部来观察本民族的人无法看到的东西。
关于流散或曰流亡的状态,自称“流亡者”的典型流散知识分子、当代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Edward W. Said,也译作萨义德,本书通称赛义德)曾经在2000年出版的《流亡的反思》中带着无法弥合的精神创伤如此说道:“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由此看来,流散作家的书写状态和叙事内容都是局外人无法真切体验的。迄今为止,由于国际移民越来越普遍,以或痛苦或轻松的移民体验为描述内容的流散文学越来越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关注热点。印度海外作家创作的流散文学也自然成为西方与印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说到印度海外作家,不能不简单地回顾一下印度海外移民的概况。在世界历史上,移民现象由来已久,但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却出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它是随着欧洲掀起的殖民狂潮开始的。时至如今,世界移民还处于现在进行时。根据专家的研究,印度人移民海外有四个高潮,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海外在19世纪30—40年代,由英国、法国、荷兰等殖民帝国组织,移民的身份是契约工(indenfured labors),目的地是西印度群岛、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岛屿等西方殖民地,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祖先就是在这一波移民潮中来到西印度的;第二次印度人大规模移民发生在20世纪初期,它由英国组织,目的地是英国本土,最后却落脚非洲;第三次移民高潮在1923年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也由英国组织,目的地是波斯湾;第四次移民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是印度人的自发行为,这一时期移民的目的地比较分散,但以欧美发达国家、东南亚和海湾国家为主,移民中既有前往波斯湾的劳工,也有前往欧美求学、定居、工作、投资的高科技人才和实业家。这些印度移民中包括了一大批科技与文化精英,当代后殖民作家实力派人物、印度海外作家中的佼佼者拉什迪、维克拉姆?赛特、芭拉蒂?穆克吉、尼拉德?乔杜里、罗辛顿?米斯特利和基兰?德赛等人便是此类文化的精英。其中,奈保尔、拉什迪、卡玛拉?玛康达雅和赛特等人定居英国,安妮塔?德赛及其女儿基兰?德赛等定居美国,罗辛顿?米斯特利等定居加拿大,贾布瓦拉则先后涉足英国、印度,后来定居美国,芭拉蒂?穆克吉则从加拿大迁移到美国定居。以上这些作家均以英语从事创作,他们是印度海外作家的代表人物。
目前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在3000万人和2500万人左右。海外印度人被认为是世界第三大海外移民群体,仅次于分布于全世界的英国后裔和海外华人群体。目前,海外印度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海外印度人分布较多的国家及其具体人数分别是:美国,168万;英国,120万;加拿大,85万;圭亚那,40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0多万;南非,100万;沙特阿拉伯,150万;阿联酋,100万;缅甸,300万;马拉西亚,170万;新加坡,170万;澳大利亚,20万,等等。目前,海外印度人的国际影响力不可忽视,这对印度政府近年来采取双重国籍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不承认独立前移民海外的印度人与印度有任何联系,半个世纪里,海外印度人与印度政府也没有任何正式交往。联系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的纽带以宗教、语言、电影、音乐等文化因素为主。一般而言,海外印度人基本保持着对印度的文化认同,大多数人仍将印度视为祖国,并和印度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印度海外移民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乃至文化影响力不断上升,印度政府一改此前谨慎保守的态度,开始主动接纳他们。很多移民欧美的海外印度人渴望双重国籍,因为,这是打破他们回国投资“瓶颈”的关键,同时也是维系他们对印度文化认同的纽带。自然,这也给印度带来了莫大的利益。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海外印度人受到了印度政府的空前重视,印度学界对海外印度人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例如,1975、1979、1984和1995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先后举办了四次大型的有关印度移民的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印度安德拉邦的海德拉巴大学成立了印度第一个专门研究海外印度人的学术机构即海外印度人研究中心,后来在古吉拉特邦的北古吉拉特大学也成立了另一个相似的机构。为了重新调整印度政府与海外印度人的关系及制定实际政策,当时执政的瓦杰帕伊政府决定由外交部牵头成立海外印度人高级委员会(High Level Committee on Indian Diaspora),专门负责调查、研究海外印度人的历史、现状及印度政府应该制定的相关政策。
2003年1月9日,印度政府在新德里召开了第一届“海外印度人节暨海外印度人奖颁奖大会”。在这次活动的开幕式上,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郑重宣布印度计划实施双重国籍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双重国籍只给予1947年之后离开印度的印度人的第四代后人;双重国籍除保障可以拥有印度护照、不须签证可以随时访问印度外,还可保障印度护照拥有者在印度做生意,购买地产。但印度政府也同时做了一些解释,即拥有双重国籍者不能投票和竞选,不能参军,不能担任某些法定的职位。印度政府经过多方慎重论证,最后决定七个国家的海外印度人可以申请印度国籍。这七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印度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一规定带有某种势利和歧视的色彩。印度的双重国籍政策自酝酿之初到正式实施,一直充满着争议,但是,它毕竟开始正式成为印度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有力地说明了海外印度人地位上升和印度政府格外重视他们的两大事实。
参加第一届海外印度人颁奖大会的奈保尔认为,这次大会及印度的双重国籍政策带有浓厚的“交易成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开放。此次与会者还对印度的世俗化政策等敏感问题提出批评。有的海外印度人士的措辞相当激烈。海外印度人和国内各界人士的激烈批评引起了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对原来的双重国籍政策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其中,印度政府将可以给予双重国籍的原来七国扩展为十八个国家。2004年1月7日,在第二届“海外印度人节”开幕前夕,该修正案通过了总统的批准。至此,印度双重国籍政策完成了法律化的程序。总之,可以这样说:“印度的双重国籍政策可以被视为印度对待其海外移民的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可被视为其改革开放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
赛特等海外作家对双重国籍政策表示满意。《印度时报》是印度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笔者留学印度期间曾经读到该报一则有趣的报道。这就是2005年4月20日的《印度时报》,它刊载了一则题为《维克拉姆?赛特获得“海外印度人奖”》的报道。未署名的记者这么写道:“最著名的印度英语作家维克拉姆?赛特星期二被授予印度政府颁发的2005年‘海外印度人奖(Pravasi Bharatiya Samman)’。海外印度人事务部部长贾格迪西?泰特勒在此间的一个简单仪式上给这位53岁的作家颁发了奖章和证书。出席颁奖仪式的是赛特的家人,包括他的父亲普勒姆?赛特和母亲丽娜?赛特。这一奖项颁发给海外印度人和有印度血统的人,他们在个人领域里成就卓著,并在促进国外更好地且有兴趣理解印度方面贡献突出。赛特在内的十五人获得了2005年的这项奖励。他未能出席2005年1月9日为他们颁奖的‘海外印度人日’(Pravasi Bharatiya Divas,或译‘海外印度人节’)活动。赛特在仪式后说:‘我非常高兴从自己的国家获得这项奖励。’这位在伦敦和新德里两地生活的作家很愉快地说:‘我并不真正觉得身处海外(But I dont feel completely pravasi)。’”“Vikram Seth Gets ‘Pravasi Bharatiya Samman,’” 事实上,按照pravasi的语源,也可将赛特的后一句引申译为“我并不真正觉得是流浪海外”。
2005年的另外一期《印度时报》报道了拉什迪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角逐世界顶尖思想家的消息。这次投票将从百名候选者中评选出五位世界顶级思想家。拉什迪和森获得了提名。这条消息显示,印度公众和媒体仍然将拉什迪和阿玛蒂亚?森等居住海外的作家或学者视为印度人,并以他们的成就为骄傲。
既然印度政府大张旗鼓地实行双重国籍政策,在法律层面认可海外印度人的身份归属,印度国内大多数人对他们表示欢迎,印度学者也就不甘落后,理所当然地将奈保尔、拉什迪等众多海外英语作家视为印度作家进行研究。很多印度学者的印度英语文学研究著述便将奈保尔、拉什迪和赛特等印度海外作家与纳拉扬、安纳德等长期居住在本土进行创作的英语作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正因如此,本书将取得英美国籍的奈保尔、拉什迪、赛特和芭拉蒂?穆克吉等人视为身份独特的印度作家亦即印度海外作家进行集中考察,以探究他们在印度之外如何叙述眼中所见或心灵所思的印度。按照当下学界的说法,这种研究其实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后殖民文学或第三世界流散文学研究。
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印度学界近年来的印度英语文学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动向就会发现,印度海外作家的研究不仅限于欧美英语研究界,它的重镇其实还在印度学界。随着拉什迪的长篇小说八十年代初在西方英语世界突然走红,印度英语文学开始以崭新的姿态集体亮相,西方学界开始对包括印裔流散作家作品在内的印度英语文学刮目相看。这进一步激发了印度的英语文学研究。和此前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立场不同,印度英语文学研究迅速实现“与国际接轨”,即在评价作家或作品时态度更加灵活开放,研究对象开始向海外作家的流散写作看齐,有时候也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则借鉴采纳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可以说,从比较文学最终走向总体文学的趋势来看,当今研究世界后殖民文学、特别是研究亚裔英国文学、亚裔美国文学或亚裔加拿大文学等,如果忽视印度学者的海外流散作家研究成果,将是有缺憾的一种考察。
$第二节 印度海外作家研究在中国
迄今为止,西方、印度和中国学术界都对印度海外作家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西方学界对亚裔英国作家、美国作家、加拿大作家等的集体研究已经在中国学者关于华裔作家的很多研究著述中有过介绍,西方学界对奈保尔、拉什迪等印裔流散作家亦即印度海外作家的研究成果也时有所见,这里不再赘述。印度学者关于印度海外作家的某些代表性著述将在本书第一章进行简略介绍。此处先对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印度海外作家的研究动向做点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