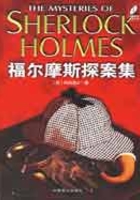4.机遇说来就来了
无独有偶,机遇说来就来了呢!大田高中时的班长给他来了封信,就是这封信使大田看到了农转非户口的信息,看到了脱掉农皮,走出山区的人生的亮光儿。班长在信中问当年的文体委员大田此时在山乡过得怎样,想不想出来工作?自己现在是丝绸厂的厂长,可以帮些忙的。后来大田才知道,这位班长给每个同班同学都写了这样内容大同小异的信,旨在炫耀自己人生得志,他是闲暇时心血来潮随便写写而已,根本就没有想到真的会有同学来找自己解决工作问题的。大田满怀着信心去了,临走时帮容交代,你去见你老同学不能空着手去,人家现在是厂长,今非昔比,家里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你到兴隆乡妈那里去捡几十个鸡蛋给人家提去,空手没有礼,人家会小看你。
大田蹑脚蹑手地进了丝绸厂,问了几个人,钻了几座迷宫样的房子,才在丝绸厂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溜溜光的同学——现任丝绸厂的邝厂长。他大喊了声邝同学邝坚的名字,邝同学偏起戴着墨镜的脸,二指上夹着只冒着烟缕的红塔山纸烟,墨镜后是一双审视着他的眯缝的眼睛,不但没有自己在途中想象了无数次的同学多年未相见的惊喜,而且还有一丝丝陌生。当厂长的同学从头到脚打量着面前这个敢大声武气喊自己名字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这时,大田已经将他写给自己的信递了上去。他脸上镜片上端的眉毛皱了下小声说,雷大田。大田就有些迫不及待,说在农村待不下去了,当个民办教师都被初中生夺了饭碗,你写来这封信算是救我出苦海呢!老同学,我来你厂里当工人吧!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能不再回山里当农民。邝同学没有叫他坐,他自己在他对面的藤椅上坐下了。呵哟!这个厂太难找了,穿过了整个城区,还穿过了火车站,日头火辣辣地照着,比在青牛沱山里肩挑背扛了一百来斤还恼火,拐弯抹角,加上瞎走了的冤枉路,脚早就走得来不起了。大田此时口渴得很,他很希望当厂长的同学能给自己倒一大瓷盅水,白生生的茶盅就摆在漆得红亮的茶几上,可同学却连一丝待人接物的想法都没有。办公室里不断有人往这边看,同学厂长没有听他说完就极不耐烦地说,我马上要去局上开会,你晚上到我家里面来谈。说完,起身就往外走,把大田丢在了办公室。大田回过神来撵上去,已不见踪影。他站在办公室门上悻悻地说,老同学,你家住哪里嘛,我从没去过,我晚上到哪去找你家嘛?这时,一个双手戴着细花布袖套的中年妇女从窗子上伸出个头说,东门剧场,火神庙茶馆商业局家属区。大田隙起耗子牙齿说,感谢你!感谢你!就匆匆地往兴隆乡的老丈母家里去了。
老婆帮容真是想得周到,当年的班长同学现在的邝厂长真的是今非昔比了。自己猜想他对自己态度那样冷淡可能是办公室里不宜谈私事的原因,自己的性急给人家带来了难堪,自己不懂方式方法,人家没有撵自己走就算是给面子了,人家还是念了同学情分的,不然为啥叫自己晚上到人家家里去谈,这就说明是把自己当同学待的,是愿意给自己帮忙的,给自己留了条到厂里工作的机遇的门缝的。大田累都不怕,就是肚子饿了,还是早上四点钟在家里吃的玉米面馍,中午后才赶拢印月井县城的,家里的积蓄给娃儿买了奶粉了,分家修房子又带了些账,车费钱都是帮容平时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难为了老婆帮容了,她跟着自己受了不少罪,月母子连鸡蛋都没有吃到一百个,深更半夜还起来给哇哇叫着的小娃儿喂奶,可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又起了床去烧开水冲奶粉,山里的冬夜好冷呀!她一个坝区长大的女子硬是挺住了,轻脚轻手地做完了这一切,生怕惊醒了白天扛木头累得猪样沉睡的自己。就凭这,大田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进城找到份工作,农转非后把自己的农皮脱掉成为城镇人户口,让母子俩人模人样地过城里人的日子。大田到了丈母娘家,丈母娘眼睛泪汪汪地问他为啥你一个人来,帮容和孙儿呢!大田只好说明了来意。丈母娘给女婿娃煮了荷包蛋、米饭,趁大田饿痨饿虾吃的时候,就把四十个鸡蛋捡好了,装在一个竹子提篼里,提篼里装了酒米,鸡蛋就嵌在白生生的酒米里,赶车或行走时摇晃簸荡不会打烂。大田骑不来自行车,那时到小镇上没有公交车的,他像来时一样走了两小时的路从兴隆乡去县城的,只不过这时是提着提篼,小伙子提个不到十斤的提篼也没啥的,心情好,脚下就生风。大田叮嘱自己用不着慌的,天黑才好去同学的屋里办事,天没黑进进出出的对同学影响不好。时间是恰到好处,大田走拢印月井县城时,天就麻黑麻黑的了。东问西问问到东门剧场火神庙附近的商业局家属区时,天就完全黑了下来,街边的街灯已亮了。大田总感觉自己像做贼似的,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去给人送东西,同样是送东西,走亲访友手上提着东西却是正南齐北的,是越贵重越惹眼见着的都投来羡慕的喜气的眼神儿,不像今晚去同学邝坚家,总觉得来往的人的眼睛都钉子样扎着自己,乜斜着自己,自己手里提着的竹提篼是偷来的或是装着见不得人的东西。如果不是天黑,大田是不敢向人打听商业局宿舍在哪儿,更不敢问邝坚邝厂长住在哪幢哪单元哪楼的。大田冒着胆子终于问着了丝绸厂的邝厂长就住在他爸商业局的三楼上。那时的当官的都坐三楼、四楼,底楼和顶楼都是单位上最弱势的人住的,因为底楼除了耗子多、虫虫蚂蚁多外,还常遭遇排污管道堵塞,粪水污水泛滥成灾把屋子里的家具全漂了起来的霉事情。
俗话说,好手难提二两。大田提着竹提篼终于敲开了一单元三楼的门,门是乳黄色的油漆漆的,是当时门窗较流行的颜色。里面传出来一个干涩的男人的声音,不大,但即使隔着木门传来都透着威严,有些不像邝坚的声音。大田汗水跟着颈脖子流,他小声地有些害羞似的说是我,我找邝坚。门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个矮胖的老头,圆领丝质汗衫衬着一张四方形的脸,头发倒后梳着,溜溜光,露出宽阔饱满的额头,一看就是个干部的派头。大田自觉矮了几分,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的,但他晓得此时自己千万不能因为过于紧张而乱了分寸。他估计对方是邝坚的父亲,这从他们的脸型、眼神上看得出来。他说伯父,我是邝坚的同学,下午我们约了的,他叫我到家里来找他。对方从头到脚溜了他一眼,很快地,有些审视的意思。大田赶紧说,也没带啥好东西来,顺便带了点土鸡蛋来孝敬同学。对方饱满的脸上微微笑了下,把他让进了客厅,倒了杯开水给他说,坚坚打台球去了,你只有等一下,看看电视。他就在褐色的皮沙发上坐下来,屁股生怕将灯光下发亮的皮沙发坐脏了似的,躬着瘦瘦的腰,不敢将背斜靠在沙发上,害怕身上的汗咸味巴在了洁白的针织的布垫上。邝坚的父亲也陪着大田坐着看电视,电视里正放着电视连续剧《渴望》。那阵农村电视还很少,大田所在的青牛沱山村里有一个电视,是供销社配给山区生产队的指标,每个生产队只有一台,放映人员是教书的杨二娃,还是在乡上统一培训怎样开关调台的,好在金河磷矿的半山岩上安有个电视信号差转架,直对着青牛沱河沟,否则有电视也收不到信号的,那时还没有卫星电视。边看电视,邝坚的爸就与大田拉起了家常,大田自然就摆到了自己的老汉儿是铁器社的铁匠,是城镇户口,邝同学来信说自己来城里谋生他可以帮忙,自己想如果以接老汉儿的班为名先农转非然后招工进城不知可不可以。邝坚的爸说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的老汉儿我认识的,外号雷大手,二十年前就在我的铁器社下面。人很忠厚的。他的手长得比一般人大,手劲也大,打铁的手艺特好,动作麻利,大家就称他雷大手。跟我两个处得相当不错的,改天你叫他进城就来耍。
久不见邝坚回来,那阵还没有传呼手机什么的。邝坚的爸开始打呵欠了,大田傻傻地坐着。邝坚的爸说,说起来都是熟人,邝坚答应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等他回来我跟他说叫他马上帮你办,你把你的出生地、户口籍贯、家庭情况都留下,我乡镇局下面有个饮料厂,届时进个人是没问题的。大田心里陡然升起股暖流,眼流水就蚯蚓样爬了出来。活了二十多年是第二次听见关系着自己前途转变的话呢!第一次是前几年谢老师叫自己准备准备去当代课教师的话,第二次就是现在了。这次的感动程度是远远超过了上次的,上次只不过是当代课教师,与这次农转非进城工作是没法相比的。大田本是一个爱感动的人,每当春风唤醒山花,瑞雪飘落树丛等自然景观降临,触景生情的他都会眼睛湿润的。蚯蚓样的眼流水在脸上蠕动,大田喉咙硬硬地说,伯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对我这么大的恩情我该咋样报答你呢?邝坚的爸若无其事地说,不用不用。大田在邝坚的爸拿出的纸上写了情况,足足写了满满的一页,邝坚的爸用笔呼哧一声勾了大半,说你下次来填个招工表。这就说明邝坚的爸是实打实在帮大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