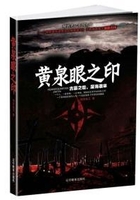大秀现在愈来愈爱打扮了,不光是漂了唇线和眼线,穿的衣服也分外地紧绷,全身勒得三弯三翘的,像春天鼓胀的豌豆荚,快要爆裂似的。女工们悄悄地说,大秀的胸脯并没有那么大,她戴的胸罩厚实,鼓胀的其实是泡沫。现在她对于刘胖子的出现,就像草儿花儿对于春天的气息的敏感,表现得很激动。胖子出差或是到外地办事去了,她会一个人说阴凉话,晓得胖子啥子时候回来哟!王小兰愣了她一眼,故意说,胖子这一走,会不会不回来了呢?她立刻皱起眉毛,声音提高了八度,他敢!挨着折底的女工都拿眼盯她,有的捂着嘴笑,那嘻嘻的笑声里分明含着轻蔑。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心里的秘密,一时头啄着,脸红着,没有了声气。
过了几天,刘胖子穿着黑呢子大衣出现在车间里,她弯起脑壳,仰起脸庞儿,痴痴地望着胖子,那眼睛里有些湿润,像孤单的小猫小狗蹲在家门前,望着离家很久了回家的主人。她好像也知道大家背地里议论她与死胖子的关系,与王小兰她们闲谈时就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我与胖子没有那种事,我这人最恨那些靠出卖色相获取什么的人。王小兰鼻子就很轻地哼了一声。大秀听不见的。王小兰心里想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又没有哪个问你。有时她又滔滔不绝地谈,老黑六十大寿,胖子都去了的,还与二哥三哥较酒,死胖子硬是喝得!死胖子的电话硬是多,这个月给他交了三百九十多元。他这次回总厂要走这么久,我要喊他留点钱。王小兰翻起眼睛愣着大秀,鼻子里又哼一声,当然是掌握好度的,大秀不易觉察。王小兰心里想,还说与胖子没关系,乌龟都上了门了,连钱都可以随便叫留些来用了,还没那种子事,没有才怪!
王小兰的头发还是在掉,大秀她们几个女工也是。
按新陈代谢,万物复苏的规律,进入春天以后,人是会长头发,不会掉头发的。这就充分说明掉头发与厂里的环境有关系。王小兰想,这样下去咋得了呢,做几年活路,钱又挣不到几个,自己变成了癞子了。女的如果没有头发,好丑人啰!
家里种田,绝不会有这些危害,满眼都是绿的。
三月的菜花五月的麦香七月青葱的秧田九月稻田的金黄,一年四季房子都被茂盛的庄稼包围着,被都江堰流出的潺湲的水环绕着,想吃啥就种啥。城里人喜欢吃无公害蔬菜,少打农药,少施化肥的蔬菜,就全用农家肥,包管价钱卖得好。如果想多赚点钱,就投资点竹木和薄膜种大棚,蔬菜可以提前上市。王小兰心里想,如果自己回家搞大棚,包管会搞好,因为自己在城里打了几年工,已完全晓得城里人喜欢吃什么蔬菜啰!现在当农民一点也不累了,自种,抛秧,秸秆还田,已不像以前红五月双脚泡在水里了,女人家每月来例假,也要泡在水里插秧呀,一窝窝地插呀!现在不了,收割也不弯腰驼背的,一镰刀一镰刀地割了,有联合收割机,呼呼呼地几亩田就割完了,那边麦子谷子就出来了,不用肩挑背扛地用拌桶打了。愈想愈看不顺眼车间里的一切,王小兰心里愈觉得在印月井城恒久包装厂里做活路是个恼火事情。
促使她下了回去决心的还有一件事。晚上回租住的房子洗澡时,无意间发现大腿间那片美地上的草掉了。当时她淋着热水冲洗,手一抹,手指上竟粘了五六根,她放在电灯下一看,大惊!这地方怎么会掉呢?王小兰想,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做下去了,再做下去就要出大问题了。她在心里嘀咕,这个月底拿到上个月的工资就走,带上福来走,管他向明同意不同意。他要一个人在两路口做活路由他,他能一起回去更好!这个月工资邓姐愿发就发,不发也就算了,浙江老板不怕做活路的人走了,走了就拿不到本月的工资,因为他们实行的是押一个月发工资,第二个月拿第一个月的工资,第三个月拿第二个月的工资。如果你长期为厂里效劳,那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到了年底就拿得到了,如果走了,就拿不到了。邓姐实行这样的管理,就是怕工人做到中途想走就走了。这也是一种管理的办法。
午饭时是女工们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蒸熟的饭蒸热的菜聚在一起,你尝点我的青椒炒肉,我尝点你的凉拌猪耳朵,各人带的不一样,五花八门,车间里一片饭菜的香味。王小兰正吃着,就见赵老乡鸡刨刨地跑进来。喘着粗气说,小兰,将你的自行车借给我用一下,玲玲发高烧,老师打小会的电话又打不通。王小兰说你去吧去吧!赵老乡骑上自行车嗖嗖嗖地射出了车间。
赵老乡边骑车边想着,回去先把取款的存折拿上,千万不要忘记了,进医院没钱不行,报纸上说一个感冒都要医两三千呢!
嗖嗖嗖地,赵老乡到了城郊的出租房。掏出钥匙插进锁孔里,钥匙扭不动,门是反锁着的。赵老乡呯呯地敲门,屋里一阵窸窣声,仿佛正偷吃大米的老鼠看见了猫仓皇逃走发出的那种声音。但门始终没有开。赵老乡大吼,开门呀!玲玲发烧,在学校里昏迷不醒的,我回来拿钱呀!快开门呀!
门开了,露出小会极不情愿的脸和一头凌乱的头发,她的眼光是散的,一碰到他的视线就散到一边去了。门全部打开,一个胖壮的男人挤出门外,瞟了自己一眼,三步并着两步,惊惶而去。虽然他只瞟了赵老乡一眼,赵老乡是看清楚了这个胖壮的男人的脸孔的,是王小兰她们恒久包装厂的厂长刘胖子,女工们背后都叫的死胖子。赵老乡什么都明白了,小会早已不是以前的小会了,难怪时不时地床角会钻出些高档烟的烟头,上个星期还有白壳壳烟纸盒。原来她是趁自己中午不回来吃饭,白天不在家,把生意做到屋里了。以前自己也听说过,一些打工妹在外面勾搭上生意后,将男的带到自己的出租房里,既安全又替对方节约了开房费,对方觉得女方还有人情味,皮肉生意才做得长久。赵老乡从米口袋里刨出存折,小会递上几张红花花的票子,说都这个时候了,还取什么钱。赵老乡脑壳一扭,哼了一声,走出屋外,骑上自行车嗖嗖嗖地飞奔而去。
小会小跑着,在后面撵。
浙江恒久包装总厂来了人,是来查厂里的账的,确切地说,是来查刘胖子的账的。因为那边打过来的两笔材料钱和印月井这边化工厂付的两笔钛白粉袋子款十一万的数目都对不上,这边还在闹买材料没有钱,总厂却没收到钱。胖子把总厂汇过来的材料款和化工厂收的袋子钱投进他的两路口的合伙假烟作坊里去了。胖子这是在铤而走险,巨大的利润吸引着他的心,他梦想挪用个两三个月就能把本钱悄悄地还进去,窟窿不就填上了?厂里急招胖子回厂对账,胖子怎敢不回?回来了的胖子心里也并不是很虚,总厂的厂长姐哥实是一个“气管炎”,就是妻管严。财务上的事情都是姐姐说了算。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他们笑嘻了对胖子说,刘厂长,不是我们俩与你过不去,是老板的意思,叫我们出差成都顺便来查一下你的账。胖子嘿嘿笑几声说,回去给老板说一下,我晓得给他个交代,那十一万元钱我借来急用下,这是借条,你们回去拿给我姐哥,其他就什么也不要多说。说着,就将借条递上。两个人当然晓得他们的关系,酒肉饭吃了后,只好笑嘻嘻地离去。
向明给老婆王小兰打过招呼,胖子说的,哪个都不能讲,讲了你娃的工资饭碗都泡汤。第一个月还可以,向明基本工资加管理津贴拿了一千五百七十元,这是自己出来打工以来拿得最多的一次,比自己打工的两个月的工资还多呢!手指蘸着口水数着手里一叠红花花的票子,向明黄瘦的脸在阳光下笑着。马不吃野草不肥,人不经商不富呢!前人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他把一千元挪在一边,把五百七十元揣进了另一个包里,他想的是一会儿就去存在卡上,把卡装进一个纸烟盒里,放在烟丝材料库的旧木桌里,加了密码,自己平时锁了木门的,烟丝贵重呢!虽几个合伙人都有钥匙,但谁去翻呀!翻着了也没用,加了密码的,取不了的。这样自己一个月就宽裕了,可以喝酒打牌了。
晚上向明回去,双手把一千元红花花的票子递给老婆。婆娘问多少钱,向明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往天好多现在还是好多!王小兰放下手里正择的空心菜接过钱数了说,比往天多了三百,胖子没亏待你呢!福来,快去幺店子上给你爸提两瓶强生啤酒回来,再买半斤油炸花生,你想吃啥也买一包,赊在那里,给阿姨说还瓶子时一起给。夏天黑得迟,福来正在屋檐下做作业。听见妈的话,哎哎地应答着,放着小跑就去了。酒桌上婆娘扯了两张红花花的票子给老公道,说话上算,你们男人家身上没有两个钱也窝囊。向明笑了下,脸红着说,不要啰!厂里给我委了个职,仓库材料保管员,发发烟丝泡沫烟嘴银丝纸条纸袋儿材料什么的,白天帮着记记数,记数是两个人,主要是互相监督,怕计数的得了工人的好处。王小兰说,特别是现在的女人犯贱,动不动就松裤带儿,男的怎么抵挡得了。向明说,你说对了一点点,主要的是胖子怕他不在,那几个股东在数量上和利润上烧了他。我帮他看着,股东都没意见,每月就给我两百多元钱管理费。王小兰眼里就升起了从未有过的笑意。
昏黄的电灯下,王小兰看着手上卷曲的细毛,头上的头发已掉得差不多了,下面又掉起来,王小兰下定决心等这个月发了上个月的工资,她就要带上福来回射洪家里。她搓了搓手上柔丝样的细毛,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星期天,福来起得早,学校今天开运动会,他很轻松地出去了。厂里这几天没货,王小兰也放了星期。
傍晚了,吃了夜饭好大一阵了,福来问王小兰,妈妈——爸爸咋这阵还没回来?王小兰说,他们的厂里加夜班,明天清早才能回来。
实际上,不光是向明他们造假烟的作坊,两路口所有造假烟的或大或小的地下工厂里都是晚上上班的。白天只是管理人在,向明说的白天上班是给老婆扯的谎,是怕老婆担心。附近的农户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是造假的,白天来把烟丝银烟带儿等材料领回自己家去做,做好了拿来交。验了质量按支数领取酬劳,现货现款,互不亏欠,比出去打工松活,还可以照顾家里的庄稼鸡儿鸭儿猪儿的。最后几道工序,烟嘴与烟杆,还有外包装覆膜封口打码打上烟草公司已验的标记,是必须在隐蔽的厂里的作坊里操作机器来完成的。那机器就是刘胖子挪用厂里的十一万元钱买的。操作都是深更半夜进行,作坊还有眼线看外面的动静。向明是吃了中午饭就出去的,自从他向老婆交了两个月的工资,老婆就不怎么把他管得那么紧了。厂里的几个与他身份差不多的人约着在离作坊不远的一个小茶馆打小麻将,下午是赢了。有规矩的,赢家办招待,小赢家给茶钱。向明是属于请喝酒的赢家,自然就请客了。喝了酒接着打,手气先不行,倒了两百多出去。过了十一点,手气来了,刚好自抠了个三番,正想着十二点全部捞回来说不定还要赢几个,情况就来了。先是一辆警车没有像平时拉响警笛几乎是滑行似地悄然地从打牌的小茶馆门前的村道开了过去,另外三个人愣了向明一眼,向明也愣了他们一眼,眼睛里的意思都是可能是哪里出事,不会是与我们的地下烟厂有关吧,莫得那么巧!刘胖子不是和另两个合伙人在他们面前拍着胸脯说的,他们市公安局都有人,有大伞罩着,没有问题的,即使有问题,我们早就拉上设备转移了。因为有这句话,他们也就不过多地想面前从夜色中滑过去的警车的事。可是警车一辆接一辆,大概有五六七八辆悄然地开过去时,他们有些坐不住了。特别是看到有两辆油绿色的军车上密密站着的荷枪实弹的戴钢盔的特警,他们不得不停止了麻将。处理个一般的治安事件哪用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哟!况且,都是向着他们打工的地下烟厂的方向开去的。向明突然把桌子一推,猛地站起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向着夜色里的地下作坊跑去。他虽抄的小路,还是去迟了,作坊所处的废弃厂房车灯雪亮,大批的武装警察已经将废旧厂房围得水泄不通。他选了个黑暗的地方站着,正揪心地埋怨,我的金穗卡呀!金穗卡上还有一千余元的私房钱呀!这时电话响了,是刘胖子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几乎是哭着说,都是小会害的呀!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她介绍的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亲戚呀!说在本地随便咋个歪都不会翻船的啊!这十一万元钱我这下咋个向姐哥交代呀!他几乎是捶胸顿足了。
而此时,王小兰正拥着福来在哄哧哄哧的拉沙石的汽车震动土路的喧杂声音中进入梦乡。她要到天亮后才会知道,自己的老公和刘胖子为了躲避公安的对制造假烟犯罪嫌疑人的搜捕,已经逃亡他乡了。迷迷糊糊中,王小兰和老公向明及福来已回到了村庄,田地里长满了荒草,王小兰使劲地拨弄着,好想把杂草扯完,请黄牛来操地,疏松,打田,开始种大棚蔬菜。这时她看见了赵老乡,正挥着锄头在挖地,他的女儿玲玲在帮他捡拾地里挖起的杂草。两只猫嗖嗖地从杂草丛中跳出来,一只麻色的,一只背上是白花斑纹路的,盯着她喵喵地叫。这就是自己家的那两只猫呀,一只送给了邓姐,它们都消失了好久了呀!原来是回了射洪老家的乡坝头了。怎么都好好的,没有一点点在城里的病病哀哀的样子呢?一大一小两只猫嘶声地叫着向她扑来。眨眼间,两只猫身上的毛全秃了,露出了黄色的肉皮。
王小兰醒来,想这是咋回事呢?看着牛肋巴窗外浓墨般的夜色,她不经意地摸了摸下身,原来是自己的那个地方秃了!唉……
王小兰已决意这个月做完就回老家去,是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连命都会没有的。不管老公回不回去,自己都要带着娃儿回乡下去的。她觉得有些刻不容缓,明天上班自己就得先给邓姐说说,以免她怪罪自己不提前打招呼而克扣自己的工钱。天蒙蒙亮了,她揉着眼睛悻悻地说,家里的田不能再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