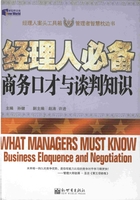第二天,那女人果真又来了。她说:“饿了两天,你应当是要跟我说实话了吧。况且,那男人已经被我打得要死不活了。你若是想要救他,最好就全招了。我再问你一次,你们,是什么人?”
我有气无力地说:“你先让我见见他……”
她朝门外击了两次掌,就有两人将楚殇拖了进来。彼时,风流倜傥的楚殇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的地方,血染红了他以前一丝不苟的衣服,就连墨色的长发也如枯草一般毫无生气。整个人,像是失了支撑的玩偶一般,任人丢弃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只呆在那里,说不出话。心里竟莫名地哀恸起来,眼角也不自主地泛出了泪,再不忍看向那边。
她用空洞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说:“你若不说,他的今日便是你的明天。”
“我只知道他叫楚殇,再多的,不知道了。”
她欲伸手来打我。却被一旁的一位婆婆拦住了:“小姐,依老婆子看,这姑娘委实是不知情。你就莫要动手了。”
“好,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就暂且放过她。”她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要等的人,也一直没有来,看来这筹码也的确不值钱。婆婆,你打点一下,送她下去吧。”说完,就走了。
那女人的话我只听了个半懂,却分明听懂了“下去”的意思呐,就是要让我挂掉。
我想啊,不就是去接见接见阎王,品鉴品鉴孟婆汤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婆婆真的给我端来一碗汤药的时候,我却没那么豁达了。此时,那碗毒药离我只有一寸远,我忽然福至心灵地想起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这么说的:人固有一死,能够明日死,今日就不死。
我被这句富含哲理的话深深地启发到了,于是,我豪迈地打翻了婆婆手中的汤,大声地将那句话吟了出来。
婆婆可能是被我的气场震到了。呆在那里反应了半天,才说:“哎呀,可惜了这活血祛瘀的良药。”她见我一脸的敌意,又笑着说,“姑娘家的脸可是顶要紧的事,自个儿得好好爱惜。”
我自是知道自己的脸昨日里被那女人打得肿了起来。却不明白在死之前喝下那么一碗药有什么用。于是我说:“难不成阎王会觉得我生得漂亮,然后收起来当个小妾?”
“你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娃娃,怎么就老把‘死’啊,‘阎王’的挂在嘴边呢。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兴许会苦些,但活着总是好的。”
我看到婆婆褶皱的眼角带着笑意,莫名地觉得很是温暖。于是问:“婆婆,可是你们小姐说要处死我啊?”
“真是个有趣的丫头。”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婆婆会说我有趣。因为,“下去”的意思呢,不是下到另一个世界,而是下到玉溪坛的下一层。而这里,才是真正的玉溪坛。
我站在楼梯的末端,看着这望不到边的酒窖张大了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制曲、选料、蒸酒、封口、入窖,每一步皆是秩序井然。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竟没有一人抬头,仿若手上的工作就是全部。
下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酿酒有这么多讲究。就连最简单的封口也很有学问。婆婆见我不明白也就耐心同我解释:“每坛加蜡三钱,竹叶五片,隔水煮开,趁热封口。酒便能经久醇香。”
她将我交付给一个祥和的大婶,安排了个相对轻松的活。婆婆临走前,我请她替我照看楚殇。她却说,不必担心,他很好。
我不明白,楚殇被伤成了那个样子,如何还能好。只当她是说来安慰我的。从玉溪坛出来之后,我回想她所说的,才知道这并非是宽慰人的话。
相处下来,我才知道,领头的大婶虽然看似祥和,却沉默寡言。不仅是她,这里所有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也极少笑。他们讲半句留半句,我才明白:这里不仅是个酒窖,亦是个囚笼;而上面的,只是一个伪装与空壳。
那是两年前的一天,掌势的卢老太遣散了老弱家仆,只将青壮的召集到地窖。
他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总归是衣食父母的指令,也就没有多想,一齐来了。
卢老太却当着众人的面,变成了位美艳女子。大家正想问出个所以然来,那女子就以倨傲的姿态宣布了他们未来的命运——就如我现在所见的——终日不见天日的工作。
他们之中也有过人想反抗。但那狠毒女子却早在饭食里下了一种叫酿月断魂散的毒。这种毒药每月都需要服食部分解药来抑制毒性,如若不然,那么,月圆之日便是死期。
这种稀罕的毒药是闻所未闻的,解药就更不知道要从何配起,以至于大家不得不被钳制。
他们放心大胆地让我知道了这个天大的秘密,又不害怕我会泄露出去。
如此看来,我同这里的其它人一样,除非有仙人搭救,否则很难重见天日。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在我的吃食里,多添了一味叫酿月断魂散的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