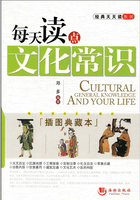贾雯鹤
一、诸家关于鱼凫名义的研究
鱼凫继蚕丛、柏濩(灌)而王,是为第三代蜀王。鱼凫,《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纪》前作“鱼易”,后作“鱼尾”,显然是形近而误。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华阳国志?蜀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从上述记载来看,鱼凫王田猎于湔山的时候,便升仙而去。蜀国人十分想念他,还在湔山建祠祭祀这位蜀王。湔山即汉绵虒玉垒山,湔水所出,就是今天都江堰、彭县北境的茶坪山。所谓从湔山升仙而去,是一种隐喻的表达,学者认为是“说明鱼凫兴起于此,亦退保于此”。
这样看来,鱼凫族和蚕丛、柏灌族一样,都是来源于成都西北的岷山山区。《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三杨齐贤注引《成都记》云:“蚕丛之后有柏灌,柏灌之后有鱼凫,皆蚕丛之子。鱼凫治导江县,尝猎湔山,得道,乘虎而去。”径直将柏灌和鱼凫看作蚕丛的后代,虽然与史实不合,但多少也透露出三者的一些共同性来。他们都是源起岷山,而后入主成都平原,最后退居岷山。同时他们都是氐羌族系,先后都建都于瞿上(即三星堆)。
对于鱼凫名义的理解,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将“鱼”和“凫”分开来解释,孙华先生《蜀人渊源考(续)》说:
鱼凫,其名由“鱼”和“凫”两个名词组成。“凫”字如前所述,即蒲卑之“蒲”,也就是一种水鸟。《尔雅?释鸟》说:“舒凫,鹜。”晋郭璞解释说:“鸭也。”实际上,凫字的意义并不像郭璞解释的那样狭窄,凫在先秦时乃是包括了鸭在内的一类鸟的名称。《诗?大雅?凫鹥》有“凫鹥在径”的句子,“鹥”字,毛《传》和《说文?鸟部》都释为“凫属”。可知凫也包括了鹥在内。然而,鹥在先秦时又是凤凰的别名。《楚辞?离骚》有“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的句子,王逸注道:“鹥,凤凰别名也。”《山海经?海内经》也说:“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鹥鸟。”这样,凫鹥不仅是实有的水鸟之名,而且也是虚幻的神鸟之名了。按鹥字本与“乙”、“鳦”、“益”字古音相近,前人早就指出,乙、鳦均义为玄鸟,也就是燕子。鱼凫这一族名以鸟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并且这种鸟或以为是水鸟,或以为是凤凰,还有可能是燕子,这些又大都与前述蒲卑氏的祖神望帝杜宇的形象相似(杜宇即子雟,又名雟周、燕燕、鳦)。因此,很可能鱼凫一族中的凫氏,也就是蒲卑族,它是一个以凫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至于“鱼”字,应为《说文?鱼部》的所谓“水虫也”,也就是“鳞介之属”的总称,它应是一个以鱼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如此看来,所谓鱼凫应是由鱼氏和凫氏两个氏族所组成的古族的称号。
胡昌钰、蔡革先生《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对鱼凫的理解实际上和孙华先生一致,他们说:
鱼凫,可分释为鱼和凫。结合出土铜人的体质特征看,鱼和凫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鱼、凫的结合,实际上应是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
另外一种看法是将鱼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鱼凫就是善于捕鱼的鸬鹚。《四川古代史稿》说:
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种“鸟首形器柄”颇引人注意。都是在第二期以后的文化层中发现的,没有完整器形,只存棒形器柄,柄端形如鸟头,喙长而带钩,其形象与巴蜀铜兵器(戈、矛、剑)上的鸟首图案颇为相似。这种鸟首图案就是被艺术化了的鸬鹚,鸬鹚俗称鱼老鸦,也就是鱼凫,它可能是一种图腾象征。
管维良先生《鱼凫族探源与三星堆断想》说:
关于鱼凫——鸬鹚,《尔雅?释鱼》郭注曰:“鸬鹚,嘴头曲如钩,食鱼。”明朝徐芳有《鹚说》曰:“鹚,水鸟,状类凫而健喙者也,善捕鱼。河上人多畜之,载以小桴,至水渟洑鱼所聚处,辄驱之入。鹚见鱼,深没疾捕,小者衔之以出,大者力不胜,则碎其羽,呼类共博,必噎之乃已。而渔人先以小环束其颈间,其大者既不可食,得之则攫去;小者虽已咽之环束处,鲠不可下,渔人又辄提而捋之,鱼累累自喉间出。至楞极乃消(稍)以一二饲之,而又驱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六亦曰:“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正是由于这部分巴人以役使鱼凫捕鱼为特色而异于其他部族的巴人,故获得鱼凫族(实应称巴人鱼凫部)之称。
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难以成立。鱼凫作为一个氏族名,却被分开来解释为由鱼氏和凫氏结合而来,这种命名方式,我们不但在蚕丛、柏濩、杜宇、鳖灵等古蜀氏族名号中找不到相似的例证,就是在我国上古时期的其他氏族名号中也难以找到同样的例证。因此,学者在凫字的解释上游移不定,“或以为是水鸟,或以为是凤凰,还有可能是燕子”,让人难以适从,就是因为这种分释的方法本身就站不住脚。将鱼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身是正确的,但将鱼凫和鸬鹚画上等号却缺乏文献证据。
考虑到鱼凫一词,鱼字始终不变,而凫字多有异写,我们认为鱼凫是一个与鱼关系密切的部族。鱼凫可能是鱼的缓读,或者说凫字是个没有实义的词缀。总之,鱼凫和鸟没有任何关系。这从我们下面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来。
二、鱼凫族的神鱼崇拜
我们前面说过,鱼凫族是源于岷山地区的一支部族,而这一地区古为氐羌聚居之地,因此早就有学者将鱼凫和《山海经》中人面鱼身的氐人国联系起来,认为鱼凫族是氐族的一支。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面而鱼身,无足。”郭璞注:“尽胸以上人,胸以下鱼也。”《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郭注:“人面鱼身。”郝懿行疏:“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王念孙、孙星衍均校改“互”为“氐”。因此互人之国就是氐人国。
氐人国在建木之西,我们曾著文指出,建木在都广之野,都广之野在昆仑之上,而昆仑的原型正是岷山,因此氐人国应该在岷山地区。而建木和昆仑都是古人所认为的连接天地之间的天梯,因此生活在这里的氐人“能上下于天”。
《山海经》紧接着互(氐)人之国的就是“鱼妇”,《大荒西经》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郭璞注:“《淮南子》曰:‘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盖谓此也。”袁珂注:“郭注引《淮南子?坠形篇》文,今本云:‘后稷垄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故郭注龙当为垄,中当为半,并字形之讹也。宋本、明《藏》本中正作半。据经文之意,鱼妇当即颛顼之所化。其所以称为‘鱼妇’者,或以其因风起泉涌、蛇化为鱼之机,得鱼与之合体而复苏,半体仍为人躯,半体已化为鱼,故称‘鱼妇’也。后稷死复苏,亦称‘其半鱼在其间’,知古固有此类奇闻异说流播民间也。”
从注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鱼妇为颛顼所化,即指鱼妇为颛顼的后裔,所化作的形体和氐人国完全一样,都是半人半鱼的形象。鱼妇所在,从它紧接互(氐)人之国来看,应该和氐人国相邻。而且郭璞引《淮南子》后稷垄来作注,显然以为二者为一。后稷垄从《淮南子》来看,是在建木西。据《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则后稷葬在都广之野。《海内西经》又云:“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因此后稷之葬(垄)或说在建木西,或说在都广之野,或说在氐(人)国西,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个地方,就是昆仑,或者说是岷山。因此鱼妇所在和氐人国一样,都在岷山地区。
鱼妇,已经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就是鱼凫。妇,古音为之部并纽;凫为侯部并纽,声为双声,韵为旁转。可见,鱼凫和鱼妇不仅仅在古音上可以通转,而且从上面考察来看,他们都处于岷山地区。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鱼妇就是鱼凫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犹有说者,《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大荒北经》亦云:“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郝懿行疏:“《文选》注谢朓《哀策文》引此经作鲋禺之山,《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此经与今本同。”我们认为颛顼死后化作鱼妇(凫),而颛顼所葬之地务隅、附禺和鲋禺之山并为鱼妇(凫)之倒称。而山之得名自然是因为鱼凫族兴起于此而得名。
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我们既然说鱼妇(凫)是颛顼之后,颛顼又是黄帝之后,但《山海经?大荒西经》不是明说氐人国是炎帝之后吗?实际上在《山海经》的记载中,同一人物往往同时归属于黄帝和炎帝之后,举一例以明之。《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是祝融为炎帝之后。《山海经?海内经》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大荒西经》又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是祝融亦为黄帝之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鱼凫族只和鱼发生关联,和鸟没有任何瓜葛。因此,我们推测鱼凫族是一个崇拜鱼的部族。而从“鱼妇”的描写来看,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而是能够死而复苏的神化的鱼。
《山海经?南山经》云:“又东三百里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郭璞注:“此亦蛰类也;谓之死者,言其蛰无所知如死耳。”我们认为柢山之上的鯥鱼就是鱼凫族所崇拜的鱼的原型。首先,柢山之柢和氐古字相通。《老子》五十九章:“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马王堆帛书乙本《老子》“柢”作“氐”。因此,柢山就是氐山,而鱼凫族正是氐人,显然氐山是以氐人而得名。其次,鯥鱼冬死而夏生,和鱼妇的死即复苏如出一辙。而且鯥鱼有蛇的尾巴,联想到鱼妇也是“蛇乃化为鱼”。所以,我们认为鯥鱼就是鱼凫族所崇拜的神鱼的原型。
鯥鱼陵居,显然是一种两栖类的动物,而鯥鱼也正以陆居而得名。或许正是鯥鱼这种既能水居,又能陆居的两栖特性,被鱼凫族视为神异,以它为部族的崇拜之物,而有鱼凫之称。
我们说鯥鱼只是鱼凫族崇拜的神鱼的原型,而鯥鱼向神鱼转化的最终产物就是陵鱼和龙鱼。《山海经?海内北经》云:“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这里的陵鱼已经是人面鱼身,和氐人国之人、鱼妇等的形貌完全相同,显然已经是一种神化的鱼了。
《山海经?海外西经》在“诸夭之野”之后紧接着说:“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鳖鱼在夭野北,其为鱼也如鲤。”袁珂注:“龙鱼,疑即《海内北经》所记陵鱼,盖均神话传说中人鱼之类也。龙、陵一声之转,一也;龙鱼陵居,陵鱼当亦因其既可居水,复可居陵而号陵鱼,二也;龙鱼似鲤,谓之龙鲤,陵鱼亦似鲤,谓之陵鲤,三也;龙鱼‘一曰鰕’,《尔雅?释鱼》云:‘鲵大者谓之’,《本草纲目》云:‘鲵鱼,一名人鱼’;而‘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之陵鱼,正是人鱼形貌,四也。有此四者,故谓龙鱼即《海内北经》所记之陵鱼。”袁先生以龙鱼即陵鱼,甚是。此龙鱼在“诸夭之野”之北,而“诸夭之野”,我们曾著文指出,它和都广之野本是一地,都是神话的乐园,都位居昆仑之上,而昆仑的原型正是岷山,因此龙鱼亦应在岷山地区。我们认为龙鱼正是居于岷山地区的鱼凫族崇拜的神鱼。
此外,我们注意到《山海经》关于龙鱼的异文是“一曰鳖鱼在夭野北,其为鱼也如鲤”,就是说龙鱼在另外的版本中是写作鳖鱼。我们前面说鯥鱼是一种两栖类的动物,结合到龙鱼又作鳖鱼来看,鯥鱼可能就是一种鳖鱼。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出生在岷山地区的禹,他的父亲鲧在入于羽渊之后,变化而成的动物就正好有“黄龙”和“黄能”之异。
《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即《归藏?启筮》)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 《左传?昭公七年》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杜预注:“熊,亦作能。”《释文》:“能,一音奴来切,三足鳖也。” 《史记》卷二“正义”亦云:“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晰《发蒙纪》云:‘鳖三足曰熊。’”可见黄能就是三足鳖。前人在鲧化为黄龙和黄能的问题上可谓百思而不得其解,从龙鱼又作鳖鱼来看,黄龙并非指龙,而是指的是龙鱼,因此黄龙(龙鱼)和黄能(三足鳖)仍然是统一的。所谓化为三足鳖,按照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所说:“死亡就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那么鲧、禹的图腾应该是鳖鱼了。
考虑到鱼凫族和禹都曾居住在岷山地区,而又都以鳖鱼为崇拜,我们似乎可以说,在上古时期的岷山地区曾盛行着鳖鱼崇拜。
三、鱼凫与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