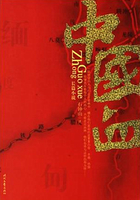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德洁,德洁。”李宗仁连声呼唤妻子,却不闻回音。他有些诧异,她到哪里去了?自这次逃离南京又聚首上海,夫妻俩的感情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离乱给人痛苦,也自然会使人变得更加珍惜团聚的幸福。“德洁——”李宗仁稍稍抬高了嗓门。心胃又一阵不适,以至有些想呕吐。
郭德洁出门去了,也许临走时看李宗仁在闭目养神,她不忍打扰他。
她知道他心胃气痛,昨夜一整夜都没睡好。
李宗仁索性躺在皮沙发上,头枕着那个圆筒扶手。他想起逃离南京那天早晨给妻子许下的愿——元宵节陪她到蒋主席的黄埔路官邸去参加舞会,害得她白高兴了一场。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个不可与蒋氏交好的命。北伐前在广州交谈的不投机,长沙换帖的不自在,以及蒋宋结婚时的不送礼,他总觉得,在感情上,他和老蒋隔着一座山。德洁月初到上海后,他还偶尔问及元宵舞会的事。德洁说,哪还敢出门呢,每天每天,我最怕听见的是那犹如警报的门铃声。一有人来,我便以为是来抓我去当人质的……
一阵鞋帮叩击水泥台阶的声响,不一会儿便有人打开了二楼的厅门。
“德邻,德邻。”郭德洁的呼声很急,“我给你请来一位法国医生,出来看看吧!”李宗仁披上大衣,缓缓走到厅里来。客厅里坐着位黄发金须的法国大夫。他能操夹生的汉语,不用翻译。郭德洁滔滔地向他诉说李宗仁的病情,他却只顾拨弄他的血压表、听诊器,大有“病家不用开口”之势。
李宗仁一向不太信奉西医,特别是心胃气痛这类病。“西医么,发热也是发炎,发冷也是发炎,冷热都不分呢!”这话,他不知对郭德洁说过多少次。可她今天偏又帮他请来个西医。
一阵折腾,那医生开了三大张处方笺的药才耸耸肩膀说:“胃炎。吃这些药准好。”郭德洁送医生走后,李宗仁才拿起处方笺来看,尽是些蚜虫文。“哼,曲里拐弯莫吓人,不过又是些苏打粉、维他命。”“德邻,西医快,中医慢。你就依了我,吃几天西药看看吧!”郭德洁知道丈夫的脾性,她拿上处方笺便要上街去买药。
“人说久病成良医,我这病自己最清楚。你就照我那老单方去捡中药吧!”李宗仁那个危急时常贴身带着的公文包里,有一张翻叠得快烂了的处方笺,是他曾祖父传下来的治心胃气痛的秘方。这些年来,他吃了也还应验。
他的曾祖父,是乡村里远近闻名的老中医。
郭德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到房间里取了那份老单方,拖着很不情愿的步子,出门去了。
李宗仁又回到居室侧厅的那张皮沙发上,心情比先前更加郁闷,随手翻了翻条几上的报纸,也只是摇头叹气。时局变化,风云莫测,北伐中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了胜利,本以为可过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如今形势却急转直下,原先曾在一条战壕里的人,转眼侧目,派系纷争,此伏彼起。
自己于治兵之道虽颇有些方法,于这类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人事纠纷,却显得才不如人。
李宗仁咂了咂嘴,苦涩极了。近来,兴许是胃真是在发炎,他舌苔黄腻,苦得像吃了胆汁。他起身在茶几上将暖瓶往茶盘里那只长嘴罗汉肚宜兴陶壶灌了些开水,又用手轻轻地摇了摇,然后含着壶嘴缓缓地吮了两口茶。
长期在两广生活,他养成了讲究喝茶的习惯。甚至那些浓得如同酱油一般的“功夫茶”,他也能喝上两杯。以苦茶润苦口,“以毒攻毒”,他又一连吮了三四口,咂咂嘴,依旧是那么苦涩。
他穿过廊道来到南面那个宽敞的阳台上。阳光柔和得似有似无,老历二月的日子,春寒料峭。庭院里那几株法国梧桐,被寒风剥光的枝条上,已经挂满了拇指大的新叶,二月春风似剪刀,把嫩绿剪裁得如诗似画。阳台上的盆花,刚刚从冬眠中苏醒,那玫瑰和月季的紫红色的新芽,怯怯地从岔枝的老叶下,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冬去春来又一年。这一年,北伐虽取得了胜利,全国基本实现了统一,但国民党人内部龃龉纷争,愈演愈烈:
以汪精卫为首的汉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派,各持一端,夺利争权。社会上流传的“党军北伐,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的话语,确是眼下中国的时弊。
李宗仁伫立在阳台上的漆木扶栏边,沐浴着并不温暖的阳光,心颇似气候一般寒冷。这一年来,从结束战争到纠葛于人事,使他感觉到自己以往那种军人不参政的想法的幼稚与不实际。中国这块土地,自民国成立18年来,似乎是没有真正统一过,该因军人与政客混为一体,而他一个在促成和完成北伐中屡建功勋的军人,如今却被形势所逼,避居到这法租界的融园里,过着流亡避难般的生活,是多么惨痛而又令人愤然。
飞过来一只麻褐色的小鸟,在那株高高的梧桐树上叽叽地叫着。也许是刚刚失群,声音有几分凄厉。李宗仁想起家乡广西临桂两江头村后山林里的杜鹃鸟。这春日,也许已经开叫了吧,那鸟儿催春,总“赶快啰赶快啰”地啼叫。啼血的杜鹃!催人耕耘,催人上进。如今,即使那杜鹃在眼前催啼,又何济于事?兴许是心的寒凉与郁闷,李宗仁闻声不禁打了几个寒战。
“德邻——德邻——”正当李宗仁想折回房间里来的时候,厅门边传来郭德洁一阵急促的呼唤声。
“哟,这么快,药就捡回来了?”“我和雨农雇了一辆黄包车想到城隍庙那边去捡药。出门不多远,便听得有报童呼唤:‘特大消息,李济深被蒋主席软禁于汤山。’我急得跳下车来,买了张《国民日报》,见消息确如此,急着要赶回来告诉你,只好叫雨农一个人去捡药了。”“嘭!”李宗仁一拳打在那扇嵌着凸花玻璃的厅门上,震得门扇上的玻璃格子嘎喇响。他原本对任潮入京调解中央与武汉方面的矛盾就提心吊胆,只企求能免去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如今蒋介石却对“以人格作担保”的李济深下了手!他那本就气痛交加、抑郁隐痛的心,像猛地受了两块巨石的夹击,顿时头脑晕昏。他踉跄着大步冲进厅里,跌坐在沙发上,用抖抖的手,接过妻子手上那张《国民日报》。
李宗仁感到身上一阵发冷,像岭南的摆子病一样,骤然而来,使他牙齿微微相叩,虽然身上穿着件羔皮背心,外加件丝棉袄,却抵不住这发自内心的寒凉。他只是瞭了一眼任潮被困汤山的那篇文章的标题,一目十行地扫过题下那些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混账话,战栗的心在发出夹杂着怨艾的惨痛的悲鸣:任潮啊任潮,照理说,你是个智者能人,为什么你偏偏看不清时局大势,识不破蒋介石的两面三刀,如今是误入圈套,自投罗网?
郭德洁陪坐在李宗仁身边,神色有些惶惑紧张。她没有作声,只默默地企图镇定自己的情绪。
“德邻,你说任潮会有生命危险吗?”郭德洁双手捏着李宗仁那冰冷的手,身子紧挨着丈夫。她知道他全身都在发冷,她想用体温来温慰他。
郭德洁与李济深并不很相熟,交往也不多,只是自与李宗仁结婚五年来,常常听丈夫谈到这位厚道的长兄,谈到他对桂省新军的扶助和他重义重情的为人,也听丈夫谈到他善处人事的才能。一个广西人,那年头在粤军中要想长期地立下足来,而且在地方上有威望,是非要些本领不可的。兴许是听的多了,郭德洁对丈夫这位显得黑矮、貌不惊人的朋友,也产生了几分敬佩之情。特别是十天前,当李济深执意要离沪赴京前夕,匆匆到这融园来告别的那一幕——那天,天下着毛毛小雨。上海初春的夜雨,寒凉得有些浸人肌肤。李济深穿过雨幕走进厅门时,本有些乌黑的嘴唇变得青紫。
“德邻,我决定明日进京。”不待坐定下来,李济深边用袖口拭着前额上的细水珠,边话语急促地说,“我再三想过了,我这次若不去见蒋先生,恐怕他疑心更大,对武汉用兵更快。”“任潮兄,不能,万万不能!”李宗仁面对这位比自己大五岁的长兄,从来没用过这般强硬的话语。他亲自给李济深沏了茶,扶着李济深走到还燃着温火的壁炉前,又不客气地问道:“你怎么变卦了?”前天,李济深以省主席名义率领一批广东代表抵沪,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大全会。前段时期李济深在广东已听说武汉对长沙鲁涤平用兵后,李宗仁自知待在南京危险而避到上海之事,并与李宗仁通过电报,但纸短话长,一时说不清楚。这次抵沪,自然要来当面问个明白。加之蒋介石想做些表面工作,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元老趁李济深到沪时,劝说他做中央和武汉两方面的调停人,所以李济深到沪的当天晚上,就到融园来看李宗仁了。当李宗仁向他详叙了“武汉事件”真相,并剖析利弊,奉劝李济深暂不入京时,李济深已满口答应。为什么仅一夜之隔,如今便又那么毅然决定要赴京?
“德邻,不是我变卦。国事为重,我愿跳火坑。再说,吴老先生也说过,蒋先生对我的人身安全,愿以人格担保嘛!”原来蔡、李、吴、张四人在劝李济深入京做调停人时,已向李济深保证过,说是蒋先生愿以人格作担保。
“哼,蒋先生以人格担保,说得好听!”李宗仁愤愤地说,“蒋先生这句话可曾真讲过?这又有谁能担保?再说,蒋先生若有些诚意调解矛盾,又何尝不可屈尊来沪?”
“我入京,是想避免一场战事。”“你入京,正是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促成了一场战事。”“不能吧,德邻!”“你入京,他必把你拘禁,然后用甘辞厚禄引诱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叛你。那么,广西失去广东的援助,武汉则完全独立。中央军四面合围,我们四集团军寡难敌众。”“德邻,你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任潮兄,难道你今天还不懂得蒋中正的为人?”那天夜里,李济深和李宗仁一直争论到天亮。郭德洁反常地有耐心,默默地陪在一旁,为他们添茶水、旺壁炉。最后,李济深以“为息战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慨,告辞融园,消失在雨幕中。
“任潮兄太不肯听我的劝告了!”李宗仁见妻子一直握着他的手,若有所思。良久,才慨叹地说,“这遭遇,果中了我的预料啊!”“德邻,事情已到这地步,气也无用。”郭德洁平和、温存地劝李宗仁,“你正患心胃气痛。万事万物,身体第一啊!”郭德洁不提起,李宗仁倒像是忘了身上的难过,一时只气得脸色青紫。
郭德洁这一提,他即刻感到胸口一阵难耐地疼痛,以至禁不住返出清口水来。
“德邻,我扶你到床上躺躺。”郭德洁松开手,站起来要搀扶李宗仁。
“不,不!”李宗仁坚决而又有些迟缓地摇了摇头,沉重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任潮是个好人。他虽长年在粤省军政界任职,实际上总护着我们桂省。如今落难,我岂能安得下心来?”“我哪是叫你不去解救任潮呢?德邻,眼下你自顾不暇,疾病缠身,总该顾本啊!”郭德洁使劲要将李宗仁扶起,李宗仁也只好就着她。的确,心胃气痛使他感到眼下诸事力不从心。
李宗仁忍着痛,坚决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卧室走去,口里愤愤地说:
“吴稚晖说什么蒋先生用人格保证任潮的安全。现在,难道吴稚晖是放屁!
蒋中正的人格让狗吃了!”李宗仁刚在那张宽大的棕绷床上躺下,忽地又撑起身来,咬着牙坐到写字桌前,拿起毛笔,在十行纸上给吴稚晖写信。可刚刚写下称呼,寒暄的话都还没结句,他又一把抓起,揉成一团,朝字纸篓掷去,写写掷掷,一连三张。他觉得写也无用,说也无补。一个吴稚晖,劝得动铁石心肠的蒋介石吗?就算是吴稚晖说蒋介石用人格作担保的事是骗人,如今木已成舟,莫说是写信骂他几句,就是当面打他几巴掌,难道又能够救得了任潮?
郭德洁帮李宗仁端来那只罗汉肚小宜兴壶,默默地放在桌上。时局的不顺,丈夫的病痛,客居在这法租界里的不安,使她本来红润的脸色变得黄白黄白。她自然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用怎样的语言劝慰丈夫,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李宗仁感到嘴唇燥枯,端起茶壶便咕咕地吮茶。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很重,像是雨农。
“总司令,总司令!德公,德公!”季雨农在楼道口急促地呼唤。他平时,尽管脚步再重,也总是轻轻地叩门。而且,自从跟上李宗仁从南京逃到上海之后,他也开始跟着那些与李宗仁亲近者称李宗仁为“德公”。
眼下的李宗仁,挂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而无兵权,挂着国府委员不理国事,至于那本就徒有空名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更是挨不着边了。他觉得无论称李宗仁什么职务衔头,李宗仁面部都会略略出现难色和窘态;只有称呼他德公时,他才对应自如。
厅门虚掩着,季雨农用手推了推,险些和来开门的郭德洁撞个满怀。
“李夫人!”季雨农歉意地将提袋里的中药交给郭德洁,“药。”李宗仁已经坐在沙发上,注视着季雨农有些反常的慌张神色,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德公,我刚才在街上遇到王又庸了。”季雨农疾速挨坐到李宗仁身边,用一种让人感到惶惑的口气说道,“就是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的那个心腹。”李宗仁睁大了那双显得疲惫的眼睛,等待着季雨农的下文。
“他说,唐生智已奉蒋主席之命,前日在北京顺承王府宣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还说,第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已宣布脱离白参谋长管辖。”李宗仁目光变得有些呆滞,盯着季雨农,半信半疑:蒋介石忽而下令讨伐唐生智,忽而又利用唐生智来对付“桂系”的事,这倒是他的惯技。唐生智有钱有官不认人,有奶有饭就是娘的禀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唯五十一师和五十三师,分属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和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所辖。
两个地道的广西人,在我李宗仁和白崇禧手下发迹升官,如何也那么黄脸寡情,六亲不认?他禁不住问道:“雨农,这消息可真?”“五十一师、五十三师多是三湘子弟。唐生智一是带着巨款,二是拉乡情关系。吃粮当兵的,难免朝秦暮楚。再说,王又庸与白参谋长相好,哪会乱造谣?”李宗仁点了点头。季雨农又说:“他还告诉我,今早上他无意中走进熊司令的办公室,偶然得见桌面上摆着件红色签条的‘急件’。他拿起一看,竟是蒋主席发来的‘手启’电报,电文是:据报白崇禧3 月20 日乘‘日清’轮从天津南下,着即派一快轮到吴淞口处截留,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李宗仁深深地吸了口气,困顿地闭上了眼睛。两个至友,李济深被困汤山,白崇禧被暗夺了军权,正在逃难,吉凶未卜。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郭德洁一直捧着从季雨农手中接过的那四包中药,站在沙发边,神情随季雨农的叙述,从沉郁变得有几分惶恐。她不像别的女人、别的军官太太,丈夫有钱有势,自己则只顾享乐消闲;她似乎想关心丈夫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政事军事还是私事。如今避难似的寓居在这租界里,相依为命,自然更是息息相关了。
“德洁,你先去叫人熬药吧!”李宗仁想缓和一下厅里这紧张的气氛。
人遇到不幸的时候,有女人在身边,会使不幸变得更不幸。郭德洁有些依依不肯离去,但终于还是走了。
“雨农,你坐坐!”李宗仁脸色很难看,蜡黄中带着青灰。
“德公,我不想坐。这屋子里真有点闷人,我们到阳台上走走,可好?”屋外,刚才那似有似无的太阳光,被厚重的瓦灰云遮住。杨柳风吹面不寒,却给人三分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