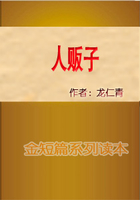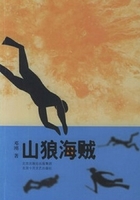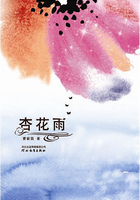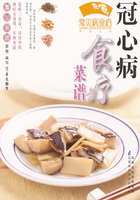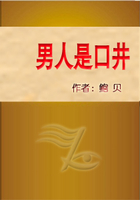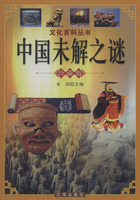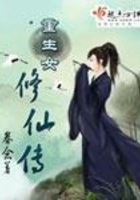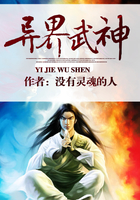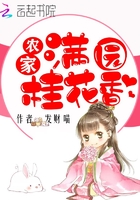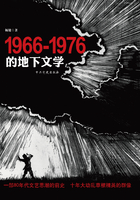“唉!”李宗仁一声重叹,频频摇头。人啊,许多许多的事都是不能由己的,还是王熙凤那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他重又进了书房,坐在那张大写字桌前的皮转椅上,无心再去翻《唐诗三百首》,却瞟见书房那张《先驱论坛报》。那是上个月中旬的一张旧报纸,红题黑字,尽是李宗仁所说的“腊肠文”,他一个也不认识。可是那上面有一篇文章,他却了如指掌——那是他的一封给美国政府的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再走制造两个中国的错误道路,应该效法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方针,承认共产党中国。15 年来,他虽然是个“亡国之君”,但系国之心不已,曾以在野之身发表过许多言谈见解,《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特别是1963年夏天,他为见程思远而到罗马,在那里,他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时慷慨陈词:“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他的这些言谈见解每每受到台湾势力的攻击,眼前这张《先驱论坛报》上的公开信,更引起蒋派势力的起哄辱骂。前几天,他收到老友白崇禧的电信,信中居然指责他“历年来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本来,音讯久疏的老友来电,自当深虑,但他却一笑置之。他早就预料到那位“小诸葛”误入樊笼后,会身不由己,言不由衷。1959 年,马来西亚共和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该国政府总理东姑拉赫漫邀请白崇禧以中国伊斯兰教理事长名义前往吉隆坡观礼。老蒋唯恐他一去不返,坚决不允。台北松山路的白寓,便是“小诸葛”的“定军山”了。
“健生!”李宗仁没有去翻那张《先驱论坛报》,而是又一声重叹。
他想去书柜里取出那几大本珍藏的相册,重温一番往日的风姿,回味那在风火中逞强的历史,却又直坐在转椅上,起不了身。那些相册,他不知翻看过多少次了,每每思旧,每每苦闷,每每孤独,他便要去翻翻,让自己暂时地撇开现实,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面,有他在台儿庄车站站牌下以手叉腰,昂首挺立,傲视寇仇的英姿;也有白崇禧在北平故宫崇禧门下扬扬得意、倜傥洒脱的笑容;还有他和白崇禧在南京大方巷官邸会见外国女记者时的风流合影……可是,只要一合上相册,便顿生忧伤之情。往事历历,不堪回首。“人到愁来无处会,无关情处总伤心”,那些照片却处处关情啊!
明艳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在他的写字桌上,把那份《先驱论坛报》的红字报头,映得有些耀眼。阳光,多好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它才永恒!
他打算到室外的花坛草地上去走走,梳理一番纷乱的思绪,然后给程思远写封信,写一封他早已想写但一直未写的信。
绿荫的院子里空气真好,花草树木春的生机,给人以春的感染,玫瑰的淡淡清香融合在芳草的淡淡的清香中,偶尔飞来一两只小白花蝶,缀在这草色青青、树色青青之中。李宗仁缓缓地在那条褐色的水泥道上行走,已经显得有几分龙钟老态。胃病割治后,没有再患过,可近年来,肺心病又渐渐冒了出来,不仅急速的行动会气喘吁吁,就是走上二楼,也有些喘喘。人老了,一年不如一年啊!
他想起1963年冬天,在瑞士的苏黎世与程思远见面。为避开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两人驾着汽车沿着莱茵河畔的公路向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的工业城市巴塞尔作长途旅行,并在一间山谷中的小旅馆过夜的情形。晚饭后,他和比自己小17 岁的程思远,还兴致勃勃地在山间小路上散步,那时不喘,也不累。兴许有太多的话要对那位阔别14 年的老部属、老朋友说,他和他在那个山间小旅馆一直谈到天明。他向那位大陆解放后久居香港且常能见到中共最高级官员的贤弟倾诉了书信所无法表白的衷肠:
“我的几乎一切灾难和不幸,都是因为与蒋介石决裂得太晚了。一时犹豫,错过良机,酿成千古之恨。”“共产党的政策是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呀!”“我曾经对人说过,我并不像台湾某些报纸攻击我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能否认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
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组织得好……共产党有像周恩来那样虚怀若谷的人,我又何必沉溺于个人的区区得失之中呢?我愿意向西方的运动员学习,在竞争中眼看自己注定要失败,便不再竞争下去,甘拜下风……”“德公,我一定把你的想法转告周恩来总理,一定。”李宗仁沿着水泥道缓缓走了一圈,已经感到有些吃力,便在晾衣架旁那张石绿色的塑料靠椅上坐下来。自苏黎世回来转眼又一年多了,思远偶有信来,却未提及落叶归根的事,他不会忘了将我的话转告周恩来吧?要不,难道时机还没成熟?“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年已经74 四了,这断了线的风筝还能飞到几时?
李宗仁靠坐在椅子上,本想到院子里来梳理一番思绪,却“剪不断,理还乱”。他只好微闭着眼睛,让北美洲的春日给他些温暖。
“噗噗噗”,贝拉夫人又在篱笆那边晾晒东西了。她没有再向李宗仁打招呼。她猜想她的这位中国前代总统的邻居大概又是在想事,她不去打搅他,也不必有那么多俗套。而李宗仁呢,见贝拉夫人忙得不亦乐乎,心中却生出一种羡慕感。这位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女人,也像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女人一样勤劳、朴实。他常常见她那样忙碌。人,劳动着、忙碌着是幸福的、充实的。自己呢,去国十有五年,而这15 年却是在闲、闷、孤独与懊恼中度过。就这身体,往后的日子绝不会再有15 年了。归去,坚决地归去!他想,回到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去,哪怕是还能做一丁点于中华民族有益的事,便也心满意足了。
他一撑身站了起来,大步走进屋去。他打算马上给程思远写一封信,表示急欲归国之情,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祖国建设事业的一分子,不愿再在这悠闲得令人发慌的盎格鲁林镇里,虚度残年。
他重新回到那间铺着中国地毯的书房里,拿出纸笔,认真写下“思远贤弟”这个工整的称呼,便听得院落的门开了。郭德洁驾着那辆林肯小车,缓缓地驶进院角的停车棚。他很熟悉这些声音,这些动作。他知道,一两分钟之后,那个穿着灰呢西服披着玫红色风衣的妻子,就会和以往一样,拎着她那只凡出门总不离身的小皮包,出现在客厅里,出现在书房里,或兴致或气愤或伤感地讲述在外面的遭遇。
李宗仁放下笔,把转椅扭向门口,迎接着那位到纽约去检查病情的妻子——她的乳病最近又复发了。这老病已经折磨了她数十年。早在抗战时期,她的乳部就生了个疔疮。那年到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去见李宗仁,她就向他讲过。他劝她及早回桂林或是到汉口的医院去医治,她却羞于以乳部示人,不听李宗仁的劝告,每日只用万金油涂抹止痛去痒。那时,大概这病确实不甚要紧,以万金油医治也能应付过去。自到美国来之后,为追求青春永驻,她千方百计托人搜集雌性激素,定期注射,医师曾告诫过她不可如此久为,性激素用得太多,有致癌危险,她却一笑了之。1962 年,她发觉乳疮硬化,医生确诊为乳腺癌早期,并立即收入院准备施行手术,切除根治。可她唯恐失去一侧乳房而影响体形,且以为医生是小题大作或是为了捞钱而诳人,竟于手术之前夜,悄悄溜出医院。两年半来,乳房时好时坏,她总想侥幸遇上神医妙手,既保住乳房又医愈疾病的两全其美。
可是神医妙手终不可得,近日乳部又痛又胀,她只好再次去医院检查。
“德洁,情况怎样?”当郭德洁出现在客厅里时,李宗仁起身迎了上去。
他接过她手中的风衣,看她那蜡黄的脸,心中估摸事已不妙。
“还是两年半以前的结论,住院,作手术。”郭德洁郁郁中带着几分惶恐。切除乳房的事赖过了两年多,如今还得走那条最可怕的路。五十多岁的女人,在西方并不算老。女人的最大本钱,便是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风姿,真是要失去,她太不情愿。她忆起一句桂平的民歌:“人不风流无二世,花不风流无二春。”“明天就去住院吧,要相信科学。” “你……”她有些气愤:你倒说得轻松,要女人失去一侧乳房,无异于打瞎她一只眼睛!她没有把这些下文说出来,悻悻地走进书房,见桌上的信笺,问道:“你又给程思远写信了?”“我催他快些去和周恩来打交道。我想快些回国,我不愿在这里多待一天!”“你……”郭德洁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一层怒色,“你就那么迫不及待吗?五年前我就到香港为你归国的事活动过,你不是不清楚。共产党,有那么好说话吗?”“我相信思远,也相信周恩来。1938 年,徐州撤退后,我在武汉东湖医牙时,就与周恩来交谈过。我认为,他绝不是蒋介石那种奸人!”“我什么时候也不反对你回去。我也不想拉住你的后腿。我赞成叙利亚一位先知的格言:夫妻好比同一把琴上的弦,他们在同一个旋律中和谐地颤动,但彼此又是独立的。”郭德洁在皮转椅上坐下来,“可是,回去的事,有那么简单吗?喏,你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那封公开信,显然是要美国抛弃台湾,老蒋还能容得了你! 16 年前,在南京时,他派军统特务沈醉准备暗杀你的事,难道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李宗仁没有作声,他心里应道:“事在人为嘛!要做成一件大事,还能前怕狼后怕虎!”“再说,”郭德洁见李宗仁不语,脸色更沉,“我的病也还没有个结果,你何必那么急呢!”“我当然要等你做完手术。”李宗仁放低了声调,“不过,我们终须一别。
因为你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而我,15 年来一直只是居住新泽西州的一个中国移民。”“我知道我们要分手。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我不是政治家,自然不愿去吃那种阶级斗争之苦。我常常梦见家乡成了但丁笔下的地狱。”“不谈这些,我们不谈这些。”李宗仁知道郭德洁的脾气,看着她那蜡黄而阴沉的脸,他心里很沉重。他估摸她的病已经快入膏肓,割乳房之事再也不可逃遁。毕竟是数十年荣辱与共的夫妻,他愿她健康,“还是先确定一下你明天去住院的事吧!”他们一同来到阳光下的庭院里,忧心忡忡地磋商着,左右为难地讨论着,那气氛与这恬适、雅静且生机勃勃的花园,似很不协调。
31
也是一个花木葱茏、美丽别致的花园式庭院,坐落在纽约市郊区。自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驱车至此,不过半小时光景。
庭院里那幢两层的乳白色住宅,覆盖着既高且尖的棕黄色瓦顶,厚实的墙基和宽敞的廊檐,让人感到古朴与庄严。室外的绿荫下,有沙池、秋千和木马,砖铺的小道嵌在茵茵的草地之中。
天,阴阴的。春夏之交,这地方常常下雨。几只燕子,在厚重的云层下散乱地飞翔。
庭院里很静。雨篷下的台阶上,坐着个穿中国唐装衫的老妇人,慢条斯理地在选择枸杞菜。纽约这地方兴许无人识得枸杞菜是一种佳蔬。这一大堆枸杞菜,便是老妇人刚才到附近路边去拾来的,那里野生着绿茸茸一大片。老人的神情有些惆怅,白皙而多皱的脸上没有半点笑容。她不时抬头看看天色,似乎也讨厌下雨。见燕子在树梢上叽叽着乱飞,她嘴里也喃喃地用桂林话哼起她曾千百遍哼吟过的那首儿歌来:“小麻雀,小麻雀,你有什么不快乐,请你说一说!”自然,她不是唱给燕子听的。这儿歌,她从前常唱给儿子听,后来又唱给孙女听。她常常唱它解闷。儿子和儿媳工作去了,孙女们上学去了,中午都不回来,这偌大的庭院只有“小麻雀”的歌声,证明它不是一座“空城”。
老人今天的心绪有些不宁,以至好几次把枸杞菜的梗子和叶子放错。
以往她做事总是有条不紊的,虽然已经74 岁了,手脚都还灵便。她从古巴到美国来已经七年了。那以前的九年,因为儿子国籍的原因,她不能随来美国,在香港、在古巴,她度过了痛苦不堪的岁月。自到美国以来,和儿子、儿媳、孙女们住在这花园式的庭院里,不仅丰衣足食,还可安享天伦之乐,照说应心满意足了,然而满足总是暂时的。人,总有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情趣。近来,有一件事使她常萦怀于心,她惦念、猜测着、等待着。
她在等他——等她的老丈夫李宗仁。
七年前,她刚从古巴来到这里时,李宗仁常来这花园式的庭院里度过星期天。尽管是流落异国,也比不上以往在北平,在广州时的情趣,但毕竟是一家三代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在她眼里,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业的成功而是家庭的温慰。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追求。
这愿望,在自己的国土上没能实现,在这异国他乡反而体味到了。所以,她快活了好一阵子。那时,她唱这“小麻雀”的儿歌,是唱给四个常打闹斗气的小孙女听的。尽管她们听不懂奶奶的桂林土话,但爸爸只要翻译过一遍,她们便总记得。后来,孙女们慢慢长大,都上学或奔自己的前程去了,她渐渐又感到孤独起来。语言不通,使她不能像在中国那样,到邻里去串门。
而且美国人也没有串门的习惯,有事见面必须先挂电话,得允后才能造访,大不如中国那么方便。再说,德邻近年也来得少了。他自己不会开车,每往来一次,总得要求人或趁便。志圣虽然也会开车,但整日忙着生计,连星期天也不得闲。德洁是绝不来这里的。自二十多年前在灵堂里的那次龃龉之后,她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她听说近来德邻在积极活动回国,这事有成功的希望没有?又听说德洁重病住院,要作大手术,情况如何了?她当然也不喜欢德洁,但毕竟关联着,因而就关心着。她昨夜做了个梦,梦见德洁危在旦夕,而德邻又已离美归去。她紧张得冒了一身冷汗,醒来虽知道是梦,可早餐的牛奶面包,她半口也吃不下。今天虽不是星期天,可她却盼着德邻来,她想见见他、问问他。
她选择完枸杞菜,从那些准备倒掉的废梗中挑了几根粗壮的,兀自到屋后院墙边的沙土堆上去插种。每次都这样,那块簸箕大的沙土堆,已经快插种满了。这枸杞菜也贱,叶儿被摘光了,只要将梗子插在土里,每日浇些水,它又活转过来,渐渐地吐出嫩绿的新叶。“人如果能像枸杞菜这样,白发落尽又生黑发,那该多好!”她想。随即又自嘲地摇摇头,轻叹一声,唱起她那首“小麻雀”来。
快10 点钟了。房间里桌上那只方形闹钟,是她特意叫儿子幼邻买的。
她不习惯戴手表,她觉得戴手表是一种负担。她也不爱那种显示数码字的电子钟,难认。就这工工整整标着几个数字,明明白白走着两根长短针的钟,她最顺眼。中午的饭菜,只需要从电冰箱里取出来热一热,再说一个人的饭菜,大可以简简单单,她根本没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