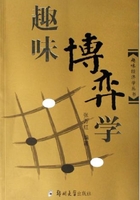恃蛮横妙桔霸宫女◇逞意气天枢救绿萼
且说天枢领着绿茵出了含凉殿,穿花拂柳往东宫来,却撞着见君的宫女云荔在殿门外垂手侍立。云荔素日在太子跟前是极体面的,哪有像今日这般在宫外伺候的境遇。天枢心知有异,一面踏入蓬莱宫一面道:“姑娘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云荔连忙答应着进来,跟到中庭天枢停住了脚步她也便站着。
天枢站在庭中央四顾无人,便悠然问道:“你家小姐哪去了?”未等云荔作答,陡然话锋一转,又道,“你休要想瞒我,我今儿个可是来问她要债的。”
云荔嫩白面皮上潮红如霞彩,鬓发间密密汗珠淌了下来,慌忙道:“不敢。我家七小姐昨夜突然身子不爽,已请过皇后娘娘回府歇着了。”天枢听出她话里有不实倒也不存心为难她,哼了一声往太裳殿方向走。云荔拦住她,急着道:“公主,太子殿下这会子不在松露院却在枫霜院呢。”
天枢心头生恼,故意装着糊涂问:“这我可就闹不明白了,君姐姐既然不在院里,他又是跑去作甚的?”边说边甩袖执意要闯。
云荔急得脸上没了一丝血色,咬了咬牙才算把要紧话都漏出来:“我不曾有心欺瞒公主,只因着方才皇后娘娘审问过六公主苑里的祸事,说了六公主几句,罚她闭门思过不得出苑门。又将她苑里的宫女都换给枫霜院里的三公主,要三公主亲自管教那群不给主子长脸的奴才。”
天枢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又气恼又顿足,叹道:“了不得了,这可怎生是好?”皆因她这三姐行事惯来狠辣又不留情面,时有体罚宫人的坏脾气,稍稍出得个什么差错就要撵人去掖庭。宫内众人俱是以侍奉这位公主最为苦差,是以六公主苑里人此番应是给那清韵连坐着吃了回大苦头,反倒是原本伺候三公主的一群人算是因祸得福了。
天枢心头萦思百转千回,脸上又故作诧异,问道:“这么说,你家小姐是同我三姐起了冲突才出宫的?”
云荔面上又一红,道:“我家小姐闹性子同三公主赌气,说六公主那的一个叫绿萼的姑娘是她早先同太子提起过的,这回正好可以跟三公主要来。”顿了顿,又道:“三公主不留情面怎样都不肯应允,我家小姐这才生了恼一气出宫,只留下太子这会子还在三公主殿中理论呢!”
一语未了,身旁绿茵已“啊”一记哀叹出声,天枢倒不想是这般缘由,感服激荡之下更觉见君的脾气性子爽朗亲和,故此就愣住了。半晌,她才道:“不是你家小姐要的人,是我跟二哥哥讨的。”闻得此言,云荔惊得瞪大了眼。
三人遂一同来至枫霜院中。日已中天,东宫里庭院寂寂悄无声息。天枢在垂花门外整饬好衣裙方要入殿中去,却见太子身侧的小太监正从里头退了出来。那小太监见了天枢似是有些慌乱,正要进去通传,天枢不愿驻足,一鼓作气只管往里闯,小太监无法,只得轻轻击了两声掌向里头暗示。
天枢进得殿去,殿前的正方白玉砖上遍布金辉,三公主妙桔正在九凤雕花窗前肃然危坐,太子立在石榴花阴里作陪,余下的宫女太监乌压压地跪了一地,无人敢咳嗽一声。
天枢带着云荔绿茵二人走至廊上,肃下身去请了太子与妙桔安。正要开口,妙桔一见天枢就知道此间事已经走了风,料着瞒不过,便抢先冷笑道:“十三妹也是来给未来的太子妃当说客的?”
天枢心中虽有不满,面上却不肯露出,反而顾左右而言他道:“再没有的事,我可不知三姐姐同君姐姐怎的又拌上嘴了?只是刚有个我母妃殿里的执事婆子到我苑里来悄悄告诉我说,君姐姐这两日身子懒懒的吃不下东西又提不起兴致。我念着她素来待我可亲,今日又碰巧得了幅新画卷,所以想来找她去我那里赏鉴赏鉴。”
妙桔自然不信,横眼朝她身后云荔剜上一眼,哂笑道:“什么样的奇画?几时也让我去瞧瞧?”
天枢却不再理她,转而向一旁的太子问东问西的,又劝道:“可是二哥又给君姐姐闲气受了?竟勾得她躲回府里去?”肚里赶紧念一声“老君保佑”,心想这二人若是真生分了,她的归仙之途必将更为坎坷。
太子尔雅笑道:“只有我在她跟前受气的理,每每劝她养身子,她都要与我耍性子呢。”
天枢垂头想了一想,舔了舔唇好整以暇,道:“倘若是什么小症候倒也不打紧,要是真生的是场大病的话,可得赶紧要请太医瞧瞧。君姐姐一贯身子娇弱,不比三姐姐一般保养得贵重……”目光一转,盯上了妙桔手边的碧玉碗,不禁要赞叹一声,道:“三姐姐的芙蓉清露倒是稀罕,可否赏妹子两口吃?”
妙桔正等着她话头转过几转再转回自个儿身上来,见她开口讨要便干笑一声,道:“可巧了,这还正好是见君她昨日派人送给我尝的呢!妹妹若喜欢,只管拿去。”语毕,略抬一抬手,已有个小太监上来取了一只茶盅就着镶金羊脂玉壶嘴斟满,双手托着躬身送到天枢跟前。
天枢眯了眯双眼,伸手接过他递来的玉盅,触手间冰气袭人甚是冻手,不禁要扯扯嘴角,就着玉盅抿了一丝,道:“这露委实能祛心热解暑气,三姐姐殿里的都是好物。自然,人也是好的。”
她回过头去暗示了绿茵一眼,要她指给她瞧哪个宫女是绿萼。绿茵自然会意,一努嘴朝就近花阴挨着太子跪缩成一团的那名少女展颜一笑。天枢拿眼瞅去,见那少女十五六岁年纪神态镇定自若,隐约透出三分英气,额上还有一道淡白色的疤痕。
三公主与六公主同争见君府上的笙二公子也算是一桩宫里人暗地里皆知的秘闻,私底下饶舌说起时对两位公主的境遇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笙二公子虽对她俩都从容相待恭敬有礼,但究竟是要对温婉柔顺的六公主另眼相看一些,待三公主却是多有回避礼让三分。
见君家姑姑也有意向皇后求聘六公主下嫁,皇后自然是欢喜亲上加亲就私下同意了。谁料不知哪个看不牢嘴的底下人到妙桔跟前一搬弄,让她得了风声知晓了此事,自此便左右为难妙柑宫里人,还总要逮着空就亲自来芳菲苑里指桑骂槐地折腾。
绿萼那会子刚被拨到芳菲苑中当差,见自个儿主子受了委屈镇日里坐卧不宁,实在是心疼不已。有一日,绿萼看不下去又火了烈性子,脱口而出道:“我们公主安分守己,与笙二公子才是佳偶天成的好姻缘!”气得妙桔当即一个耳刮子甩得她磕破了头,再命人将她罚到掖庭宫中禁闭三个月。妙桔又与皇后撒泼赖娇了一整晚,皇后耳根子本软拗不过她,已生出悔意要同那姑姑毁约,却又为难寻不着可用来退婚的正经理由。
恰逢那时北边落叶城战局告急,笙二公子不耐烦留在京中敷衍妙桔,遂自请赴北疆驻军镇守,第二年冬天就立下赫赫战功。妙柑日也盼夜也盼地盼他回京主动迎娶,孰料天意弄人却盼来了西夷首领处的遣使,提出愿婿周以自亲,娶六公主为阏氏与天朝修好。明眼人皆知这是妙桔生母越华妃与她胞兄东郡越王共同图谋打的好主意,只可怜六公主芳情一段终成虚话。
妙桔冷着脸暗忖她今日来意,多少也料着几分,轻哼道:“枢妹妹若真有心惦记我殿里好物,我倒也不是那般小气的人不会疼惜着不给。有些个精致衣裳是前几日皇后娘娘打发人送来的,大抵是些袖衫襦裙对襟褙子之类,妹妹若喜欢,只管取了去。”
天枢知她搪塞,自然也看不上那些个平常衣饰,泰然自若道:“阿枢那衣衫子倒还不缺,只是想来跟三姐姐要个原先伺候六姐姐的宫女去。”
妙桔心头大怒,暗道好你个小蹄子竟也是来讨人的,面色黑了几分,口吻冷峻道:“原来妹妹也是眼巴巴地来图谋我这的人呢!今儿个瞧着这阵仗,二哥哥与十三妹妹是要联合着来排挤我了?”
天枢冷冷道:“三姐姐这番话从何而起?我只说我想来要个六姐姐身侧的人过去,与君姐姐的事又有何关联了?”她装作不知见君已向妙桔讨要过,也不怕妙桔心头见疑,只管自顾自说下去,“有个叫绿萼的宫女平日里专理六姐姐那的琐事,我偶尔几回遇着了心里欢喜便多看了几眼,果真是个办事妥当的好人材。此番六姐姐有意将她留给我用,我今早正要去跟六姐姐讨来使唤呢,谁料说她宫里的宫人都给派到三姐姐这来了。”
天枢故意一顿,妙桔哽了一口水在喉咙止不住地咳嗽,却无一人敢上前替她捶背顺气。到最后,还是太子看不过眼,半扶着她窄肩叹道:“你平常就爱动刀动枪的又偏偏伤过心肺,还这样易动怒的话——”
妙桔当即厉声道:“我好得很,多亏二哥哥惦记了!”当即愈发暴跳如雷,几步冲到那绿萼跟前劈头又是一耳光,骂道:“合着你就是个吃里爬外的东西!想当年你在我大哥跟前侍候时我大哥待你何等亲善?!谁晓得我母妃与大哥才出了宫,你就一心赶高枝儿捧着那六丫头去。活该你个没眼色!这回你就等着跟她一起滚蛮子地上去吧!”
绿萼被抽翻在地上动弹不得,天枢也不理会妙桔震怒反应,走到太子跟前将绿萼从地上搀起来,又直直地盯着妙桔道:“好端端的三姐姐打我的人作甚?若三姐姐不信我刚才那话,可以遣人去寻我母妃问问。六姐姐那话可不是平白无故说的,况且,还正是在我母妃跟前说的。”
绿萼跪得良久双膝发麻酸痛,被她扶着也颤巍巍地站不住脚。天枢忽然想起昨夜的清韵,也是这般眉目姣好弱不禁风,鼻端不禁也是一汪酸水。
枫霜院前此刻极静,只听得到一瓣酴醾花飘落而下,叶丛中悉索一响。院中鸦雀无声,妙桔心知母妃大事未成之前不可轻举妄动与文家人翻脸,无奈她情绪暴躁惯了,想亦未想就随手操起黄花梨木案几上的羊脂玉瓶狠狠地向石砖上掼去,那玉瓶子被砸得玉屑粉碎片片亮白,日头光一照就如同上好的玉镜子一般倒影出五色斑斓的华彩来,刺得她额际好一阵晕眩,双目前明晃晃地睁不开眼。
天枢愈发从容不迫,面无表情缓缓道:“若是三姐姐无异议,我便领这宫女告退了。三姐姐好生将养身子,阿枢改日再来瞧三姐姐。”
妙桔缓过神来笑道:“不过是个宫女,我哪能真为着她跟妹妹动气了?不过这领人的事也不是一会子半会子就能成的,你先回去,等我向皇后娘娘禀过后再去录个档,随后再派人将这宫女给你送过去……”
天枢不等她说完就离了东宫,在殿门口又跟云荔嘱咐道:“你家娘娘可是答应我中元赏会的,她若忘了,你得要替我提醒一回。”云荔笑盈盈地应了。
仲夏时宫里的光景极好,太液池两岸绿槐高柳枝繁叶茂,一片葳蕤中有蝉鸣嘈嘈声起,暖风薰得池水澹澹生烟。小荷初开清新素雅,石榴花却已是如火如荼如天边翻涌的锦霞,花深如海。天枢站在花海柳荫光影处,慢慢地向绿萼道:“你,先回芳菲苑去吧。等六姐姐出嫁了,你再到我宫里来向攸伶要个差事。”绿萼的嘴角微微在颤抖。
夏日晴好,湘妃竹帘外的暮光斜斜地渗进含凉殿,在青砖上烙成一格一格的浅浅灰印,印痕或浓活淡。天枢挺直腰背跪得不动不摇,一股子的正气与倔强气隐约间透出面来。殿外的阳光逐渐黯淡下去,贤妃的脸色晦暗不明,道:“有了这半会子的功夫,你也该想明白了,今日之事你可知错?”
天枢屏息静气,从容道:“母妃教训的是,女儿实在是不该在三姐姐那里跟她顶嘴,未能自重身份,也丢了咱含凉殿的清白脸面,教那班子的闲人白瞧了笑话去。”
贤妃见她有认错的意思,便和声道:“我也不知你今日是着了什么魔障了,往日你可是最不生事最叫我宽心的。你既知错,且将那绿萼再寻个差错打发回枫霜院去。”
天枢静默半晌过后,忽又磕下头去,道:“女儿不肖,恕难从命。”
贤妃的和颜悦色僵硬在半空中,又沉下脸去,道:“现放着你苑里的那些个人还不嫌够,我说再拨两个精明能干的去你又给退回来,可是存着心儿要与我生出嫌隙来呢?”
天枢恭声道:“女儿绝无半点子这样的意思,母妃恕罪。”
贤妃的眉梢剧烈地颤动扭曲起来,愈发动气,道:“你既要与我怄气,暂且跪着不用起了!”说完,哼的一声从天枢低垂的眉眼前疾步而过,那拖曳得老长的裙裾上,半月扇形银杏叶纹样的金缕丝线灼灼生采。
天枢神色宁淡,安静地望着母亲从她面前经过,那背影轮廓袅娜又不失庄重,那人是撑着这整座含凉殿的主心骨……瞧着她走远了,天枢才敢伸手摩挲个两下后颈上的腻滑,那里早已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浊泥黏糊着后脑碎发纠缠出千百结,待取出方帕子稍稍一抹揩,素净白绢上登时画出一道浅浅牙白的淡痕。
正是:一片风情,怎堪画图。红莲绿芰亦芳菲,不奈金风兼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