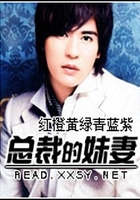现在好不容易有片刻消停的时候,她起身然后走到屋内。
打通东曜光的电话,“光啊,小风在外面睡着了,我也弄不进来,你还是过来把她弄屋里去吧。”
东曜光看着躺在床上睡的恬静的女人,蹙眉,伸手触摸着她那紧锁着的眉头。
不知道她梦见了什么,眉头皱得这么紧。
周英姿使出浑身解数躲过男人的攻击,累的要死也不见男人有动弹的迹象。
“夜琛……求你别折腾了……好好一个午休就被你给浪费了。”周英姿看着身上作威作福的男人,就像是永不知餍足的兽。
夜琛吻了一下那喋喋不休的唇,“好。”蓦地一顶,周英姿失声,然后忙捂着嘴巴,看了看门口,幸亏没事,士兵们都回营房了。
“我真想掐死你,夜琛……”几乎咬牙切齿的,她怒瞪着头顶上方的他。
男人则是享受的整理好两个人的作训服,然后躺在她的身材,“你舍得?”
难得闷骚的男人话变得多了起来,她白了一眼,有什么舍不得惹自己生气愤怒的少一个是一个。
“老婆,能不能在训练的时候,你离那个男的远点儿?”夜琛一脸醋意的看着她,这些日子老是看见一个男人在她的身边鞍前马后的替她做这个那个的,拜托他才是正室,女人的男人,那个男人难道就没有人告诉他,他夜琛就是团长姐夫么。
周英姿莫名的看着他,“谁啊?”
还谁啊,看来在她身边围绕的男人不止哪一个。
他使劲儿的看着她。
“我要是真的喜欢部队里的男人,还找你干嘛?”起身将衣服整理了一番确认无误看了一眼还满脸委屈的男人,他这是怨夫吗?
在听到她说的以后,夜琛点了点头,“也是,我那么优秀,你怎么可能去选择那些个劣质男。”心里顿时宽松了不少。
额……
他还真是闷骚外加自恋的很。
训练场上,依旧是男女分别站两队,而团长大人则是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
自家的男人不得不说魅力十足,那举手投足间都透着狂野霸气。
教官则是不停的喊着各种口号,折腾着新兵们。
有的则是挨不住姿势都走了样。
周英姿起身双手背后,脸上架着一墨镜儿,那叼劲儿暴帅。
手机铃声响起,她掏出接听,里面传来的声音,令她眸子一沉。
历练的时刻到了。
雨不停的在下,而那些个站在原地待命的人们则是一脸严肃的等着发布命令。
“在C市的边界处出现一伙非法持枪贩毒国境的人在午夜两点准备进入我国境内,周英姿你要调配你的精英前去堵截,防止毒品进入我国境内。”那边下达的醉高级的指令,周英姿蹙眉,特警已经去了好几拨,而且久攻不下死伤人员不少。
看着已经整装待发的那些人们,周英姿立马信心十足起来,他们是什么,是特种兵是所有想做都做不到,最为奇异最为强大的一支特殊的部队。
而夜琛不是军人只能提心吊胆的看着自己的女人提枪上阵,他走到正在检查装备的周英姿面前一把将她拽到怀里死死的搂住,“不要去……”
“只是一小部分,别担心。”她拍了拍他的肩膀故作轻松,天知道她心里也在同时打着鼓,那队贩毒非法想要越境的人团伙足有上百人,而且都带着杀伤性武器,线人也已经被他们割下了头颅,只要想到这里她心里一阵愤懑,那些个畜生她一定要全部逮着判死刑。
“我能不担心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他狠狠的吻着她的唇,而周英姿不以为然这种事又不是头一次遇上,弄的怪怪的,她推了推他,“就是围剿,没事,等我回来……”在他的脸颊上印下一吻然后转身消失在雨幕中。
夜琛的心开始慌乱起来,在看到她那背景在雨幕中消失不见,有着一种将要失去的感觉,不对,不能想这些有的没的,她一定会回来的。
夜晚的雨过后,早上的天还是阴沉沉的,没有人回来,训练场上还有一个连的人在训练着,散打之类的,他站在那里定定的看着,整整一天。
碰……
花瓶碎裂的声音。
叶凌风看着那掉在地上的花瓶,心里莫名的有些不安。
东曜光忙将地上的破碎的碎渣收拾掉,看着失神的叶凌风,“怎么了?”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有一个人似乎被我忽略了。”她仿佛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对他说,然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忙跟东曜光要了手机。
拨打周英姿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应该是在执行什么任务,你不要太紧张了。”难得的东曜光柔声相劝。
叶凌风则是直摇头,不是这样的,那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她忙拨通了周英姿父母的电话,接通后那边说是跟夜琛一起去了部队。
辗转一番,终于打到了夜琛的手机上。
“她出任务去了。”夜琛此时在屋内走来走去,他的心跟叶凌风一样,有着不安,紧的透不过起来。
“什么时候去的?”叶凌风握着拳,然后慢慢撒开再握上,希望不会有事。
“两天了。”在说到两天的时候,他看见两辆军用卡车回来,忙挂断电话跑了过去,看着一个接一个下来的士兵,身上都带着血迹,估计都受了轻重不一的伤。
一一问着团长呢,没人回答,均是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
水敏被人搀扶着下来,在看到夜琛的时候,她走到他的面前,语气有点儿哽咽,“团长姐夫……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咯噔……
在听到水敏的话的时候,感觉什么东西碎裂了,他握紧了拳头紧盯着水敏。
“团长……她……她……”水敏的声音哽咽着几乎话都说不全,她是亲眼看见团长跳入了敌人的火线里,为了救那个新士兵,那炸弹的声音至今还响彻在耳边。
而夜琛只是僵硬着身子麻木的看着军人们将一副担架在车上抬下来,上面蒙着一块白布,血迹斑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