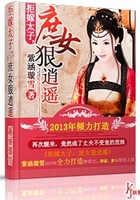在赵构的记忆中,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光:开始于十六岁盛夏,终止在十九岁那年的初冬。
遇见邢蔓,着实是一场意外。那一天,是他十六岁的生日。那一天,按照皇家的规矩,他自宫中搬出,有了属于自己的府邸。
站在自己的新居里,他笑意盎然,这一天他等好久了。房子不是很大,位置也有些偏僻,但这是他的家,虽然朴素却比那个外表豪华气派内里暗无天日的皇宫好上千倍万倍。
在府中前前后后看了三遍,总觉得院中空荡荡的太过冷清,想起母亲最爱桂花,便兴致勃勃的决定亲自去买两株回来种在院中。
然后,他便遇见了邢蔓。彼时,她正被一群恶少围在当中肆意欺辱调戏。
十六岁的赵构正是一腔热血,疾恶如仇的年纪,在宫中隐忍憋屈了多年的怒气,在看见这一幕的时候瞬间爆发了出来。他忘了自己是怎么出手的,总之,等他清醒过来时已经将那帮纨绔子弟通通揍了个鼻青脸肿。看着他们仓皇而逃,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
被欺负的少女面无表情的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这才抬头平静的看着他,淡淡道,“多谢。”
赵构呆了呆,难怪她会被人欺负。那一双妖异的紫瞳,会被人认为是妖怪吧?这一刻,他从这双平静的眸子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直一直被人欺负,咬紧牙关默默的忍受,在心里想着总有一天要让那些欺负过自己的人付出代价。
“你愿意跟我走吗?”他脱口而出,这个少女让他莫名的感到一股熟悉感。
“跟你走?”妖异的紫瞳微微闪烁,充满了不安全感。
“是的,跟我走,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欺负你。”他向少女伸出手。
偏头想了想,少女将手放进他的手心,对他展颜一笑,“我叫邢蔓。”
后来,他便娶了邢蔓,在他的兄弟们都三妻四妾花天酒地的时候,他与妻子情比金坚,举案齐眉。再后来,他奉旨出使金国。待到回来的时候,繁华如流水的东京已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果然如他年幼时所期待的一样,欺负过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只是,他的心中没有一丝喜悦。看着自己破败的家,心里好像戳进了一个鱼骨,随着每一次呼吸而痛彻心扉。
他历经坎坷,九死一生的回来了,邢蔓却被俘北上。他们在命运的捉弄下,擦肩而过,再无相逢的机会。幸而,邢蔓临危不乱,赶在破城前将他们刚刚满月的孩子托付给了府外的乞丐。那乞丐也算是忠肝义胆,只因平日里多受赵构府上的恩惠,竟一直抚养着这孩子,等到赵构回来。
在东京待了几日,一份密旨传到,赵构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筹集兵马救驾。于是他连夜给各省各地的武将们送去了文书,他那风流老子和软弱哥哥的的死活他其实一点不在意,他只想从金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各地的回信倒是很快便送到了,自然是纷纷响应,一个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赵构粗略算了一下,各地的兵马加起来竟然多达百万。
只是,这百万大军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等来的倒是金人的追兵。无奈之下,赵构只能带着城中残留的哪一点老弱残兵踏上了艰难的逃亡之路。他自然等不到那百万勤王大军,因为那从始至终就是个弥天大谎。百万大军,光每日的军饷便是极大的消耗,日渐空虚的国库怎么养得起。
那真的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日子,为了得到士兵的支持,他不得不娶了吴玠将军的女儿为妃。每天没日没夜的赶路,时不时便遇到金人的追兵,露宿荒野自不必说,很多时候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跟着他一路走来的士兵越来越少,每日都有人死亡,所有人都已经快要撑到极限。终于,在一场混战中,他手上一时脱力,摔下马来,伤势虽不严重,但他就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并没觉得有多难过,不能再有孩子就不能有吧,反正不是他和邢蔓的孩子他也不想要。历时一个多月的艰难逃亡,他终于到了扬州,本以为能稍稍缓口气。谁知,不过几日,竟冒出个“苗刘兵变”来,逼他让位。
心中虽然气愤,可那时对皇位并无多大执念,反正也是让给自己的儿子,让便让吧。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年幼的儿子在这连番的颠簸和惊吓中一病不起,没过多久竟夭折了。这样大的打击,让他当场呕出血来,接着便是大病一场。
而后韩世忠和张俊起兵勤王,活捉了苗刘二人。于是,赵构病愈后下的第一道旨意便是将这两人处以醢刑(剁为肉酱),自此他心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深刻的意识到,没有足够的权利,便只能被别人威胁,他从心底恨透了武将也怕透了武将,终他一身他始终不肯彻底的相信武将,无论此人多么忠诚,他总是时刻提防着武将们拥兵自重。
直至后来,他在应天府正式继位。虽说是当了皇上,但天下并不太平,前有金人虎视眈眈,后有各省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匪患猖獗。待到统治慢慢巩固下来,他才意识到原来已经很多年过去了。看着木匣里黯淡了色泽的翡翠耳环,他忽然意识到,他和邢蔓怕是永远也等不到破镜重圆的那一天了。
他开始听从大臣们的建议纳妃,为了巩固皇权,这样的政治联姻也是必要的。只是不管他纳多少妃,中宫之位永远是空着的。娶邢蔓的时候,他许给她的是妻子的位置,所以,任后宫之中的妃子们都得你死我活,皇后的位置他绝不会给任何人。
建炎四年的时候,他的妹妹柔福突然从北地逃回来。面对那张出落的竟和邢蔓几乎一模一样的容颜,他喜不自胜。对这位失而复得的妹妹极尽宠爱,为她招驸马,赐她府邸,赏她珠宝玉器。每日只要得空,他总要召这位妹妹来聊聊天喝喝茶。
谁知,这样的日子竟也没能维持多久。他好不容易才从金国接回的母亲竟让他杀掉柔福,母亲一口咬定这个柔福是假的,但赵构心里明白,柔福不是假的,相反正是因为她是真的,母亲才急着要杀她灭口。
一边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一边是唯一能给他温暖的妹妹,赵构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陷入这样的境地。最终,他下旨杀了柔福,自小他便看着母亲为他吃了太多的苦,他无法不孝。
只是,这一道圣旨在杀掉柔福的同时也杀死了他的心。哀莫大于心死,亡心——忘!自那一日起,他忘记了十九岁的赵构,忘记了什么是温暖,忘记了很多很多,甚至他不再想起邢蔓。
就这样行尸走肉般的过了五年,没有任何预兆的,那个女子如同一只突如其来的蝴蝶,撞进了他的生活。他原以为他大概就会这样木然的过完自己这混乱的一生,从没有想过已经死去的心还能再次跳动起来,这具日渐衰老的身躯还能再次感觉到温暖。
他伤心的时候,晚镜会安慰他;他不信任她的时候,她会很生气;他苦恼的时候,晚镜会对他说,“我会帮您。”
原以为晚镜是在乎他的,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都对她来说只是演戏。原来,从始至终,在林晚镜的心里,赵构就只是“师父托付要帮助的人”和“杀死义父的仇人”而已。
可是,即使知道了真相,他却还是无法恨她。他意识到,他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叫林晚镜的女子。为了能留晚镜她在身边,他不择手段的散布消息,一步一步将她逼入绝境。他以为这样晚镜就会和他回来,可是,他又错了,他爱上的这个女子竟然那样的决绝,宁愿选择死亡也不肯和他回宫。
她说,皇上你把我当成谁了?
她以为他把她当成了邢蔓的替身。可他真的没有,他想要解释,话到嘴边终究还是咽了回去,解释了又能怎样呢?晚镜根本不爱他,无论怎样的解释便都没了意义。
皇帝又怎样?有了全天下最大的权力又怎样?到头来,还不是一无所有。保护不了最亲近的人,也得不到最爱的人。
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
回宫没多久,赵构便将皇位让给了太子赵昚,这个皇位他实在是坐得太累了。
纵观历史,大约他是唯一一个在这张龙椅上坐累了的皇帝吧?坐在德寿殿的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赵构有时会这样想。暖洋洋的日光照在身上,他觉得自己随时可以死去。人还真是奇怪,以前怕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差的好像随时便会死掉,如今一心等死,却反而越活越精神了。
淳熙十四年深秋,赵构病重。
病榻前围了很多人,他的皇后和妃子们,已是皇上的赵昚,他最疼爱的小孙女,还有朝中的老臣们。他吃力的抬眼一一望过去,真的很多人,只可惜,没有他想见的那一个……闭上眼,一滴清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滑落,他深深的呼吸,积攒着最后的力量。
颤颤巍巍的从枕畔取出一道圣旨,递到赵昚手中,“皇上,这道圣旨我拟好已经二十年了,我死之后,请皇上以你的名义替我宣布它吧。”
“父皇,您为何不亲自下旨?如果这样的话……”赵昚一直在强忍着眼泪,终于在看完这道圣旨后泪流满面,那是一道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的圣旨。
“如果不这样,晚镜一定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你不知道,她是真的会说到做到的。”长长的换了口气,“即使她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我也希望她能记得我,哪怕是因为恨。”
赵昚握着他的手,哭的不能自己。
无神的望着高高的屋顶,“你看,晚镜说的没错,我果然是非常自私的一个人啊……”他说着,慢慢的笑了,仿佛回到了自己最美好的十六岁。
“我叫邢蔓。”紫眸的少女将手放进他掌中,灿烂一笑。
“你把这枚耳环带着身边,就当是我陪着你。”怀有身孕的邢蔓倚在他怀中,泪眼婆娑。
“九哥对我最好,我最喜欢九哥了!”小小的女孩儿抱着他的胳膊,欢呼雀跃。
“九哥,恭喜你,你终于要成为孤家寡人了。”幽暗的监牢中,柔福用一双紫色的眼瞳深深的看着他,低低的笑。
“皇上,您把柔福和晚镜当成谁了呢?”苍白如死的女子笑得温和,摊开手掌,里面躺着一只绿的刺眼的翡翠耳环。
“这是自私如你,永远也不能理解的感情。”消瘦的背影蹒跚离去。
多么可笑,居然直到要死的这一刻,他才终于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做错的又是什么。
仿若回光返照,他口齿清晰的开口道,“若有来生……”
赵昚急忙凑过去,他却没有说完,一口气就此断了。手无力从床边滑落,一对翡翠耳环从手心掉出来,摔成数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