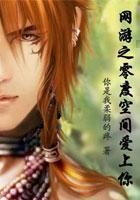正在这时,和颜悦色的上帝使者则在我们面前出现。
他站在火焰燃烧不到的山边,
唱道:“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
他的声音比我们活人的声音要响亮得多。
“圣洁的灵魂们,倘若事先不让烈火咬上一口,
你就不能向前行进:进入火中去吧,
你们对烈火另一边的歌声不会充耳不闻。”
但丁《神曲》
一
三月的天气时冷时热。春天是有风的季节,东京似乎也有些像北京,只是没有那些超过多少级的大风。天气预报往往会说今天是春天第几场风,却很少提到风的级数。小草对天气预报的春天第几场风的概念总是搞不清楚。风里时时飘来花香,提醒人们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不过,风也给日本人带来了各种刺激人感觉器官的花粉。一到春天,被花粉症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不少,包括日光自然公园里的猴子也饱受花粉症苦痛的折磨。电视里看着猴子们喷嚏不停、流泪不止、受苦受难的样子,解说员同情地说:
“可能的话,真想给它们也戴上口罩。”
中村良一回来了。当千代拉着小草下二楼来到客厅时,沙发上坐着丽子和一个男人,不用说,这就是丈夫中村良一。
“这就是杨小草,请多关照。”丽子给儿子介绍儿媳。
小草向良一看去。只见对面沙发上坐着的良一身穿白色羊毛衫,人很清瘦,两手端放在双腿上,修长的手指和指甲苍白而少血色,手背上布着青筋,脸也同指甲一样苍白。他脸部多处都像母亲丽子,如果不说有病的话,谁都会觉得他是个面目清秀的文弱书生。
听母亲介绍小草,在沙发上正襟危坐的良一身体微动一下,清秀的面部略显紧张,朝小草点了点头。
见他同自己想象中又踢又打的精神病患者完全不一样,小草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她急忙向丈夫良一深深鞠了一躬,对他说:
“我是杨小草,从今天开始请多多关照。”
说完这些,她偷眼望去,只见良一望着自己,眼睛里似乎现出了一丝笑意。别说小草,就是坐在旁边的丽子和千代本来也都神情紧张,此时她们俩也跟小草一样都松了一口气。
丽子赶忙对小草说:“良一今后托付给你了,请好好关照他吧。”
小草也连忙点头答应。
下午,千代还有小草陪良一在院子里看花,喂池子里的锦鲤。良一的样子也显得很有兴致,只是不开口说话,晚饭时也如此。
晚上十一点左右,丽子领着良一推开小草的房门进来,拉上小草和儿子来到二楼的另一个房间,告诉他们这是他们夫妇的卧室。这个房间从小草来到中村家就一直锁着,今天是第一次进来。
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收拾得洁净无比,不用说是千代在几天前就收拾好了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对面是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旁边有一个长沙发,沙发前面的玻璃茶几上摆着一盆鲜花。说是鲜花,仔细看,都是一朵朵藕荷色灯笼状的小花,别有一番味道。床头的左边靠墙的地方摆着一个很大的梳妆台,梳妆镜的两边是两排多层小抽屉。床头边的地面上有一个长脚地灯,整个房间布置得如同宾馆一般。
丽子把二人领进房间,说了声“晚安”后就退了出去。
丽子一离开,房间里就陷入了一片沉默。良一和白天看到的情况一样,依然在沙发上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思索着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小草也不知道。她坐在梳妆台前面的椅子上,也和良一一样思索了一会儿,仍然不知如何是好,无奈只好和衣躺下。
小草闭了一会儿眼睛,见床头柜上的电子钟显示0:00,望了望依旧在沙发上思索着的良一,便叹了口气,从床上爬起来,扶他在沙发上平躺下来,给他盖上了毯子。自己又回到了床上,一夜辗转不眠。
第二天早上,全家人坐在餐桌前吃早饭,丽子先用探询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小草,然后目光转向良一,问道:
“昨晚休息好了没有?”
“睡得很好。”良一点头回答了一句。
本来以为良一连话都不会说,没想到他竟说得如此清楚。这意外的发现给了小草信心,丈夫良一既不是连语言都不懂的白痴,也不是又踢又打发狂的疯子。就像母亲望着新生的婴儿,无限怜爱涌上心头,她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呵护良一是自己的使命。
这突如其来的意识如此强烈地冲击着她,使她陡然变得英雄起来,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生存的意志来自于保护一个依赖于自己的弱小生命的母爱。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烈火熊熊燃烧,融化了久久压在心头上的冰块。她仿佛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意义,医治好丈夫的心灵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决心把自己变成鲁滨孙,和良一一起开拓这心灵上的荒岛,使之成为美丽的家园。
动力支配着杨小草,她积极起来,浑身充满了活力。她不再被动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和看电视,而是和千代一起做饭、收拾房间,陪良一思索久坐,在小院里摆弄花草,喂养锦鲤。连上下楼的脚步都变得轻盈了。嘴里有时还哼着儿时的歌曲,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爱北京天安门”、“唱支山歌给党听”,甚至还有在国内就学会了的日本歌曲“拉网小调”和佐田雅治的“男子汉宣言。”
这以前,在丽子和千代的眼里,小草是个寡言少语,漂亮中带些忧郁的女孩儿。但最近小草的变化让她们吃惊地发现,小草还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儿。她给中村家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使这座小楼充满了生机。她们相信良一一定会喜欢自己的妻子,病也许可以彻底好起来,便对她刮目相看,尤其丽子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然而,她们并不知道夫妻二人的夜晚仍然是小草睡床、良一睡沙发。
直到有一天,丽子找小草谈话,询问晚上的夫妇生活,因为头一天小草和千代聊天儿时,无意间透露了这个情况。小草如实回答了丽子的询问。丽子听后,不恼不怒地说:
“知道我为什么辛辛苦苦跑到中国去把你领来吗?”
小草摇头,这本来也是她本人一直都想知道的问题。
“按照优生学,血缘离得越远,生出的下一代才会越聪明健康。我也考虑过找个西方人,但那样做,孩子可能会因为不同于东方人的外貌而遭到其他孩子的欺侮。”
“难道日本人之间血缘就近了吗?”小草心想,对丽子的说明感到不解。
丽子继续说:“良一虽然精神上有病,但身体上是健康的,我希望他早日有个优秀健康的后代,在我有生之年培养成人,将来我老了死了,有我的孙子照料良一,我死也瞑目了。请你理解我的心情。”
疑团终于解开了,这就是自己来到中村家的理由,她原以为仅仅是小夜子那莫名其妙的水晶球把自己引到了中村家。此刻,她被丽子的苦心感动得差点儿掉下泪来,表面上看,似乎只关心自己容貌美丽和热衷于出入社交场合的丽子,却有着做母亲的平凡而伟大的情怀。丽子说的完全有理,为人之妻,繁衍后代义不容辞。为了中村家有个后代,而且是优秀的后代,即便不是如此,为了报答中村家把自己从困窘中解救出来的恩德,履行这重大责任是自己不容推辞的义务,小草有这个自明。
这天晚上,她没有先躺下,试着拉起良一的手,带他到床边,替他脱好衣服,安排他躺在床上后,自己先坐到沙发上去。看到良一躺在床上安稳地闭上眼睛,小草来到床边,坐在他身边,与此同时轻轻摩挲他的后背。良一对妻子手指触摸的反应先是浑身一颤,接着像头受惊的小鹿一跃而起,满脸惊恐,瞪大了眼睛看着小草。小草见状,只好叹了口气,像母亲拍打怀抱的婴儿,让他镇静下来。
虽说小草不是初婚,经历过男女之事,可让她主动找男人做爱,却实在是难为她。她壮起胆子试着凑到良一身边,开始用手触摸他的身体,可良一除了动一下身,离开她远一点之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使她感到羞愧,便打消了进一步争取的念头。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来到床的另一边躺了下去。这一夜夫妇相安无事,总算睡在了一张床上,可谓有了进步的开端。
接连几天都是如此。
丽子没有再找她谈话,但那眼神分明在探寻。小草惴惴不安,竭力躲闪着丽子追寻的目光,那目光仿佛一把利剑,又像梅花针,刺得小草频频躲避、不敢正视,责任心也每天都在不断地谴责自己。
“你应该懂得自己的处境和立场,良一的母亲是丽子,而不是你,是妻子就要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在这个家庭里,除了给中村家传宗接代以外,你的价值等于零,你坚持的自尊就是自私自利,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这自责不断折磨着小草,令她感到窒息。每天晚上都在上床前鼓励自己一番,可事与愿违,每每一上床,那可恨的自尊心就又出来作怪。
二
这天,小草下定决心,摈弃一切杂念,她在意念上强迫自己想象身边的良一是个人体模型。她开始动手,从上到下抚摸这个人体模型,意外的是良一没有现出拒绝的表情和动作。小草受到了鼓励,进一步大胆抚慰他的下体,人的原始本能在良一身上也不例外,于是在小草的引导下,他慢慢进入了她的身体。一切顺利,多日来的疑虑都成了庸人自扰。
就在小草沉浸在幸福之中,情况发生了突变。身边的良一突然表情古怪,紧接着发出一声怪叫,抓住小草的两只胳膊又啃又咬,长长的指甲深深陷入肉里,疼得她狂喊救命。
丽子和千代闻声赶来,才掰开了良一的手。丽子咕哝了几句,似乎是埋怨小草刺激了良一,牵着儿子的手,离开房间。小草怔怔地坐在床边,脑子混乱起来,连日来对丈夫产生的母爱、夫妻爱都被吓得无影无踪。胳膊上的伤痛,让她头脑清醒过来,自己的的确确嫁给了一个重度的神经分裂症患者。
第二天,中村家死一般寂静,可小草耳边却不时响着良一的怪叫。胳膊上的伤虽然千代给她涂了消炎药膏,已经不那么疼了,但牙印和指甲印历历在目,她陷入了极度的忧郁。
丽子和千代先后到房间里看望她,关心她的伤口如何,并分析说:“良一肯定因为第一次行房,对他刺激太大,以后一定会习惯的。”无论从她们的态度上还是话语里,看不出对小草有责备之意,当然也包括鼓励。
丽子说:“过些天等他情绪稳定了,一切都恢复常态后,再让他搬回你们的房间。”
小草找不出拒绝的话和理由,顺从地点了点头。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丽子对小草说:“良一已经好了,今天晚上和你睡一起吧。”
听了这话,小草先是心颤抖了一下,接着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她没有理由拒绝,也不可能拒绝。首先,良一是自己的合法丈夫;其次,寄人篱下,没有持不同意见的主动权。她所能做的只有祈祷上苍保佑自己和良一能够相安无事地度过这个夜晚。
然而,上苍并没有听进小草的祷告,也许她的心不够虔诚,抑或是命运里注定的罪还没有受完,这天晚上情况更糟。这次已不是小草主动,而是良一不分青红皂白按住小草行事,事后又是一阵狂咬袭击。她下意识地拼命抵抗,可是看似单薄的良一却力大无比,痛得小草紧闭双唇,咬紧牙关不哼出声来,连嘴唇都咬出了血。直到他厮打累了,才倒在床上睡下。
连续几天夜夜如此,大概丽子和千代已经习以为常,听到楼上厮打的声音,不再跑上去保护小草。这天,她拼死挣脱中村良一的扭打啃咬,逃出房门。来到洗澡间,对镜子一看,胸和胳膊血糊糊的,还留着牙印,她不禁悲上心头,号啕大哭。千代闻声赶来,边安慰边替她擦泪。
“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里。”她哭喊着说。
“真是造孽呀,造孽!”千代叹息着,也不断抹泪。这天晚上小草就睡在了千代的屋里。
几天来,她害怕接触丽子的目光,一看到那目光,便提醒自己要报恩。她更害怕夜晚到来,想到进自己的房间,就如同进鬼门关,随时有失去性命的危险,便接连几天都不肯回到自己房间里睡。
这天晚上,丽子吩咐千代把杨小草领到榻榻米的和式房间里。二人一进房间,便看到房间烛火通明。房间的四周点燃了数十支蜡烛,烛烟和地桌上香炉的香烟混合在一起,呛得人要流泪。房中央的榻榻米上,直端端地跪坐着小夜子,她一身白色装束,双眼微闭,摇曳的烛光下,映出了她瘦瘦脸上的庄重神情,衬托着她那越发显得高耸的鼻峰,这一切都使巫女小夜子更加魔气重重。她嘴里喃喃叨咕着什么,双手罩在水晶球上方,水晶球在闪烁的烛光里射出了色彩怪异的光芒,整个房间充满了凝重的神秘。三人并排跪坐,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小夜子的一举一动。
“这屋里有水死鬼!”小夜子突然叫了一声,同时睁开了双眼。三人不约而同被她惊得“啊!”了一声,瘫坐在榻榻米上。
丽子战战兢兢地问:“水死鬼在哪里?”
“就在这屋里,啊!附在她身上了!快!不能让她逃走!”小夜子手指着小草大叫。
小草吓得愣住了,呆望着小夜子,丽子和千代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小夜子倏地站起身,来到小草背后,一把抱住她,嘴里喊道:“快拿绳子来捆住她,不要让水死鬼跑了!”
“快去,取绳子来!”丽子急忙命令千代。杨小草还是楞在地上,任凭小夜子捉住她的双臂。千代急忙拿来一条塑料绳,由小夜子指挥把小草的双手捆在房间的柱子上。这一来,小草只能直挺挺地躺在榻榻米上。捆住后,小夜子吩咐把点燃的蜡烛摆在她身体的周围,说水死鬼怕火,要用火来除。她嘴里念念有词,手里拿着一根燃烧的蜡烛,掀开小草的上衣,把淌下来的滚烫的烛泪一滴滴地滴在她身体上,烫得小草不断扭动身体,哀叫。小夜子又命令丽子和千代按住她的双腿,随手把一块毛巾塞到她嘴里,杨小草只能从喉咙里发出“呜呜”声了。中村良一开了拉门走进来,大概是被小草的叫声引来的,他面无表情,静静地观望着眼前这一幕。
小夜子嘴里喃喃着“滚出去,你赶快从这里滚出去!”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对着小草的身体手舞足蹈地东指一下,西划一下,折腾了一番后,看着躺在地上不动的小草说:“好了,作祟的水死鬼驱走了,拿一碗水来,让她清醒一下。”她端过千代递来的一碗水,喝了一口,对着小草的脸,把含在嘴里的水猛喷过去,接连重复几次,见小草睁开眼睛后又说:“从现在起,她可以回夫妇房间睡了。”丽子和千代赶忙解开绳子,用冰袋和湿毛巾敷在小草被烛泪烫伤处。
“这下可好了,良一是被这水死鬼吓得犯病。”丽子望着小草舒了口气说。
小草仍然躺在榻榻米上不动,她脑子混乱得一塌糊涂,连身上的灼痛都感觉不到了。这是她人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另一个世界,自己莫非真是水死鬼附体?她不想睁开眼睛,害怕触到小夜子逼人的目光,怕那个发出怪异光芒的水晶球。
小夜子把水死鬼驱赶走了,第二天晚上,和婆婆中村丽子一样舒了口气的杨小草怀着某种期望,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而几天前的事情又同样发生了,这次她不光人遍体鳞伤,心也死去,彻底陷入了绝望。
与良一搏斗时,小草先是昏厥过去,醒来后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哪里,只有身上的疼痛提醒她要赶快逃离这虎狼之地。她爬起身来踉踉跄跄摸到大门,冲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