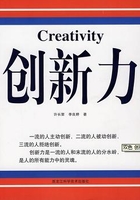两个人对峙半晌,她干脆动手将礼盒的包装拆开了给我。我不经意的低头一看,整个人就愣住了。
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小小的一个纸片,上面用毛笔写着十分潦草的三个字——“一种花”。
我想说点什么,至少移动一下目光。可是我紧紧盯着那片纸张那么久,却始终没有办法说出哪怕一个字来。那是什么,我很清楚。当我还是苏小小的时候,莫北去给肃白泽治病,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建康。那时我住在莫北家,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我喝醉以后变得神经错乱,逼着莫北跟我玩游戏。
当时我在纸上写了“一种花”。原本以为他会被我骗到的,可没想到,纸张交换之后,莫北写的也是“一种花”。
而眼前这一张纸,无疑是我的字迹。
我呆愣了好久好久,才终于沙哑着声音问薛茜:“这东西……”顿了顿,我轻咳一声,说,“薛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薛茜笑了笑,将礼盒放到了桌子上,对我说:“这个东西,莫北一直贴身收着。”她伸手拍了拍胸口,说,“放在这里。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放在枕头下面呢。”
我觉得自己额角的青筋都已经爆出来了。可是细想一下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能找到我?还能确认我是苏小小?虽然我承认自己长的与苏小小十分相像,可是她以前没见过我啊,怎么可能一上来就拿了这么个东西要给我。
再者,她现在这是在暗示什么?按理说,薛茜既然有头有脑,不可能那么无聊,费这么大力气只是为了确认我是不是回去过南齐。难道她是想让我去找莫北?
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回去古代生活。她是做这一行的,不可能不知道灰飞烟灭的事,那她就根本没道理暗示我这个啊。
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这个时候我手机突然响起来,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接了,是奈奈。
奈奈说:“大小姐我现在准备出门啦!”
我说:“好好。我也快了。那个吃完饭到底去哪里啊?”
奈奈咯咯笑着说:“上个月你昏的时候新开了一个酒吧,听说挺好的,叫once。你也没去过呢吧?哈哈……哎我先不跟你说了,我男朋友来接我了。我们吃饭的地方见啊,拜拜!”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半天都有点回不过神来,手指摩挲着盒子,想着还是缓兵之计吧。先看看她下一步怎么办,我也要再探探师父的口风,然后才能出对策。于是清了清喉咙对她说:“薛小姐。虽然不知道你送这么个纸片给我究竟是为什么,但是你如此诚意,我便收下了。不瞒薛小姐,我马上有急事要出门。”
话说到这里,正常人都能明白弦外之音了。薛茜不是笨人,笑着站起来对我说:“那就不打扰了。我今天前来,其实就是想拜见一下,毕竟你的辈分比我的高。现在见也见了,礼物也送到,也就没什么要跟你讲的。不过苏小姐,我说一句——如果我是你,我会活得坦然一些。”
说完,她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向房门走去。
我心里的一股无明火“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
无论在现代还是南齐,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话——这也就算了。关键是,现在这么对我态度不恭敬的人,居然是我徒孙!——这也就算了!最关键的是,这个人,是茜雪!
这我就有点不淡定了。
我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扣着桌面,深呼吸了好几口气,心里一直在对自己说:要淡定要淡定。要冷静要冷静。我犯不着跟自己的徒孙计较。
可是缓了好一会儿,我还是没坚持住,嘴巴吐出“放肆”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阻止自己都已经来不及了。
薛茜的脚步顿住,转过身来望着我,手都已经放在了门把上。
当我还是苏小桥的时候,从来没有责备过谁,归墨总说我的眼神不够厉。可是经过十年的洗礼,当我走过血雨腥风,此刻的我怎可能还是十年前那个唯唯诺诺的苏小桥。
我缓缓靠到椅子里,吸了口气,说:“你是我们师门出来的,现在说来拜见我,应该不会不知道师门的规矩。我受你们这些小辈的拜见,向来依的是张祖师定下来的规矩。若是第一次正经见我,需要提前三日沐浴净体,斋戒焚香。见我的时候,需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我不是为难你。这礼算大,可就算是你那陈姓的师父来给我行这个礼,我也断没有受不起的道理。”
薛茜的脸色随着我的每一个字,变得越来越难看。到了最后,干脆是铁青了一张脸,站在门口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从来不愿意为难旁人。可这个人,自是多年的瓜葛一世的情怨纠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清,自然也就不能用常理来解。
两个人又是静了一会儿。薛茜开口说:“苏小姐……”
“薛茜。”我出声打断她,道,“你这小小的辈分,喊我苏小姐,是不是太不合宜了?还是照着规矩,称我一声太师叔吧。”
若说刚才薛茜的脸色已经是铁青,这个时候的脸色恐怕是死了三年的死尸色了,连我都看得不舒服起来。我挥了挥手,道:“你走吧。”
薛茜仿似很不甘心,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可是我刚才说的话,句句是真,每个字都在理,她也实在反驳不了。于是一个人纠结了半晌,终于还是拉开门去了。
不经意的向窗外一瞥,见到薛茜已经走到了院子里。一边在讲电话一边疾步走了出去。我在椅子上又坐了一会儿,手里握着那片纸,脑子空茫茫的。直到奈奈又打来一个电话催我,我才连忙穿好鞋子拿起手包也走了出去。
和好友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快乐的。一群人,吃吃喝喝笑笑闹闹,转眼就过了九点。又闹了好一会儿,奈奈突然跟她的男朋友陈齐说:“你不是约了刺青的么?我陪你过去吧。”
彼时我正坐在麻将桌前赢的风生水起,奈奈是我下家,陈齐就坐在我和她之间,于是她的声音虽然小,我却听到了,就不经意的问了一句:“约了什么啊?”
奈奈转过头来说:“阿齐想纹身,就约纹身师找个时间过去看图案。好死不死那个人只今天晚上有空。”
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才九点刚刚过了一点点。这么玩下去,不知道要打多少麻将才能等到酒吧开门,于是跟奈奈说:“不然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还没见过现场纹身呢。”
奈奈说好。于是我们先辞别了众人,约好十一点钟在once见面,然后就和奈奈陈齐,三人一起去了纹身店。
纹身店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小巷子里面,连个门牌都没有,就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老板叫阿粥,是陈齐的朋友。房间别提有多散乱。我轻轻扯了扯奈奈,小声说:“你家陈齐怎么会选了这么个地方……干不干净,行不行啊?可别给传染个乙肝什么的,那就不值当的了。”
奈奈估计也被这个场景给弄懵了,跟我说:“阿齐说他是个香港人,技术特别好,所以才来找他弄呢……他说别的地方纹出来的图案都特别俗。阿粥是画家,比较有品位。”说完她凑近一点,再次将声音压低,说,“他想纹我的名字来着,NN。但是印刷体太丑,得找阿粥帮他弄好看点儿。”
我“哦”了一声。心想这陈齐跟奈奈才在一起多久,怎么就纹人家名字到身上了。这要是以后分手了,洗了都得留疤,真是不值当的。可是人家新婚燕尔的,我也不能真说出来打击他俩,于是就往肚子里咽,口上呵呵笑着说:“挺好的,挺好的。”心里却在想,真是好个屁。
过了一会儿,陈齐在里面叫我们过去。我和奈奈走到里面的房间,这才发现这个屋子简直别有洞天。里面应该是工作室,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所有的工具器械有条不紊的摆放着,地板擦的比手术室都干净。我忍不住“哇”了一声。
阿粥抬头瞄了我一眼,眯起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
奈奈正低头看一张纸,这时抬头看我,说:“小桥你快来看,真是挺漂亮的。”
我也凑过去看,又忍不住“哇”了一声。纸上是一个大约我四分之一个手掌大小的图案,看似藤蔓纠缠,仔细辨认,却能发现是两个“N”。美丽又不失阳刚,非常合适。
我在心里赞叹,怪不得陈齐要专门预约他的时间,果然是名不虚传。
可是看着看着,我却突然“咦”了一声。奈奈忙问我怎么了,我摇了摇头。又凑近点细细看了几眼,突然发现,居然跟苏小小后背上的胎记的感觉有一点像。
我想了想,从旁边拿了纸和铅笔,随手在纸上描摹了一下我记忆中的苏小小的胎记。当时的镜子是铜镜,我其实并没有太看清楚自己背上的到底是什么图案。不过以前曾经请贾姨帮我画下来看过,所以应该能复原至少百分之八十。
我坐在旁边想想画画,再抬头的时候,陈齐的纹身已经完成了。纹在后脖颈上,真是挺好看的。
接着我把手里的纸递给阿粥:“你看看这个图案,你能纹吗?”
阿粥接过去看了几眼,想了想,又拿起笔来勾勒了一会儿。片刻后他将东西递回给我,用不是特别标准的普通话跟我说:“这样比较好。”
奈奈也凑过来看,跟我说:“欸?我以前没发觉,你还挺有艺术细胞的啊。这图案真好看,你怎么想出来的?”
我苦笑着摇摇头。阿粥给我修改过后的图案明显完整了很多,整个画面变得流畅了,一勾一撇都很精致。我看着这个熟悉的图案,把他交给阿粥,说:“能不能现在帮我纹?”
阿粥还没说话,奈奈先叫了起来:“小桥?你吃错药啦?!”
我示意她先别说话,阿粥翻来覆去的看手里的画,时不时的还要比一下大小长短。片刻之后,他点头说:“可以。我今晚没有客人了,现在就可以纹。纹在哪里?”
我笑着指了指后背。
到达酒吧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我和奈奈往里面走,经过一个很长的走廊。走廊的天花板和左右墙壁都是镜子,各色的灯光打过来,反射的光芒很美丽。我一边走一边回头去看镜子里面的我,后背的纹身在卷发后面时隐时现。我站定脚步看了一会儿,从手包里面拿出来一个发簪,将头发都盘了上去。
因为头发特地作过了卷,又很蓬松,所以盘得并不紧,几缕发丝垂在肩膀上。奈奈却笑道:“这样很好看,你脖子本来就长,配这身衣服很合适。”
后背左肩胛骨的地方有点痒,是刚刚纹了纹身的刺痛。我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笑着拉上奈奈跑过去喝酒。
如此这般又是跳舞又是喝酒又是玩闹的,连我都不知道过了多久。陈齐对我竖起拇指说:“小桥你酒量可真好!喝了这么多还这么清醒。”
我握着酒杯笑的东倒西歪。以前我酒量一直不怎么样,可是今天也不知是怎么了,突然变得能喝了起来。不过终究有点过度,已经微微上头。站起来去洗手间的时候我都必须扶着墙壁走。
在洗手间我就吐了。
出来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眼镜有点红,脸上的妆也快不行了,就补了一下妆。转头看到两个男人站在我身后,见我望过去,其中一个走上来对我说:“小姐,能不能请你喝杯酒?”
我很少来酒吧,唯一的几次都是过节的时候和朋友出来,而且也一直很讨厌被陌生人搭讪,和陌生人喝酒。在南齐的时候是碍于诗妓的身份,现在可不用想那么多,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出去。
回去之后奈奈就对我挤眉弄眼,说:“刚才你去洗手间,有个人过来要你电话哦。哇哈哈。”
我吓了一跳:“你给他了?!”
“当然没有!”奈奈瞪我,“我是那么没原则的人吗?我说,你是我女朋友,让他不要打你的主意。哈哈哈哈……”
我囧了一下,又觉得也无所谓,遂没有多言。不过闹了这么久,大家也都有些乏了。我看看手机,居然已经凌晨四点,就对奈奈说:“我不行了……我喝多了,现在脑子都懵了。看着差不多的话就招呼大家走吧。”
奈奈说好。跟旁边的几个人说了一声,大家也都说好。不过买来的酒还有整整大半瓶没有喝完。于是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畜生提了一个建议,说:“大家来玩俄罗斯吧,把酒喝的差不多了再走。”
在酒吧里,所谓俄罗斯,那可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游戏。以至于坐在我旁边的奈奈一瞬间脸色都白了,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你们先玩,我去洗手间。”又瞬间被人抓了回来。
我和奈奈很萧瑟的对望了一眼。
我思考了一下,以我现在的状态,加上这酒的后劲本来就大,再喝一杯——顶多两杯,我肯定就倒了。可是鉴于我玩这个游戏向来运气不错,玩个十几轮最多最多喝上一两次,而且看样子这群人是绝对不会放我走的,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了。
事实证明,情场失意赌场得意这句话,说的不是我。
几轮下来之后,我都晕的找不到北了,胃里翻涌的比钱塘江大潮还厉害。连奈奈都瞪着眼睛望着我,说:“小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抵制浪费行为的啊?六个杯子只有一个有酒都能被你抽到,剩下半瓶酒我看几乎全都是你一个人喝了。要不要这么拼命啊?”
我连骂她的力气都没有,全身软绵绵的就往后倒。酒确实剩的不多,大概也就是三四杯的量。可我是真的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对奈奈说:“我……我去洗手间……”说完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往洗手间走。
估计是看我确实是喝了太多,这次倒是没人拦我。我一路快步走到洗手间,打开一个隔间的门冲进去就开始吐。
吐的我胆汁都要出来了,还是觉得晕,整个人都站不稳,可是好歹脑子清醒了一些。站起来揉了揉太阳穴,就打开隔间门走了出去。
出去我就愣了。
一排男人站在那里,目瞪口呆的望着我。
我愣了半天,升调的“啊”了一声,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走到男洗手间来了。连忙一边说“对不起”一边低着头往外面走。可这件事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一瞬间又晕的不行,走也走不顺了,脚下十二厘米的高跟鞋也不听使唤了,“喀嚓”一声就崴了脚了。
我疼的冷汗直流,可是全身都没力气,站也站不起来。这时候有人从背后拉了我一把,他力气很大,一下子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架着我的胳膊将我弄了出去。
出去之后,我还没来得及说句“谢谢”,就迷迷糊糊的被人塞到了一辆车里面。我倒在后座上半天才反应过来,倏然一下子睁开眼,却看到旁边一个人脸和我靠的很近,居然是方才在洗手间跟我搭讪的男人。
见我睁开眼,他笑眯眯的说:“小姐,能不能请你喝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