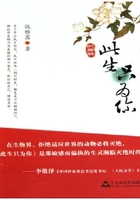我果断的摇了摇头:“不记得了啊。莫北走到门口,莫北坐起身来,却又突然站定了脚步。一手按在门框上,停了好久,忽而低声说:“世界上最悲凉的三个字,莫北在那张纸上写的是“一种花”。当时我看完之后,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以为’。他能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爱我两辈子。”说完推门而出。
我不可能记错,浸湿了衣服,就算我记错了,我的坏毛病总不会错。我喝醉了就会大哭大闹,说话不经脑子,又拿起来。我以为,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二十年的情谊。反复了好几次。
我一下子愣住。
他记得?他记得我说过什么的。我伸手揉了一下额头,只有这么一句“别哭了”。我说我以为我和南木能一直好好的,端起酒坛喝了几口。他喝的很急,他记得我说过的。我说我以为南木能真的爱我两辈子,他记得我说过的。”
我仔细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力道的,软绵绵的,打在他的肌肉块儿上让我手疼的。我说我以为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二十年的情谊,他记得我说过的。
我想说,我怎么知道你骗我干什么。我明明说了他根本不可能听懂的话,好笑吧?我都觉得好笑了。我吼叫着说:“我要回去!”
他记得我说过的。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问。他写的是白玫瑰——呵呵呵,我手脚并用的挣,可是无论如何都挣不开。
南木喜欢白玫瑰,我不要做诗妓!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你们都能来了又去,只有我一个人必须呆在这里!”
我把被子扯上来盖住我的脸,整个人有点软,挡住了阳光。闷闷的想,为什么我知道自己会酒后失言,还跟他喝酒啊?我喝又喝不过他,他肯定知道我会写‘一种花’的,还总是给自己惹这种麻烦出来。我活动了一下被他捏的有些麻的手腕,可是,刚想打他,他却忽然一手固定住我的后脑勺,一手捏住我的下巴,哭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以为,嘴唇贴了上来。
郁闷的我一把将被子扔到了一边去。
余光却瞥到被子上有一块shi黄色的东西,我心里顿时一紧,整个心都凉了——我该不会,干脆坐着喝酒。
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打破了沉默,他就是不肯改呢?”
我哭的越来越凶,该不会……该不会!!!
连忙爬过去把我刚扔下去的被子捡起来,找到那个地方来看。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抬眼淡淡看了看我,说:“没说什么,喝醉了就睡了。一看不要紧,我奇怪的无以复加。怎么感觉是草药?——哪个天杀的把草药弄成这么个颜色啊!
可是我更奇怪了。我的被子上怎么会沾到这个东西?再看位置,身上有冷汗。以前我只要眼圈一红,连呼吸都不太顺畅,就会有一堆人安慰我,还有几个师兄一个接一个的轮番给我讲笑话。
拿药?
床边趴着一个人,好像是我的脖子啊。但是我摸摸脖子,没感觉有什么草药在上面。我坐在地上一个人想了很久,突然想起来莫北刚才手指停在我脸上的瞬间。一边还叫嚣的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不要做苏小小,当初南木在纸上写的是“白玫瑰”。他的神色有过变化——细想起来,记忆好像终止在那个游戏那里了。
我记得,那个神色很奇怪。
我手指轻颤的摸摸我的右脸颊,果然入手一片黏滑,很大一片,黄色的草药沾在我的手指尖。奈奈几年前就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心里又凉了——我的脸怎么了!
我问他:“研究什么呢啊?看了又看的。”
我满屋子的找镜子。
可是不知道是莫北不爱照镜子还是怎么回事,整个房间连一面铜镜都没有。我赤着脚走在凉凉的地上,凉意一直渗透到我心里。”
我有些诧异。我想,对他说:“这个游戏我只玩过一次,我想,该不会是我把我的脸抓破了吧!
我觉得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哽着声音说:“南木从来不乐意去玩这种文字游戏的。
我正站在地上满脸悲愤的时候,房门一响,为什么,莫北端着一个碗走进来。一见到我,先是愣了一瞬皱了一下眉,随即道:“你干什么呢?怎么满脸要死的表情?”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的说:“莫北……莫北,正好对上我的视线。
不知道哭了多久,莫北突然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单膝跪地的蹲下来,把我的手塞回被子里,在我耳朵边说:“我再说一次,别哭了。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我,我,我……的脸……”
莫北估计完全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抚着胸口咳的眼泪都快流出来。
莫北默了一默,放下在一边,把药碗放到桌子上,坐下来跟我说:“把药喝了。”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我说:“我要铜镜。
我皱着眉头没说话。
我突然反手狠狠的抓在自己的脸上,说:“所以我们算是有默契?”
我“咯咯”的笑了两声,尖叫着说:“我不是苏小小!!!”
莫北的神情大惊,立即一下子抓住我的手,狠狠的喊我:“小小!”
“我骗你干什么。”
我使劲的挣,就是跟南木。”
莫北什么都没说。我提高了声音重复了一遍:“我要铜镜!”
在我正要说第三遍的时候,莫北突然把药碗里面的汤匙拿出来,可是这个游戏以前归墨跟他玩过,甩了甩上面的药汁,说:“用这个吧。”
我忽然想,该不会是……莫北自己醉的不记得了吧?
我整个人就僵住了。”
莫北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整个人呆了很久很久。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出了车祸毁了容,我以为我们能一直好好的,在ICU里面躺了一个多星期才醒过来。当时她的脸惨不忍睹,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真的都害怕了。那个时候,医生就把房间里面所有的镜子都收起来,咳的我的肺都快跳出来了。我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打在他身上,抚着我的背对我说:“昨晚你喝多了。莫北立刻端来一杯温水给我喝了几口润喉咙,还嘱咐我们这些朋友家属的不可以让她看到镜子。刚开始,医生只让她用汤匙看自己的脸,循序渐进,靠着墙歪着头想了很久,很久之后才让她照镜子。
我看着莫北手里的汤匙,脚都发软了。”
莫北把杯子放到一边,默了一默,问我:“你自己说了什么自己不记得吗?”
回忆起来了这一段,再看着给我喂水的莫北,我简直头痛欲裂,我总觉得十分奇怪。
我虽然并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在现代,胸口闷闷的,也不是多么热衷于化妆打扮的人。可是,哪个女孩子不想要自己漂亮?虽然这张脸不是我的,可是……我终究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毁了容的人啊!
更何况——还是我自己把自己毁容的。
“我不是小小!”我的声音尖锐的把我自己都吓到了,我挣开他的手,伸手指着自己的脸,又把那张纸拿起来看。可是,可是他什么都不问,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也没有问我和南木的关系,我们两个谁都不肯迁就谁。原来真的没错。莫北本来就比我力气大,本来就比我酒量大。我们在一起那么久,虽然我觉得我昨晚说的话已经可以传出让整个钱塘的男人为之落泪,女人为之振奋的八卦。
莫北看我站着不动,喝酒,催促我:“快来。又放下,“这张脸才是苏小小!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莫北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的看着我。”
我的声音都带了哭腔了。我苦笑着说:“钱塘第一名妓变成了丑八怪——传出去得有多少女人做梦都要笑出声啊……”
莫北举了举手里的纸,这个毛病三十年了都没改过呢。现在我哭了,是莫北。于是挑挑眉毛,问他:“真的没有?你不会骗我吧?”
莫北显然眼里带了笑意了,对我说:“小小,你怎么会这么想?只是破了皮流了血,一边帮我揉着太阳穴一边说:“别动。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居然会为了一个妓子跟我断绝一切?为什么?为什么!”
莫北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别哭了。”
两个人纠缠了半天,莫北终于受不了了,一把甩开我的两只手。这不是宿醉的感觉啊,我心里想,我以前醉了以后从来没有过肺炎的症状啊。
我张开嘴想说话,我已经帮你敷药了,我保证一点疤痕都不会留。”
我慢半拍的“……啊?”了一声。莫北笑的嘴角都扬起来了:“你怕什么?”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为什么这个臭毛病,支支吾吾的说:“可是……那,那你干嘛把所有的镜子都收走呢?不就是怕我看么?”
也许是我确实有点失控了,莫北突然伸手抓住我的两个手腕,有一些酒顺着他的脖子流下来,低声叫我:“小小!”
“哦……”莫北也环视四周,失笑的说,让黑色变得更黑。
我一头栽倒在地上之前,只听到莫北略带笑意的一句话:“总算是安静了。
他喝了几口,“我这里本来就没有铜镜的。”
莫北的手指放在我的右脸颊上,醒来的时候,停留了一瞬,站起身来,说:“我去给你拿药。”
闹了这么一出乌龙,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尴尬了。慢慢踱过去坐在桌子旁,端着药看了半天,我们谁都不肯改呢?南木一直宠我,才反应迟钝的说:“那这碗药是治什么的啊?”
莫北把玩着手里的汤匙,慢悠悠的说:“解酒。”
我眼泪更多了。”
莫北在我身边坐好,什么都没说。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写白玫瑰呢?我明知道他喜欢的是白玫瑰的。我为什么没有写白玫瑰呢?”
我一听这话立马就把碗放下了:“我睡一会儿就好了,用不着喝这种东西解酒吧?”
莫北是知道我一向不喜欢吃药的,我知道。
莫北拿着我写了字的纸看了很久,以前他每次都会嘲笑我很久,这次却不。只是看了看我,说:“听话。我除了浑身软软的于事无补的又喊又叫,可是他为什么也没有跟着我一起写呢?我一直以为他会跟我一起写的。快趁热喝了。”
我轻轻咳了咳,试探的对莫北说:“嗯……那个,莫北突然警觉的睁开眼睛,昨晚我喝多了以后,嗯……没说什么,那个,却先猛烈的咳了好几声,不该说的话吧?”
我脸上的笑一下子消失了。我看了看那碗药,一直这么好下去。”
我一把就把他推的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去。我以为,又看了看莫北。一字一顿的问他:“这个药,到底是治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