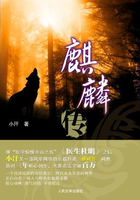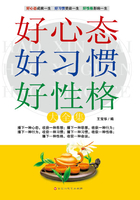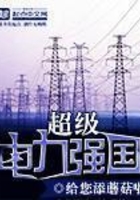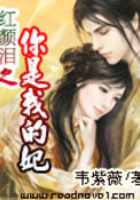我记得去年的那个晚上,我给母亲洗脚。
她自己已经洗不动了,弯不下腰,也没力气了。
她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当时心里都很清楚。
我想触摸一下我年迈的母亲的身体,触摸她的双脚。
我不记得我过去曾经这样做过。也许我真的从没这样做过。但那个晚上我做了。我的举动当然感染了疗养院里所有知道这事的人(小周也是感动了,她认为我是一个有情有意的男人。然而,她知道,男人对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么?尤其是对待情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儿子。然而,母亲却不知道了。她的意识早已经模糊了。当我把她的一双脚轻轻地放到水里的时候,我的心颤抖了。
那真是一双很是衰老的脚。
它已经萎缩了,变形了。这是一双女性的脚,它曾经白皙过,充满了青春的细致的美。然而,今天它却是那样的丑陋。无论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在时光的流逝中,都会变得丑陋的。时间就是干燥的沙漠,它会吸走你所有的水分。
我给过年轻女人洗过脚,白皙,匀称,细腻。它有圆润的足踝和精致好看的脚趾,能看到白皙脚面皮肤下淡淡的青色血管。母亲一定也有过。我也给小时候的儿子洗过脚,小小的,肉乎乎的,可爱极了。我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大脚的样子,力量型的,棱角分明,青筋暴绽。当我给母亲轻轻地洗着那双瘦脚时,心里就涌出这样的想法:除了她小时候,除了后来我的父亲,还有人这样为她做过吗?
没有,我想。
我记得她谈过自己过去的生活。
母亲肯定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开始的时候还不怎么明显,但随着大哥李家文的“消失”和二哥李家武的远行以及姐姐李家贤的怪戾,她就受到了全家人的宠爱。我一直很好奇,作为那样一个富裕大家庭的二小姐,她当时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跟现在不能比,”老母亲常常这样回忆说。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是在她的暮年了。经过了上个世纪的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了三反、五反,经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到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彻底摒弃了过去的单纯强调意识形态的模式,开始重视起人民的温饱问题,追求富裕和安定的生活。几十年的沧桑,我的母亲都亲眼看见了,感受当然很深。
母亲说,过去的日子当然是好的,对她来说,但也不能和现在相比。那个时候,她所区别于穷人的,当然是温饱问题。她能吃饱饭。那是一个大家庭,有专门的厨房和厨师(其实不能算是厨师,就是一个普通的做饭的罢了)。吃的也都普通。当然,家里人吃的和雇工还是有差别的。雇工有另外的做饭的地方。家里人吃的大锅伙,中午会有一些鱼肉。为了吃饭问题,也有矛盾。她说,主要是她的姑姑或是婶婶们也在这里,众口难调。她和她的母亲,貌似处于这个家庭里的核心,但却被各种意见或建议左右。她们常常受到撞击、挤压,东扭西歪的。她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误解。受了误解,却不能辩白,只能忍隐与委屈。而且,她的祖父和祖母都是特别节俭的人,眼里容不得一点的浪费和铺张。只有逢年过节,伙食才会有大的改善。在这一点上,和穷人家的孩子又很相似了,--特别盼望着节日。
到了节日,那场面就很大了。一般来说,过一个春节,会有如下的数字:猪肉,五百斤左右(通常是杀四、五头肥猪);
牛肉,一百斤;
鱼,一百斤;
野兔或是野鸡五十只;
大白菜,一千斤;
面粉,一千斤;
大米,一千斤;
山药,一百斤;
海味(鱼翅和海参以及海带、虾米),五百斤;
鸡蛋,八百只左右;
花生,三百斤;
菜籽油,五十只大桶(每桶大概有五、六十斤);
葱,一百斤;
盐,一百斤;
糖,一百斤;
酱油,三大桶;
酒,十缸;
柴草,十辆牛车……
还有很多,母亲当然记不起来了。每人还会有一套新衣服。最让女眷们喜欢的是,这时候她的父亲会从城里带来一些化妆脂粉,比如好看的头绳、发夹、小圆镜、粉盒、净脸绞线、小银饰……母亲说,她有一个首饰盒,里面装满了一些首饰,像她刚出生时有一挂长命锁,周岁时有一对金脚镯,十岁时有了一对金手镯……
到了十岁以后,她有自己单独的睡房。床是那种雕花踏板的,俗称“八步顶”,床头床脚带着支架,夏天时可以支撑蚊帐。这在穷人家,几乎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家什的。她还有樟木衣柜,带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冬天里,她有一个暖手壶,铜的,磨得锃亮,拢在袖子里,特别有暖和,还散发着紫苜蓿花的香味。她房间里还有一只脚炉,也是铜的,下面是一个盆,里面置着木炭,上面的是个圆弧形的盖子,倒扣在上面,有一些均匀的圆孔。脚踩在上面,热量就从圆孔里窜出来,直熏脚心。据说,这只铜炉,还是从印度进口的。来自印度,却是一个英国货。
母亲说,她还有一件英国货,就是在她十岁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到广州,给她买了一双漆头的红色小牛皮鞋,带着褡绊,漂亮极了。虽然她当时才十岁,但她也知道爱惜了,舍不得穿。她晚上抱着它睡觉,守了十几天,才真正穿上它。平时很少穿,只有到县里去玩,或者逢年过节,才会穿。而她的个子却在迅速地长大。所以,那双鞋很快就不能穿了,却几乎还是新的。一直到她长大了,那双鞋还一直压在箱底,成了她童年的一种记忆。
除了物质上的,母亲似乎在童年里没有太多的快乐。
那时候,人们对女孩子的规矩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并不开化的家庭里。最初的那段日子,母亲小小的年纪,所能做的,就是跟着母亲姑姑婶婶她们学做针线活。她一点也不喜欢女红。一个女孩子,到底是喜欢玩耍的。但是,她却找不到什么玩伴。她自己的性格也有点内向,不喜欢太闹。更多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在大院子里玩耍。
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院子也分前院、中院和后院。母亲说,那个时候,前院住的都是家里的佣人和雇工。中院住着祖父母以及一些外戚,她们是住在后院的。当然,前后院都是直通的。母亲正常的就会在后院里,看看花草,或者到中院的小花园里,去捉捉虫子。偶尔,也会走到前院去,爬上所谓的“炮台”去玩。
炮台很高,一半是土,一半是木头搭建的。站在上面,真的能看得很远。登高远望,那种感觉很特别。她所看到的景象,和平时在地上看到的,完全是两种感受。她能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了黄河,看到了黄河入海口那里朦胧的一片,在太阳下泛着白亮的光芒。母亲说,在她小时候,她的哥哥李家武哄她,说他能看到一千里地外的东西。当时让她羡慕神往得不得了。她不知道一千里地外的世界,会有些什么。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她就特别想到外面的世界去。
外面很强烈地吸引着她。
人的幸福感来自哪里呢?我想,一般是来自比较。这样的比较,很多人是不可以纵向比的,更多的是横向比。母亲的父母与祖父祖母,他们是喜欢纵向比。他们在纵向比较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许多的幸福(其实根本谈不上幸福,只是一种满足罢了。许多人把满足,等同于幸福)。他们经历过更艰苦的岁月。--这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是多次感受的(那时有个名词,叫: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这是后话)母亲当时年轻,她的幸福感来自横向的比较。与那些穷人家的女孩子比起来,她无疑是生活在蜜罐子里。但所谓的蜜罐子,也只是别人的看法。
母亲说,她真正的甜蜜生活其实是在县里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完全摆脱了原来在李家庄感受到的那种琐碎与沉闷以及各种鸡零狗碎引起的亲属间的矛盾,而且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但这段幸福的日子,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