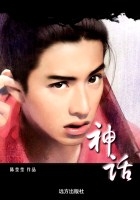看看一个人的鞋子,就知道他走了多少路……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妈妈的话
开端
一切爱与恨,都会过去的。
过去的,曾经是当下的;当下的,即将成为过去。
如果你生在当中,又将如何呢?
那是一个下午。
午后的阳光射进来,把房间里照得通亮。照在橘红色的实木地板上,反射着暖烘烘的金色光泽,屋里就像着了火。铺着雪白床单的床的上方,有一些细小的微尘在光柱里飞舞。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就像我母亲临走前的那样。不,我感觉我母亲好像还在,只是到厨房、卫生间,或者是临时下楼,到前面院子里的草地上了。但事实是老母亲已经不在了。她存在的,只是一种气息,是我的心理作用。我熟悉这里,熟悉这个房间,就像自己一直生活在这里一样。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也会选择在这里终老,我想。
去年秋天,老母亲突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那段时间,我不得不中断我的生意,去陪护她。虽然这里的护工、医生,还有姐姐。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来的,--我相信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少的。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真正的风烛残年。好些年了,她一直住在这个疗养院里。是的,她在这个疗养院已经住了七年了。送她去疗养院,是我之前和妻子多次商量的结果。这个疗养院的条件非常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每人都有一个单独的套间,卧室里连着卫生间,不大的客厅里摆放着桌椅和电视。整个陈设,其实就像是宾馆。每天的饭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工作人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老母亲也是愿意的。她不愿意拖累我们。许多老年人在一起,也会有交流,不那么孤独。当然,费用也很高,一般人家根本承受不起。在这方面,我倒是没有问题。我愿意为我的老母亲,付出更多,只要她愿意。
我还记得七年前送母亲来这个西山疗养院的情形,一路上她很沉默,眼睛看着窗外。但我相信她并不是看风景。她这一辈子经历得太多了。外面的世界同她的关系并不大,至少她是这样想的。她带了她过去所有的东西。她的东西并不多,只是一个很小的包袱。我和妻子为她准备了另外两大皮箱衣服,从春天到冬天,一年四季的衣物,应有尽有。“您去住一段时间,要是不习惯,那我再把你接回来。”一路上,我不断地这样安慰她。但她不说话,只是当我回头看她时,她才浅浅地笑着。也许,她并没听清我说什么。她的听力下降严重,聋得厉害,讲话必须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叫,才可能听清。她龙钟老态,满头的银发,反应迟缓。很多时候,她一个人呆呆在家里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尊雕像。她脸上和手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大概也只有天才的雕刻家才能那样细致地做出。即使我们主动和她说话,她有时也会默不作声。我们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想?不管如何,我希望我的母亲能够理解我。老母亲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她一向听从我的安排。到了晚年,她几乎是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就算是别人发了天大的脾气,她也不吭声。一切都与她无关了。她很超然。她仿佛把世间的一切都看透了。是的,到了她这样的年龄,即使看不透,她也无动于衷了。对她而言,时光正在一点点地消失……
老母亲住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她说她在这里很好。这个疗养院是真的很好,依山傍水。前面不远就是紫阳湖,背后靠着大青山。整个疗养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的院子,三幢两层的建筑,呈“凹”字型。母亲住在左侧的这一幢,二楼,早晨可以看到太阳东升,下午可以看到太阳西落。冬季里,连空调都不用开,室里却阳光灿烂,温暖如春。那种感觉,很惬意。我当时就对母亲说过,到老了,我也会选择到这个地方来。这是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很恬静。逢年过节,有时我主动提出要接她回城里,她也不愿意。从城里,到这个地方,不过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是的,对她而言,城里的那个家,只是我的家,而不是她的。她的家在这里。这里是她的最后归宿。院长告诉我,她的身体各方面还挺好的。只是她不大出门,好像永远只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发怔。电视完全就是个摆设,整天累月也不开一次。虽然她的耳朵聋得厉害(有一段时间疗养院施工,挖土机的巨大轰鸣她都听不到),但她却认为电视实在是太吵了。事实上,即使你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得很小,她也不愿意开。她不喜欢声音。她的世界,就像是大雪后的一片荒原,一点声音也没有。她这样的年龄,电视对她没有吸引力。她不爱看电视剧,看了也不能理解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至于新闻,那更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她所经历的那些残酷冰冷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她年轻。现在,她已经是垂暮之年,外面世界再发生什么,和她关系也不大了。因为不关心,所以她也不串门。她很少和别的老人聊天。她把自己的心思锁得很深,让人感觉她不好接近。
虽然是在疗养院里,但最初的两年间,我们还是能经常见面的。只要有空,我都会去看望她。反倒是她好像并不习惯我们来看她。我有时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像是打破了她的生活节奏与宁静。我们的感觉也不好,像是客人,来去匆匆。她也说她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后来再去,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有时,我可以陪她坐一整个下午,就是在屋子里,谁也不说话。阳光把房间里照得通亮,闪着金光,她的满发白发也生动起来,像是有了新的生命。她的嘴唇不停地颤动,像是嘬嚅着什么。当然,她经常自言自语,自己说给自己听。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那只是神经质地颤抖。后来腿和手,也一起加入了颤抖。护士说,那叫帕金森氏综合症。医生让她服用一些药丸,像是美多巴和息宁,或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但是,效果有限。毕竟她的年纪大了,效果有限。而且,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治疗难题。
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老母亲的生活。一方面当然是不想破坏她的宁静,另一方面我也实在是太忙了。或者说,前面的理由只是我的借口。每过一阵,我会打一个电话给她,询问她的身体情况。她的耳朵越发地背,我冲着话筒大声喊,她也听不清楚了。我能想像得到,电话铃响了,她必须是经过人的大声提醒,才会慢慢地起身,佝偻着腰,去接。整个接电话的过程至少需要两分钟的时间,所以,打她的电话需要足够的耐心。她举着话筒的手臂是僵直的,然后不停地颤抖。对着我在那边的话筒里的大喊大叫,她还在纳闷话筒里怎么没有声音。而除了她听不到,屋外走廊上的人差不多都能听到我向她的问候声。几次以后,我也就索性只询问院长或是管理员了。只要听说她身体还好,我就放心了。院长姓王,原来是市内一家街道医院的院长。他和我认识多年了,也算是老朋友。所以,我把老母亲放在这里,是放心的。从各方面情况看,他是蛮照顾的。另外,这个院里的管理员小周,和我的关系也很好。她对我母亲的照顾,真的就像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妇。
几年间,老母亲也住过院。一次是得了肺炎,另一次是腿摔断了。肺炎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回到疗养院又治疗了有一个月;而腿摔断的那次,则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两个月,回到疗养院又躺了大半年。据说,她只是上楼梯时不小心磕碰了一下。年纪大了,骨头很酥脆。那次摔得太重了,大半年后虽然是长好了,但人却越发地虚弱了。她人瘦了一圈,脸色也比原来黑了,白头发比原来更稀疏了。她的记忆也开始不好了(准确地说,是惊人地不好了),眼神也不好了。许多过去的熟人,她见了,也叫不上名字了。院长告诉我,事实上这个时候她已经是大脑萎缩了。通俗地说,就是有些老年痴呆了。
人到老年,真的是有些悲哀,我想。
当然,我也会老,一样。
老母亲的病倒事先没有任何症兆,小周在电话里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她还给我母亲盛了一大碗青菜粥(这是她平时最爱吃的),一只豆沙包子,一碟小菜,她都吃光了。看上去,胃口和精神都不错。夜里,有值班的护士说,她在走廊外面听到她咳嗽了一阵子,也就没当回事。到了早晨,却没见她起来。老年人早晨常常醒得特别早。很多老人四点多钟就醒了,有一些仍然躺着,有一些却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东瞅西瞧的,把所有的家具陈设都摸一遍。我的母亲也经常是五点左右就醒了,然后会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嘴里念叨着什么,却不发出一点的声音。而这个早晨一直到六点半,她还没起来。管理员进了房间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病了,爬不起来了。
早晨院长和医护人员都来了,看望她,量体温什么的,一切都还好。她说她也并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只是全身无力,有点恶心,不想吃饭。医生安慰了她一番,让护士给她挂了一瓶点滴,也就没有特别的介意。到了这样的年纪了,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感到意外的。但是小周早晨上班后,看到了我老母亲的样子,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难道她真的和我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我处理好公司里的一些事情,匆忙赶到疗养院,发现老母亲正在吊点滴,精神似乎还好。见到我,有些吃力地抬了抬手,示意我坐下。而我就在坐下的那一刻,突然就想到,也许我这一坐下,暂时就离不开了。预感这东西很奇怪。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是那感觉却特别强烈。最近的两年多,我一直有种隐隐地担心,怕她离我而去。这样的担心并不是出于对她健康的考虑,而更多的是一种理性。她已经活得太久了!人,都是会死的。生命就像是一盏灯,燃烧久了,灯油总会耗干的。最后,一定会熄灭的。看着妈妈的样子,我就想到了那盏已经基本耗干最后那点燃油的灯,稍稍一点轻风,甚至只是鼻息,就可以把灯吹灭。
“您哪不舒服?”我问她。
“……没有……就是没胃口,身上没力气……”她说得很虚弱。
“没关系的,老年人就这样,我问过医生了,他说吊瓶点滴就有精神了。”我安慰她说,“你就是平时休息不好,操心了,累着了。”说完了,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她会操什么心呢?当然,我要安慰她,给她一个听上去不那么沉重的轻松理由。人老了,就像一个孩子,需要人哄着。这个时候,也是容易哄的。他们在许多问题的差别能力上,已经出了问题。他们的大脑变得固执而简单。固执当然就要哄。
就像我预感的那样,我母亲这次躺下后就没能起来,这也是出了很多人的意外的。但是,疗养院里的人也并不是感到非常的意外,毕竟这里的老人走得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走法。通常情况下,都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而到达天堂。对许多老人来说,天堂就在隔壁,虽然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只要一合上眼,就可以到达了。
就在我来的那个下午,母亲开始时有昏迷。以后的几天里,在她弥留之际,她拉着我的手,说了许多糊里糊涂的话。有些话我根本弄不清是什么意思。她说的许多事,听上去是那样的遥远。很多是不连贯的。甚至,很多是不可信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值得怀疑的)。许多地名、人名,都是错误的。现在,我突然决定要把它写下来,--根据对当时的叙述的回忆。我把它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来做。我并不清楚它的意义,只能说对我个人而言,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儿子,我必须保留对我母亲的记忆(包括了完全属于她个人的一些记忆)。而且,她的一生,其实是可以看作是一部历史。因此,在这里我有必要加以几点说明:1、这是有关一位年迈的老妇人一生经历的回忆录。
2、所有涉及我老母亲的有关回忆,都是经过我重新的组织加工,尤其是文字,基本是另外的一个文本了(说它是全新的,也未尝不可)。在她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所有的文字都是我后来的再加工。甚至,在某些部分,我进行了大量的属于我个人的添加(完全是从主观出发的)。
3、对她叙述中的许多不甚明白的地方,我做了适当的而又大胆的修改。
4、在她的叙述中有着大量不可信的,甚至是迷信荒诞的内容,无不印证了她那样年龄的人所经历过的认识局限和时代烙印。从科学意义上来说,它基本可以被视为糟粕。我曾经一度要把它删掉。但后来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那样的念头。毕竟那些回忆,是她过去九十多年生命中的一部分。从年轻时候起,它就深植在她的内心里,并且始终影响着她。影响着她的观念,也改变着她的生活。她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怪诞内容,似乎就是一体的,很难加以区分。从某个方面来说,因为它们的存在,倒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
5、我必须强调,这并不是一本完全的个人回忆录。它是一部私人回忆记录和个人创作相混合的作品,只有我才能分辨出其中哪些是真实的回忆,哪些是出于虚构。或者,它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回忆录。
房间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
外面的天很蓝,阳光灿烂。那片湖泊,闪着一片白光。院子里的树木郁郁葱葱。一只蝴蝶不知从哪来的,一直在窗前飞着,似乎想透过透明的玻璃飞进来。我抽着烟,慢慢地吞吐着,看着它在徒劳地努力着。它从哪里来?这里并没有花香,可以吸引它。它为什么要这样的表演呢?很有意思,我想,它并不知道眼前存在着一片透明的玻璃。在它眼里,这片玻璃是不存在的。正是这不存在,却完全阻断了它的行程。
那段行程,也许正通往它的向往之地。
我津津有味(或者说是百无聊耐地)盯着它看,直到烟蒂烫着了我的手指……
蝴蝶其实和我没有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经常到她的这个房间里来。我需要休整。前一阵子在生意上,我做得太累了。在这里,我就经常不由得想起母亲,想起过去的一切。
我意识到,我应该把它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