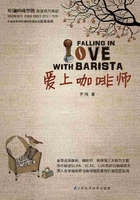我不回去了,我要逃!
我要逃,远不止是因为自行车失窃,回去没法向父亲交待,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厌倦过去的生活。过去想摆脱那样的生活,然而我没有足够的借口,而这次,正好给了我一个充足了理由,--我在心里想象:没有了自行车,我就到绝路上去了。
可是,我要逃到哪里去呢?
跟着剧团走!
在我的大脑里突然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当然成了天大的笑话。
那个姓金的团长怎么也不让我随他们走,他对我的这种要求感到十分的惊讶。在他们这些年的演出过程中,从来就只有小姑娘跟着跑的。一些姑娘他们收留了,跟着学戏,有的居然还成了角,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着来的。
跟剧团走!心里刚开始冒出这样的念头,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坚定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或者说是非常的幼稚。但那时我就是那样想的。我想我是年轻人,剧团里什么活都能干。我不需要他们钱,但要他们收留我就行,甚至我一天只要吃一顿就够了。真的,当时我在心里就是这样想的,非常简单。
正是抱着这样简单的想法,使得我一直赖在剧场的后台,一遍遍地央求着金团长。我说我能干很多活,我会拉手风琴,会吹笛子(毫无疑问,我这种拉手风琴和吹笛子的水平都非常业余,也就是刚会把一支曲子拉得像个调调。金团长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自荐。问题还在于,一个演出古代戏的剧团里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乐手,如果是二胡和鼓手倒还能派上用场)。可任我说破天,他也不同意。
我的这种死皮赖脸行为,终于把金团长气火了。他叫来后台两个搞道具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架我出去,并威胁说我要再这样,就打我一顿。他在心里把我当成了一个无事生非、故意滋事的农村小流氓。本来他是让那两个人吓唬我一下,可是他们就真打了,把我打得头上都出了血。我意识到自己流了血,就直直地躺在地上,半天也不起来。
金团长害怕了,叫人拉我。拉我也不起来。他问我到底要怎么样,我说我把自行车丢了,不能回去了。金团长说,那是你的事,你总不能要求我们赔你一辆自行车吧?要赔那也是剧场的事。我说我不是要你们赔,我就是想跟着。团长生气了,说,要跟你就跟着吧。
他们以为我不会当真的,可我就真的一直随着他们来到码头,跟着上了船。他们推我下去,可我双手扒着船帮,就是不松手。满手都是血。云子在那过程中,一直不说话,但我看到她一直在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我想要是一直那样咬下去,她会把嘴唇咬破的。
剧团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和道具一起,都集中在一条船上。船沿着运河走,每到一个联系好的城镇就停下来,演出。在我第一天刚搭上船的时候,他们谁也不理我。夜晚,我一个人躺在船的外面,看着满天的星星,心里特别的轻松。手上和身上被船浆打的伤痛全忘了。不管如何,我现在是搭上了这只船了,我可以和云子在一起了。
云子看我时的眼神是冷漠的。当他们把我扔到运河里的时候,她的眼神也是冷漠的。她不能理解我这样的行为。她在心里肯定也很看不起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农村出来到城里无事生非的小混混。我被他们扔到水里,差点就被淹死了。我不会水。金团长后来怕了,叫人把我捞上来,看我像死狗一样趴在船舱板上大口痛苦的吐水,问:“你还要不要再跟我们了?”我哭起来(没有出声,只是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流),但嘴里还说:“跟。”金团长叹了口气,说:“算了。”可那两个年轻男人还是不让我上船,他们说:“要跟你就跟吧。”他们恶作剧地在我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拴在船尾,这样我就像是一条被渔船猎杀的金枪鱼,被拖在后面。
云子好多天都不理我。我就像一条倍受冷落的丧家犬。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父母们这时候在村里的感情。父亲在我出走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头上的头发就全白了。母亲,也一下老去了不少。但我只是在船停靠在一个小镇时,往邮箱里简单地投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
爸:我把自行车丢了,你们赔一辆新的给人家。我跟县里剧
团走了。不要找我。
下面是我的大名:牛铁锹。
在剧团里,我抢着干最重最累的活。那份辛苦,有时远比在家里干农田里的活要累,但我却毫无怨言。因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想我的努力不会白费。我没有别的什么才能,身上有的只是力气。
我慢慢地越来越喜欢随剧团走南闯北。我爱戏文。更主要的,我还能经常看到云子。她不理我。我也不奢望什么,我想我只要能经常看到她就行了。每天能见她,心里就很满足。我想她是我在这个剧团里的第一个“熟人”。
金团长五十多岁,本名叫金铁山,是个大胖子,肚子永远就像一个怀了七、八个身身孕的妇女。每天他都把头发梳得油光水亮,齐齐地贴在脑顶上。左手的无名指第三关节上戴了一只金戒指,那是他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他很严肃,那张胖脸上很少有笑容。据说他过去不是这样,年轻的时候经常笑嘻嘻的,活泼好动,与年轻的女演员打情骂俏。想必他在年轻的时候挺讨剧团里妇女同志的喜欢,谁想三十五岁那年,他生了一场病,之后嗓子眼里又生了一块息肉,就再也不能上台咿咿呀呀地唱戏了。
不能演戏的金团长,自然痛苦得很。那时候他还不是团长,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热爱戏剧艺术的高调就不提了,单就不能演出这点来说,就很致命,--作为一个演员你要不能演出,就等于一个废物。
年轻的金铁山化悲痛为力量。他埋着头在团里干杂活,背地里眼泪汪汪的,很伤感。他当时深爱的团里一个年轻女演员,因他不能唱戏而和他中断了关系。慢慢地,团里发现金铁山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很快他就从一个无关紧要的干杂活的位置提拔成剧务主任、行政主任,再后来又成了副团长。四十三岁的时候,老团长退休了,金铁山成了正团长。
如果说他是副团长的时候还同人说笑,到了正团长的时候,金铁山再也不肯笑了。不是他有了什么官架子,而实在是他感到自己的担子重多了,剧团一大家子几十号人,什么他都得操心。他心里那样烦啊,别人从他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同样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很不幸福。他老婆在文化局家属大院里,是个非常有名的泼妇。
团里不少演员对金团长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慢慢发现,金团长的心肠并不坏,至少对我表现得很宽容。在我的努力表现下,他已经习惯我在剧团的存在了。因为,有那么一天,他突然对我说:“铁锹,你力气大,一会把那箱道具扛上来。”
在其他人的眼里,我则是一个十足的傻小子。钱一文就很会欺生,他看出我好用,居然不停地支使我干这干那,有一回居然让我给他倒洗屁股水,--他像一个女人,天天晚上要洗屁股。钱一文是剧团里的男一号,四十来岁了,长了一张非常白净的脸,唇上看不出一丝胡须(有人暗地里笑称他是太监。后来他告诉我说,因为是演戏的缘故,年轻时就拔胡须,每天拔,终于拔得现在连一根也长不出来了。对他这样的话,我有些半信半疑)。这倒还罢了,最让人受不得的是他居然会打毛衣,剧团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坐在屋里打毛衣。一年到头,织不完的各式毛衣。他的手很巧,毛衣能织出各种花样,惹得一些女演员也向他学。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团里给了他一个外号,“二奶奶”。
“二奶奶”虽然娘娘腔,但除了团长,在团里他是最喜欢发号施令的人。但是,他的话一点力量也没有。相反,剧团里的人都对他这样的作派非常反感。特别是女人,经常嘲笑他。嘲笑他的理由似乎也很简单,就是他从来拿不出一文钱来请女演员们吃小吃。而别的男演员,包括团长,每到一处,必然会买上炸豆腐干、烤脆饼、云片糕、玉米花、糖炒粟子等等,请她们亲爱的小嘴品尝。女人似乎就是为了美味小吃而生的,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用小吃去收买女人的心,那么就真是地道的傻瓜。
周翠莲是“二奶奶”最恨的女人,因为周翠莲动不动就会暗里整治钱一文一次。周翠莲在团里也算得上是个中坚,她当年就是看了剧团演出跑来的,跑来的那年才十四岁。谁想她从小就爱唱戏,疯疯傻傻的,嗓音条件好,入团学唱了几年以后就能上台了。二十岁的时候她算是正式入了剧团,--剧团利用招员的机会,把她的户口转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到团里后先是喜欢上一个叫赵子龙的男演员。那个男演员有老婆,有孩子,可是周翠莲生就把人家给拆了。不过也有人说是赵子龙主动引诱了周翠莲,并使她怀了孕。本来接下来进行结婚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可不知怎么两人又闹起了意见。意见闹大了,赵子龙就经常打她,打得她在剧场里团团跑。两人成了地道的冤家。剧团报告了文化局。文化局的领导找赵子龙。赵子龙不肯承认错误。文化局后来就给赵子龙一个处分。受了处分的赵子龙后来就调走了。接下来的周翠莲就嫁给了一个机械厂的小科长。结婚的第三年,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两岁的时候,他们又离了婚。又过了两年,周翠莲有了个老伴,--他都五十岁了。谁也想不到她会找一个五十岁的老头。但周翠莲的嘴里满是老头的好处,“我男人疼我,惯我,经常给我买吃的。”“我多晚回去,他都等着我。大冬天,早早就把被窝焐得热热的。”“我男人给我买了一件一百多块的衣服!”等等。
尽管周翠莲和钱一文两人有矛盾,但他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把我当做了他们使的“小伙子”,动不动就支使我买这买那,还经常怪声怪气地叫我的名字,--铁锹哎,--铁锹嗳,--牛铁锹!
我忍受着,默默地干活。
3
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了村里。
最初在剧团的那些日子里,云子一直不理我,成天板着脸。她是个心气很高傲的姑娘。也难怪,由于她年轻,唱得好,从金团长到文化局的领导,都宠着她。她不理我,我不在乎。
一年后,我成了团里的临时工。在团里,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这么说并不夸张,因为我肯干,肯学。我学上了二胡,而且写得一手好看的美术字(后来的日子里,团里演出海报都是我写。写了无数花花绿绿的海报,然后四处张贴)。我还无师自通,成了一个电工。金团长自然看出了我的能干。
活,虽然是临时的,但是我却开始每月领工资了。一个月三十块钱。这真让我感到高兴。我想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虽然还是一个农民,但是我却不需要依靠种地来获得报酬。由此,在团里,我更加卖力的干活。
云子在团里并不快乐。我看得出来,除了周翠莲外,另外几个女演员也都嫉妒她。云子年轻,漂亮,嗓子好,团里、局里都很看重她,把她视作一个“角”,将来必定会唱个大红大紫。我还看得出来,团里那个叫杨建广的小伙子在努力讨好她。杨建广同我有点像,都是瘦瘦精精的个子,大眼睛,只是皮肤比我更白,更干净。杨建广年龄同我相仿,可能比我稍大些,大也大不了几个月。杨建广的家就在县城,而且他的父母还是什么干部。因此,他在剧团里,就比别人多了一份优越感。说真的,我内心里很羡慕他。他的命运怎么就会那么好呢?
天长日久,我慢慢死了心。我看得出来,要想让云子喜欢我,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和杨建广是不能比的。我算个什么?一个农村来的小小临时工。
但是,我依然热爱着这个小小的剧团。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不到二十人的剧团,但它却是国家财政负担的正式股级单位。我没有什么奢望,只想着要是能在剧团干一辈子临时工,就是非常幸福的事了。对云子,我的表现还同过去一样,但只是不再梦想了。
那年的冬天,在运河边上的一个叫婺县的地方演出。首演的那天,在剧场里装布景,吊了几次都没有吊好。我急了,就爬了上去,刚把布景吊好就从上面摔了下来。那一下摔得我不轻,趴在舞台上我好半天也没能爬起来。我自己感觉内脏可能都摔破了。鼻血流了一脸。我摔下来之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从上面摔下来了,因为有人做了手脚,希望我从上面摔下来。做手脚的就是一个脸上长满了疙瘩的道具工。他对我越来越不满,仿佛我夺了他的彩。那天,他就在下面把我脚蹬上的扣给解了。事后,金团长问我怎么问事,我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但我感觉金团长全明白了。
剧团的经营状况不好,为了节约开支,一般演出结束后我们都是睡在舞台上面。大幕后面,一片漆黑。那个晚上,我像过去一样,睡在最靠外的位置。夜里的时候,我被什么弄醒了。朦胧中我感觉有一只小手拉住了我的手,用尖尖的指甲在我掌心里写字。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云子的手,手掌绵绵,手指纤长。横竖横竖折横点点横竖折横,撇点点捺点折横……反反复复,我心里认出那是两个字,“喜爱”。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紧紧地不放。这一切来得这样意外,让我感到格外的喜爱和紧张。躺在黑暗里,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心里更感觉,就在这黑暗之中,有好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全在别人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那个晚上,我们就那一样一直拉着手不放。她一下子表现得如此突然,让我幸福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想她也是紧张的,手心里沁出许多汗珠。
剧团里的人慢慢看出我们在恋爱。
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很隐蔽。每一次,我们都经历着心跳的感觉。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拉手的那个晚上,我们连对方的被角都没有去碰一下,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也就是彼此交换一下眼神,一个微笑,一个看似不经意地双手相触。不过,我们的心里却充满了甜蜜,创造和利用一切机会,去交换那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双手相触的机会。
演出的旅途中,就成了我们创造爱情的旅途。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单独在一起,也就只有当船行驶在运河上的时候,我们才会认真去想一下我们的未来。可是那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没有想得太多,内心里充塞着甜蜜的快乐。晚上,他们都在舱里,我会独自躺到舱外,听着水响。等别人都睡着了,云子就会偷偷地蹑手蹑脚溜出来,像一只小猫一样,躺到我的身边。夜幕漆黑,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两边的河岸向后滑动。身下,是哗哗的水响。运河两边的田野更是一片漆黑,偶尔经过一个村庄时,还看见一两点灯火,听到几声狗叫。黑暗中的运河,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伸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