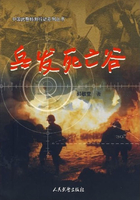九王爷皱紧地眉头终于松开了些许,点点头,心道,这小太监还真机灵。
星宓一看阿玛的表情,心底忽地涌上一股气,鼓着腮帮子立即提反对意见,道:“贝勒和格格的命是命,太监的命就不是命吗?你们谁都不准去,我要自己去。”
王妃气得牙痒痒,知道她这个怪胎女儿的“人人皆平等论”又爆发了,禁不住怒道:“我的小祖宗,你闹够了没有?这是最好的方法了,你阿玛若肯让小铁子去,自然是派最好的船队保护他的。如果你还执意不同意,那就谁都不准去了,你喜欢跪就跪着好了。”
小铁子的眼中蓄满了泪,除了懿祯贝勒爷外,第一次有人将他的命看成是命,所以满腔的感激和欣慰让他更坚定了信心,为了不让贝勒爷为难,为了星宓格格的心意,他小铁子赴汤蹈火再所不辞。于是,他又重重地将头磕向了地面,大声道:“格格,奴才小时候曾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奴才福大命大,能活到八十岁呢。所以,奴才求格格成全。”
见星宓格格依然故我,小铁子再磕,再不理,再磕,偌大的书房中,顷刻间,只余闷闷地额头碰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在回响。
“够了。”懿祯摊开手掌接住小铁子再次磕下去的头,语气一反常态的僵硬。转头对星宓道:“星宓,就这么办吧。”
星宓含泪看看懿祯,再看看小铁子已红肿起来的额头,只能妥协的低下头去。
风和日丽的五月天。
暖暖地,带着淡淡咸味儿的海风轻拂着耳畔。
几缕青丝搔过粉颊,痒痒地,舒服得让人忍不住想叹息。
“唉~”站在港口痴盼的可人儿,却是真的叹了一口气,惹得在一旁相陪的小丫环轻锁了眉头,不忍地道:“格格,您可别再叹气了,福晋曾说过,叹气多了,人会变老的。”
星宓轻横了翠儿一眼,不禁笑嗔道:“我才多大啊,就担心老?”
翠儿见星宓终于展露笑容,心中欢喜,也不怕主子嗔怪,继续道:“格格年岁尚轻,自是不必担心,但是奴婢还听懿祯贝勒爷说起过,嗯……喜则伤心,悲则伤肺,恐则伤肾,怒则伤肝,思则伤脾。”努力回忆,还好记忆力不差,居然全部记起来了,嘿嘿。
“几天来,格格您一见到有军船回港,就会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跑去寻问小铁子是否已接了靖月少爷回来,是喜;看到船上并无小铁子和靖月少爷,就会失望,是悲;怕小铁子找不到靖月少爷,又怕再也见不到靖月少爷,也担心小铁子就这样永远呆在那座孤岛上,是恐;格格还在气王爷不让您亲自出海找靖月少爷,是怒;长久以来格格都在惦念着靖月少爷,是思。这样算来……”
“这样算来,我是五脏俱损,命不久矣啦。”星宓打断翠儿的长篇大论,翻翻白眼,抢着道。
“啊,”翠儿忙的捂住嘴巴,顿觉失言,“扑嗵”一声跪倒在地,惊恐地道:“奴婢该死,奴婢一时失言,求格格恕罪。”
星宓自然明白翠儿是在为她着想,怎会忍心苛责,便上前扶起她道:“还好你是跟着我,否则就你这张嘴啊,还不知会惹来什么灾祸呢。”
翠儿喜道:“多谢格格,翠儿愿意一辈子为格格做牛做马伺候格格,那样翠儿就不怕会惹什么灾祸啦。”
“你这丫头,顺杆儿爬的鬼灵精。”星宓掐了掐翠儿还有些婴儿肥的*的细嫩脸蛋,笑道。看到翠儿,星宓会时常想到音儿,虽然音儿没有翠儿机灵,又胆小又粘人,有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憨憨地,但却最是贴心。音儿比翠儿大了两岁,如果现在还活着,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粉妆佳人了吧,唉。
“格格,您又叹气?”翠儿忙的又要控诉。
星宓翻了下白眼,这丫头,连她在心里叹气都听得到,真是成精了。
“表姐?表姐——”
一个正处于变声期的十三、四岁的长相俊俏的男孩子的喊声由远及近的传来。
星宓寻声望去,看到表弟袥辰正匆匆忙忙地跑来,一上前便拉住她,道:“表姐,镇里来了杂耍艺人,咱们去看热闹,好不好?”
为了在港口第一时间等到靖月,星宓离开了京城的王府,来到舅舅家暂住,星宓的外公曾在朝做官,但晚年因厌于官场的勾心斗角,辞官回老家做起了生意,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在这一地带的沿海城镇都有了其经营的势力范围,现在传到了袥辰父亲这一代,家业更是庞大了不少,已俨然成为了一方巨贾。
袥辰是星宓舅舅最小的儿子,仗着家里财多势大,镇里所有的孩子都得让他三分,从小便成了这里远近闻名的小霸王。其实这孩子只是顽皮成性,捣蛋耍颇,心性并不坏,对于星宓这个漂亮表姐更是打心眼里喜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不忘给表姐,所以,星宓的舅舅才放心让他做星宓的小保镖。
“好吧。”见日已西斜,星宓点点头,下意识的望向远方的海天交汇处,今天也等不到他了吧。
“走啰。”袥辰高兴地拉着星宓的手走向马车,边走还边说着他刚刚由侍从处得到的确切消息:“听说还有耍猴的呢,表姐,你看过耍猴的吗?那些小猴子都好可爱呀……”
虽然袥辰一直都尽守着小保镖的职责,但是孩子就是孩子,总也摆脱不了贪玩的天性,在闹市区,在耍猴的,顶碗儿的,扛大旗的种种杂耍艺人过人的绝活的吸引下,袥辰还是在不知不觉间放开了星宓的手,之后两人又在拥挤的人潮中被冲散了。
当袥辰由玩乐中回过神来时,早已不见了星宓的身影,心中懊恼担忧不已,立即吩咐侍从到处寻找。
不大一会儿,有侍从回报说,在离此处不远的小巷口发现翠儿昏倒在地。袥辰急急而去,扶起翠儿,掐了会儿人中穴,翠儿才悠悠转醒,袥辰忙问缘由。
翠儿不见主子星宓的身影,骇然得不知所措,却还是含着眼泪,急道:“奴婢和格格被看杂耍的人群冲向了路边,格格说累了,于是我们便躲过人群,打算到巷口那边的露天茶摊子去歇歇脚,可是没想到,刚转过巷子,奴婢就不知道被什么人从后面打了一棍,立时昏倒在地,呜……格格……格格不见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袥辰心惊的暴跳如雷,指着一帮侍从的鼻子骂:“你们这帮没用的狗奴才,就光晓得跟着我后头拍马屁,不知道我表姐在此地人生地不熟的更应该好生伺候着,现在表姐人不知让哪个找死的狗奴才给掳了去,如果有个好歹,我要你们几个的狗命。”
一帮十六、七岁的小侍从被吓得战战兢兢地跪倒一地,忙的磕头赔罪:“少爷饶命,少爷饶命……”
“少给我在这儿废话,想让我饶你们可以,还不快去找。”处在变声期的嗓子本就喑哑得可以,此时更是暴烈得失了常声。
“是……”小侍从们再不敢怠慢,爬起来便找路四下逃窜了去,虽然小少爷平日里被称作小霸王,但是他却从没有像今日这样暴怒过,看来这回是真的动了大气。
星宓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粗绳绑缚住,连嘴巴也未能幸免的被布条封住了,环顾四周,她所在的地方像是一个破旧的、年久失修的月老庙,堂**奉的月老爷爷的衣着、妆容虽然都已掉漆褪色,不复昔日容光,但看起来仍是慈眉善目的,莫明的让人觉得安心些许。
为什么自己会被人抓来这里?星宓忍着头痛努力思考着,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应该没有仇家吧?唉,星宓不禁叹息,她从小到大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好不?也不知是谁这么用力地打她的头,一定肿了一个大包,哼。
正思绪凝结时,忽听庙外有人的脚步声传来,星宓立即闭上眼睛,靠在柱子上,装作昏迷未醒的样子。
“她醒了没有?”一个年轻的男声。
“回老大,还没有。”另一个像是守门的男声回道。
两人又在门外说了句什么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推门进来了,脚步声沉稳有力,由远而近的传来,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星宓的心上,令她紧张得全身肌肉都在收缩。
然后,她感觉到他停在了她的面前,他低下了头,俯首遵循着她的脸,几乎鼻息可闻。
不行,她受不了了,除了家人、懿祯和靖月外,从没有人离她这么近过,猛地睁开眼睛,向那张近在咫尺的容颜看去,狠狠地,带着深深地恼怒。
面前的这张脸并未显露意外,也未被星宓眼中的狠意所恼,邪邪地一笑??道:“就猜到你是装睡。”
他就是老大,刚才在门口说话的人就是他。
星宓横了这老大一眼,脑袋转开,努力与他拉开一些距离,虽然心里很害怕,但还是要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的心态来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你竟然是个格格,还真是没想到。”来人伸手拿掉了星宓嘴里含着的布条,看出星宓转动的眼珠中一闪而过的光芒,不紧不慢地继续道:“别妄想喊人来救你,这里是一座早已荒废多年的月老庙,方圆十里地都不会有人经过的。”
星宓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四周,空气凝滞得仿佛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似的安静得出奇,便知他所言非虚,内心里突燃的求生欲望呐喊宛如在瞬间*底气。
“抓我来干嘛?”既然一时之间跑不出去,总要知道自己为何有此一劫吧。
“告诉你也没有关系,本来我们是想抓富察袥辰的,可是那小家伙太机灵,身边还总是有很多侍从跟着,很难下手,这次在街上发现那小家伙对你宝贝得紧,料想定是至亲,便抓了你来。呵呵,本想着是退而求其次,没想到却让我们在无意间抓到了个来头不小的正主,倒是意外的收获啊。”
“为什么要抓袥辰,你们有什么目的?”
紫禁城。
长*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给皇太妃请安,皇祖母吉祥,皇太妃吉祥。”正厅中,懿祯给坐在正位的皇太后和皇太妃请问安礼。
“快起来,”年过六旬,雍容华贵的皇太后一见小外孙儿,自是喜上眉梢,慈爱的伸出手去,边示意懿祯到她的身边来,边道:“今儿个怎这么早来请安呢?”
懿祯谢恩起身后,忙的紧走两步,将手放入祖母的手中道:“孙儿有事想请示皇祖母。”
皇太后一听这话,似乎早已是了然于胸,与一旁的皇太妃交换了个眼神,忍笑道:“说说看,什么事啊?”
“孙儿见近日来天气晴好,想出宫游玩几天,望皇祖母成全。”懿祯低头悄眼观察着皇太后的神情,生怕她说个“不”字。
“你前几日不是染了风寒,直咳嗽吗?如今病还没好利索,怎能出宫呢?”
“回皇祖母的话,孙儿的风寒已经好了,您听,我的嗓子也已经不哑了。”
“嗯,”皇太后仔细看了看懿祯的神色,点点头道:“小脸儿确是比前几日红润了些。”
懿祯面上刚露出喜色,却听皇太后又道:“可是哀家昨儿个派人问了严太医,他说你还得吃几副药巩固一下身子才好啊。”
“皇祖母,孙儿的病真的已经完全好了,只是严太医太过小心而已,整日的让孙儿吃药调养,皇祖母,孙儿好久没有出宫游历了,现在正是春暖花开,远足踏青的好时机,您就恩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