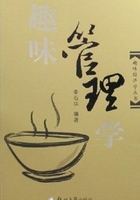引言
西方传教士马可·波罗曾在元朝时期来到中国,他在游记中记述了中国的文明富庶,无意中促成了西方想象中美好中国神话的产生,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工业文明的确立,西方人逐渐获得了一种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在一连串的失败中,西方对于中国也由美好的想象转变为直截了当、不加掩饰的蔑视,中国人相应地成为了西方"他者"眼中的"弱国子民"。
至于远东的日本,其文化是在长期学习、吸收和模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中国堪称日本的文化导师。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成功,日本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摆脱了历史文化上的自卑感,同时民族自大心理急剧膨胀,对作为导师的中国报以了无以复加的轻蔑。
这种感受内化到了现代留日作家集体无意识深处,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映,如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和藤固等都对此进行了书写。由于民族歧视的存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中中日两国男女两性关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并渗入了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使得中日跨国婚姻具有超越了个人属性而国家化的倾向。另外,作为初次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国家,日本具有暴发户的心态,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竭力把中国边缘化,以一种"东方学"式的眼光来打量中国,把中国看成"凝固"和"没落"的国家,把中国人相应地看成了"弱国子民"。由于承受日本这种特别注视的体验被创造社作家形诸笔墨,他们小说文本中多书写"零余者"的忧生之嗟,所塑造的留学生形象也被作为注视者的日本打上"东方学"的色彩。
第一节跨国婚恋的障碍
一、现代化成就与日本式"东方学"的形成
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举全国之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此后,日本人看待中国的态度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仰视"变成了"俯视",不知不觉间种下了轻蔑的种子。而随着日本国力的蒸蒸日上和中国的每况愈下,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恶劣态度也就愈加无所顾忌。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除少数人的好意外,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一片黑暗的",中国留学生"实已处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况中"。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歧视和轻蔑,当时许多在日中国人都有深切的体会,他们的笔保留了对此沉痛的记录。郁达夫作为在日本留学近十年之久的中国学子,对此自然不会陌生。他曾经根据自己在日本的感受和经验,痛切写道:
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能够坦白到像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明治维新"被称为"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经过这次改革,日本"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王韬在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写的序言中说到,日本进行现代化改革之后,"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丕然一变其积习"。而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有相当一部分诗作就形象地反映了日本现代性生活的某些方面。如对于现代消防神奇威力和速效的描写:
照海红光烛四围,弥天白雨挟龙飞。
才惊警枕钟声到,已报驰车救火归。
(第四十七首)
日本常患火灾,学习西方之后,设消防局,专司救火。"弥天白雨挟龙飞",可见救火水龙的威力之大,故才有末二句极写灭火的迅速。
另有一首写照相的云:
镜影娉婷玉有痕,竟将灵药摄离魂。
真真唤遍何曾应,翻怪桃花笑不言。
(第一百七十五首)
像这种威力如此之大、见效如此之快的救火车,以及神奇莫测的摄影术,当然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新产物,无疑体现了日本现代化的成就。诗人对域外先进科技和新生事物有一种"陌生感",充满了惊奇和羡慕之情,而将这种题材纳入自己的审美视野,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诗人先进的思想和开放的意识。类似诗篇还有写医院("维摩丈室洁无尘")、博物馆("博物千间广厦开")、博览会("左陈履宪右冠模")、新农艺("重译新翻树蓄篇")、人工授粉("初胎花事趁春融")等。这种诗歌题材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堪称是别开生面,耳目一新,闻所未闻的。黄遵宪写这类诗篇,又详加小注,不是对"陌生化"的猎奇,其良苦用心在于:希望中国人由此得到启发,维新变法,学习日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当然,由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确实可以管窥出日本当时在现代化程度上远远领先于中国。
坦诚地说,日本在文化上虽然缺乏独创性,但却是一个极其善于模仿的国家。它在文化上模仿中国,在政治、法律、军事、教育以及生产事业上效法欧美诸国。"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现)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上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混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说侮辱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咎由自取,还是说得含蓄一点叫作威胁的好。"由此可见,日本"现代化"的成就,对中国构成了现实压力,对中国留学生也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成为了他们"弱国子民"体验的源泉和有机组成部分。
日本在文化方面师法中国,但是又进行了自我改造,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意义的。"这种"创造意义",导致了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上,在情感模式上,还是在精神信仰上,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仅就道德规范而言,日本人效法中国,确实学会了表面上的恭敬有礼,但是对于中国道德规范中至高境界的"仁爱",不仅没有学到皮毛,反而还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屣。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道德规范就是将'仁'、'公正'、'博爱'上升到一个绝对的高度,按照这个标准,人们会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18世纪的日本神道家本居宣长曾这样写道:'当然,这种道德规范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用的,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方法。'近代,不少日本佛教学者及民族主义者也都以这类话题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地加以改造,经过篡改后的日本文化当然不同于中国本土固有文明;而当日本文明中出现"仁爱"缺失的时候,即使日本人对自己天生"性善"有着一厢情愿的固执信仰,但是因为战争胜利和现代化的优越感,他们形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东方学",对于中国人仍表示了无以复加的蔑视。
日本和中国都是在西方列强进行全球性扩张的历史语境下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因为"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现代化运动的成功,而中国则因为种种原因,现代化进程一再受阻和中断,这样导致了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就是这种差距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和证明。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清政府正式向原本不受重视的日本派遣留学生,这既是对日本先进性的肯定,又意味着对中日之间现代性差距无奈的接受。但是因为种族歧视、"现代性"的压迫以及文化上的差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弱国子民"的感觉。首批留日学生13人中,有4人因为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歧视和嘲弄,入学不到一个月便自动退学回国了;而在整个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中国人一直都感受到这种压力和苦楚。
二、创造社作家对跨国婚恋障碍的书写
现代留学语境下的感受,在中国文学中有深刻的反映;而文学对这种感受的书写,又来源于现实依据和生活基础。当然,中国学子在不同的国度留学,对"弱国子民"的感受也有所不同。有论者指出:"就'弱国子民'反映的强度而言,首推留日文学,其次是留美文学,再次是留英文学,最后是留法文学","就'弱国子民'的心理内涵及其反应方式而言,留日文学与留欧、留美文学又有差异:前者集中于种族歧视,后者是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和文化差异三味俱全,互相作用"。
这种"弱国子民"的感受,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中,主要体现在颟顸自负的日本军官在中国留学生面前肆无忌惮地叫嚣吞并中国,并且无视中国辛亥革命后改元的历史事实,故意把"清朝"与"民国"不分,以达到曲折隐晦地贬低中国的目的。在鲁迅的笔下,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人智力的怀疑,"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而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中日跨国婚恋上。这种创作,以创造社作家为主体。创造社作家这种创作取向,堪称是共同经验的心理凝聚物。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求偶不得、婚恋受到歧视多有反映。正如郁达夫所言:"国际地位的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1921年7月成立的"创造社",被当时文坛称为"异军突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陶晶孙和穆木天等。他们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受到了域外文化的熏陶。在他们留日期间,较多地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其创作主张与"文学研究会"自是不同。郭沫若曾经说过:"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正是初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另外,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
创造社作家在留日期间受到了风靡日本的"私小说"创作的影响。日本"私小说"吸取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同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和转化,淡化对外部景物的描写,主张再现自己的心境,侧重于作家内心的大胆暴露,包括对自己个人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的暴露。初期创造社的小说,就是以此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因此具有抒情特质和"自叙传"色彩。
创造社作家留学日本期间,在当时的世界秩序和中日国力对比来看,难免经历了"弱国子民"的痛苦体验。这种痛苦体验具体说来,包括种族歧视、"现代性"的压迫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错位等几个方面。日本对中国的歧视,较之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兆忠先生说过:"就'弱国子民'反映的强度而言,首推留日文学,其次是留美文学,再次是留英文学,最后是留法文学。文学上的这种反映,同实际的历史情景应当说很一致。就'弱国子民'的心理内涵及其反应方式而言,留日文学与留欧、留美文学又有差异:前者集中于种族歧视,后者是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和文化差异三者俱全,互相作用。",因此这种痛苦沦肌浃髓,刻骨铭心。又因为处于青春易感时期,这份经历作为他们人生最深刻的感受和体验,自然会被形诸笔端,物化为饱含血泪的文本,其间所凸显出来的留学生形象,就是抒情主人公,颇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