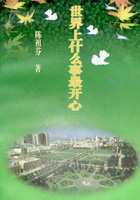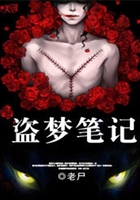第一节历史语境的变更与中国中心观的破产
在世界"轴心时期"(the Axial Period),高度发达的文明实体,大体上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国。它们通常被尊为"四大文明古国"。"轴心时期"奠定了世界现有的文明形态,也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人类今天所拥有的许多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实体的贡献。
前三大文明实体所在区域之间地理位置虽然不算近,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随着文明不断的发展成长,它们之间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相互交流。至于交流的方式,大致有商业贸易、政治外交、学术往来、战争攻伐以及族群迁徙。这种交往促进了相互的影响,"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向外传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与其说是由于采纳了某些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毋宁说,是由于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则。有关文字的概念虽说取自苏美尔,但各自独特的文字系统却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渐形成的"。又如起源于叙利亚地区的犹太基督教,古巴比伦人的几何和历法,印度的民间传说、算术和医学,都广泛地影响了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期内,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相互补充,它们和罗马法一起,构成了近代欧洲文化的三个主要源头。
上述三个区域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建立稳固而持久的政权,并以自己为中心统治边陲地区,即使某些民族和国家希图顽固地坚持自我中心,但现实又会把这种妄想予以粉碎,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无中心的多元混合态势。这种无中心的多元混合态势给人类带来莫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容易以平等的心态去了解异己的"他者",即使暂时不能和平相处,但终究能够孕育出平等相处的原则。从较浅层次的彼此接触逐渐发展到较深层次的自觉交流,再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既是人类通往和平相处之境的一般程序与规则,也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有学者指出"由于东西知识的融会,哲学家的胸襟眼界都大大地比以前开阔了。我们姑且不去细论在希腊化时期兴起的斯多噶和伊壁鸠鲁两派哲学的内容。但有一点是可以指出的,即这两派哲学家所说的人已经不是属于狭隘的城邦的人,而是属于覆载之间的世界的人。他们已经泯除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人和'蛮人'之间的界限,认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的幸福。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无疑是亚历山大帝国以后东西两方交互渗透的历史现实在思想上的反映。"
反观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和其他文明实体所处的地理环境很不相同,它东南临海,但是隔海相望的岛屿至少在公元11世纪以前都是蛮荒之地,北部是蒙古草原,西边则是戈壁荒漠,只有一条细小的商路--被历史和传说无限夸大了的丝绸之路通往波斯,而西南面更有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和青藏高原作屏障,隔绝于其他早熟的文明实体。在这样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绝无可能,华夏文明一直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成长,形成了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同时也催生了"中国即天下"的观念。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交一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
在相对封闭环境下孕育的华夏文明,长期以来一直领先于周围的国家和族群,基本上是呈向周边辐射的态势,从未遇到过巨大的挑战,即使偶尔有域外文明舶来,也无不被同化和吸收(例如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就已经传入中土,但是中国人却把它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所以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冯友兰说过:"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重要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由于长期处于"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的地位,难免就产生了"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的心态和优越感。这虽说是"固人情所宜然",但无疑隐含着深刻的危机。
在古代,"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由于交通、通讯和科学知识极不发达,人们对世界和宇宙知之甚少,只能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旅人的一点见闻来建构他们观念中的世界模式。在对世界进行观念型塑的过程中,人们都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因此许多民族都有"世界中心意识"。"如法显《佛国记》称印度为'中国'而以中国为边地,古希腊、罗马、亚剌伯人著书各以本土为世界中心。""细考民族中心意识,大约一半出于无知,一半出于傲慢和偏见。无知助长了傲慢和偏见;傲慢、偏见反过来阻碍了人类的求知。"尽管如此,但是在世界上,很少有人像古代中国人一样顽固地坚持自我中心意识,总觉得自己处于世界中心,"我们今天把中国想成'中华(Chinese)之国',但在过去她并不是把自己想象成'中华',而是'位居中央'(central)之国。"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就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尊"夏"贬"夷",严于夷夏之防,在"夏"与"夷"之间缺乏平等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孟子还幻想过一种万邦归附、天下归心的世界秩序,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莅中国而抚四夷","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引用《诗经》的话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种不平等的高姿态跃然纸上。
庄子似乎显得要客观和清醒许多,《庄子·秋水》篇对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也,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这种比较客观的"中国观"和他的宇宙观有关。其实,庄子这种观念,严格说来只能算是对"中国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一种观点,并不是一种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观点,因而并不能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古至今,坚持中国"世界中心观"的人很多。《史记·赵世家》中公子成说:"中国者,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而最能够代表中国"世界中心观",或者说把这种观点发挥到极致并至为完备的,是宋代的石介,他在《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可以说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人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中外关系最为经典的描述和表达。尽管岁月流逝,朝代更迭,但是根深蒂固的"内夏外夷"的文化观念却从未动摇。
这种"内夏外夷"的观念渗透融合在儒家文化的礼制等级秩序之中,形成一种极为稳固的具有卑尊意味的国际秩序。历史上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完全是一种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其高下有别,正如乔木和幽谷一样,中国对于四夷蕞尔小国,向来都是采取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不屑于俯就和亲近,正如孟子所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而四夷小国则应朝拜和归附中华,孟子还虚构出了一幅天下归附的乌托邦图景:"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在中国人塑造的天下模型中,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世界的中心,在文化上也处于世界的中心,周边的蛮族都没有受到启蒙教化,缺乏典章礼仪,因而属于化外之民。《礼记·王制》中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文化不发达的"蛮族"如众星拱月一般环绕在华夏的周围,它们与华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附庸和宗主之间的关系,在文明上占有优越性的华夏"光被四表"、"声教迄于四海",周围"蛮族"则"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
当然,思想观念来自于现实生活。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世界中心观,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华夏文明在客观上处于绝对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等方面,更体现在文化上。
但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一种"遏制领先法则",最发达和最先进的社会要想永远保持其领先优势是很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发达的社会可能更适应变革并在变革中逐渐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这种优势却又成为了抑制其进一步发展的负面因素。这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上长期大一统的格局,在文化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它的文明形态和文化心态,使中国人形成了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自大意识,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与之相竞争的国家和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文明优于其他文明,在其他国家和文明那里没有自己需要学习和值得借鉴的东西。在西方世界开始工业革命的同时,中国人却安于现状、自高自大、心满意足,最终因为没有与时俱进而落伍了。相反,恰恰因为中世纪欧洲的黑暗和落后,所以他们渴望学习,积极探索,并且能够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最终由中世纪的黑暗转变成为了现代化的文明,成功地超越了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和谐稳定为目标,以伦理道德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文化价值体系。这套体系以社会周期性的治乱交替和牺牲人的个性与创造性为代价,衍生出一套精密完备、伸缩自如的道统规则,它既有助于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同时也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沉重包袱。自然经济不但提供自给自足的消费用品,同时也产生出顽固坚硬的保守思维。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不久,中国就开始了海禁,不但错失了走向世界的大好时机,反而自绝于世界,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里。在利玛窦向明神宗献世界地图之前,中国人一直坚持"天圆地方"的观点,也坚持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信仰,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可以划分为东西两半球。在利玛窦所献的五洲图上,中国只是一小块,并且不在世界的中心,结果受到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士大夫群体的批评指责:"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检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并说"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
面对人们的不满、生气乃至愤怒抗议,也为了传教的需要,利玛窦只得迎合中国人的自大心理,于是他灵机一动赶紧抹去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并且"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利玛窦献五洲图,意味着西方人已经具有了世界眼光,并且意味着一个世界交往接触的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但遗憾的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它的象征意义。直到乾隆中叶,中国人对与国外交往仍然普遍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态度,在鄙薄下隐藏着恐惧情绪,在不屑中包含着防范心理。乾隆二十四年(1759)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不但禁止国人与"夷商"接触,甚至还出台了一系列法令禁止中国人出洋,同时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明确规定,不准"夷商"在广州住冬,不准"夷商"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据张德昌1935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一文介绍,一个名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为"教授夷人读书"(指学习汉文)的罪名,竟于乾隆二十四年被处以斩首的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