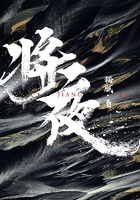年近半百的仁青平措从南峰山上下来联系物资的运输。他站在我的面前,我望着他的手——被冻伤而截掉了六根手指的手。他憨笑着朝我摇摇手,表示这点儿老伤无所谓。这是1975年登珠峰时,在海拔8600米的高度,他从冰壁上滑坠了近200米,差一点儿葬身冰谷而留下的永久纪念。右手的四根手指、左手的两根手指被截去了,他成了三等残废。在此后的登山过程中,一到艰险地段,他必须用牙咬住保护绳向上攀登。而他那辉煌的战绩,也恰恰是在他成了三等残废之后创下的!——他骄傲地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登上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人!
1981年,希夏邦马峰(8012米)。
1985年,卓奥友峰(8201米)。
1988年,珠穆朗玛峰(8844.13米)。
……在多次登山活动中,他都任攀登队长。在梅里山难发生后,又是年近半百的他率队员自西藏星夜赶往云南协助救援搜寻。他的出现,会给无数登山者带来信心和希望。他似乎只是为山而存在的。他是喜马拉雅的骄子,更是祖国和藏族人民的骄子!
他数次侦察、攀登过南迦巴瓦峰。1984年正式攀登南峰时,他曾准备把生命交给南迦巴瓦。乃彭峰上,至今鸣响着他请战的回声——”我下去。下去上不来了,就是我‘光荣’了,这也算指出这是条绝路,队友们就别下去了……”七年后,他已48岁,又来了,当高山协作队员,为战友们运输物资。
他心中的滋味,是不屈而又怅然的,年龄在那里,注定他不能成为南峰的第一批登顶者。一个登山者,心中隐忍的痛苦,能有比这更大的吗?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背起物资,为战友扑进茫茫的风雪之中。
仁青平措的人生之路,浓缩着很多藏胞自农奴时代迈向新生活的光明之路。他194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奴之家,从小就给领主放牛羊,他和他心爱的牛羊爬过多少座山?数不清了。数不清的,还有茫茫人世的苦难。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他才有权利选择了登山这个毕生的事业。山,给他的太多了,带给他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生和世界。第一次到北京来集训,他才知道,山外还有这样一个花花绿绿又真真实实的世界!再站到山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地方。他饱尝过人生的苦难,怀里才有一个永远明亮的今天和明天。所以,雪崩、滑坠、生死线,他出没往返,从不回头。
山的儿子,应是骄子。
登山界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小愚公”。我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1988年,我在北京登山基地的宾馆里,参加一次全国体育报告文学评选。一个黄昏,我在水边散步时遇到了他。我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第一次端详着这位英雄。看着他被截去六根手指的手,一种强烈的愿望在心中升起——我要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
一直到这次登山之后,我才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仁青平措。他丝毫不“愚”,相反却固守和珍存着一个最崇高的登山者的情怀。1981年,他作为高山协作人员,协助一支中日联合女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协作人员的任务,就是运输等协作,不允许登顶。但他被接近顶峰的日方女队员田部井淳子的不屈精神打动了,甘愿违犯规定,拉起田部井淳子,攀向顶峰……在顶峰,田部井淳子强拉他合影,仁青平措却谢绝了,这意味着田部井淳子单独登顶成功。田部井淳子感动得一边流着泪,一边掏出了中国的国旗。峰顶,那飘扬着的祖国国旗,分明显示着整个中国的阔大胸怀和对世界人民的深情厚意……1985年,他任攀登队长,带着队员向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冲击。这是中国第一次向该峰进军。在山上,按规定,每一个行动都必须无条件听从大本营的指挥,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下令者负责。仁青平措当然懂得这一点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未向大本营请示,就率领着八名队员突击顶峰,终于成功……事后,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山的儿子,必是骄子。
还是听听他的几句话吧——登山回来,和别人一聊起,自己也真有些害怕。家里人哭,我也哭。算是高兴地哭吧。我这人没有文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到内地上大学。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将来干登山也行。不过,不能再像我这样没有文化。
他没有文化,他对明天只有这个小小的祈愿,祝他如愿,也一定能如愿!我想对他说的却是:“不,平措,你有文化。你在无数座你所攀登的高峰上,在那登山途中的狂风暴雪里,已为我们的后代创造了一种文化,那是珍贵的山文化,她给予人们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登山,人们会记住你的名字……”
加布从山上的营地撤下来了,他在喇叭口修路时伤了脚。队里为了保存突顶力量,让他下山医伤,休整后再上去。
司机群央背上一支枪穿过原始森林去迎接他。下午,我正在食堂的帐篷里采访老炊事员瑞师傅时,远方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我一听就是群央,赶快跑出帐篷,见群央一边扶着加布从林中走出来,一边高声唱着歌。加布一瘸一拐,看来脚伤得不轻。大本营里的战友都跑上去迎接他们,大家都惦念着加布的伤。群央帮他脱下鞋,见他的脚踝肿得像发面馒头,大家赶紧打热水的打热水,取药的取药。加布笑着说:“不要紧,过两天就又能往山上跑了。”大家这才放了心。
加布正当而立之年,曾于1990年5月,在中美苏和平登山队攀登珠峰时登顶。
我挂念着山上,便和加布聊起天来。
加布说:
建军这次不容易,父亲得了癌症在北京住院,母亲在新疆。谁知他父亲还能活几天?连在身边照顾一下都不可能。干我们登山这行的,都对不起家里人。1984年我在北京集训,准备一年后攀登那木纳尼峰。我母亲为我们受了一辈子苦,我长大了才明白母亲带我们有多难。我一去登山,进了山就想她。她更想我,为我夜夜睡不着觉。母亲有个愿望,就是要到拉萨去朝拜。1983年,我带她去了,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要不然我会后悔得哭死。那一次是我和她见的最后一面,早知道,我一定会多陪她几天。就在我到北京集训时,她病了,不久就去世了,死前最后还叫着“加布,加布……”。直到登山结束后,我和次仁多吉、大齐米等撤下来到了拉孜县,那天,我还去庙里给母亲请愿,愿菩萨保佑她老人家。晚上,我们围在一起喝酒,大家都不说话。我很奇怪,看到队友们喝得比往日都多,眼都红了。我没喝多少,但心里不知为什么不好受,就回房睡了。谁知,次仁多吉摇摇晃晃地进了我的房间,发呆发了半天才说:“加布,有件事,不知怎么对你说。”我呼地爬起来:“说吧,怎么说都行!”我感到不好了。“你母亲去世了。”我不信。大齐米也说:“是的。加布,你别难过。”这时我才知道,母亲死了都快一年了……那几天,我不吃不睡,也流不出眼泪了,只拼命抽烟,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我再去寺庙,花了很多钱,不能祝母亲身体健康和平安了,只求她原谅我,求菩萨早日超度母亲,在西天不再受苦。当天我赶到拉萨,进门就问舅舅,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舅舅哭着说:“你母亲也不让告诉你,怕你登山时心里着急出事……”我放声大哭……我去大昭寺请回酥油,在母亲死时的床前,点上长明的酥油灯……这,也是一个山的儿子。
为了山,他永生都感到对不起母亲。慈母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还了。
不仅是一个加布。
加布讲到的陈建军,父亲在癌症晚期时,千里迢迢从新疆赶到儿子工作的北京住院,却见不到儿子。我因为回京给日方《读卖新闻》社送资料而提前下山了,便带着从大本营的话筒里录下的他给父亲的话,来到老人住的肿瘤医院。我握着老人的手,打开了录音机:
爸爸,您那么远到北京看病,我又不能在床前伺候您……您要多多保重,等着我!等着我回去……老人曾是一位军人,是他把儿子送进登山这个行业的。他那慈祥的脸上,泛起了欣慰的微笑。但是,他的双手在抖……老人对我说:“请告诉他,我很好,就说我的病快好了。叫他和同志们紧密团结,完成好登山任务。”
还不到一年,老人就去世了,带着他对儿子的爱和对登山这项事业的理解。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安息!愿我们任何时候提起山来,都不要忘记这些登山者坚强的父辈及所有的亲人!
建军及所有的汉族队员们,也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喜马拉雅的儿子!
喜马拉雅。祖国所有的雪山。雪山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