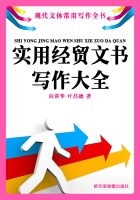高全根原籍是河北深县人,1957年来到北京的父亲身边。1964年上的北京四十三中学。两年后,“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一定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出来了,高全根是班上第一个入团的干部,在学校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时,老师问他能不能带个头?高全根说行,随后拿起笔就写了下面一行字:我初四班高全根,坚决申请到内蒙。写完后就交给了学校。回家他也没让父母知道。“就是知道了,当时他们也拦不住。”高全根说。没几天,军宣队就批准了他和另外班上的15名同学,一起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高全根说他们不是兵团,而是真正拿工分的牧民。这是1968年的事。到1971年时,与高全根一起下乡的另外十几位知青走的走、跑的跑,只剩家里没门路又穷得响叮当的高全根还留在旗上。一天,他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对他说当地的乌达矿务局五虎山矿要招工,问高全根去不去?他说那就去吧。就这样,他被幸运地招到矿上当了一名每月拿82元工资的挖煤工。这在当时,能从牧民变成吃“商品粮”的工人简直就跟进天堂一般。但毕竟内蒙四子王旗是个风沙和冰雪围聚的戈壁滩,矿上的生活也极其艰苦。那时知青们对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幻想,不多久高全根就和矿上同事的一位表妹结了婚,之后就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全家人就靠他一个月82块工资维持着。到了80年代中后期,知青可以回城了,高全根因为当了矿工又成了家,所以按最初的政策他只能把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孩子送回北京。到了1992年,知青政策又有新的说法: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就可以把全家迁回来。已经离开北京20多年的高全根觉得这是个机会--主要是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个大学上,所以便托人联系了京郊的一个接收单位,于是全家回到了久别的北京。但是20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变化令高全根这位北京人面临了许多他想象不到的事,最重要的是房子问题。接收单位说,我们可以勉强接收你,但房子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北京有色金属粉末厂能接收高全根的最大原因是这样的工种一般人不愿意干。然而一个4口之家不能没有房子呀!北京又不像内蒙古农村,随便搭建一个小棚棚没人管你。在内蒙古苦了20多年的高全根没有想到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着急啊,大儿子已经进高中了,小儿子也快进初中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怎么能让孩子上学读书呀!自己的一生也就这么着了,可孩子的路才刚刚起步,不能耽误啊!他高全根难就难在他是个穷光蛋返回北京的,且还拖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两个读书的孩子。高全根在接收单位一个月也就六七百块工资,他用这份工资养活全家4口人已经省得不能再省了,哪有余钱在城里租房?无奈,老高只好托朋友帮助。朋友把他带到市郊十八里店乡周庄一队的一个猪棚那儿,说这里有个猪场仓库反正也是闲着,你看能用就住下,不要一分钱,老高还没看一眼是什么样的地方,一听不要钱就连声说“行行,不要钱就行。”
高全根就这样在离别北京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住下的“家”。哪是什么家呀?儿子第一个进的猪棚,又第一个吓得从里面逃出来:爸,这地方不能住人,耗子大得跟猫似的!老高不信,他进去了,脚刚刚跨进去,突然从一堆草窝里“噌噌”窜出两只硕大无比的耗子!老高惊呆了,犹豫了,可他想不出还能为儿子和妻子找到另一个可以跟这儿相比的地方--这儿不要钱,什么都不要。
“那几年怎么过来的,我现在连自己都不敢去想一想。”老高说:“也不是我这个人好将就,或者说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家庭好将就,没办法,我当年离开北京时就背着一床被子和一本语录,现在回北京时是带着老婆和两个大儿子回来的,能回到北京就是场梦。我跟妻子和孩子们经常说,我们是北京人,但又不全是,既然现在户口能落在北京,算是最大的福气了,其它的咱们啥都不要跟人家比。妻子和孩子都是听话的,他们跟着我已经吃惯了苦,但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这种苦与其它的苦不一样,这才叫苦呢!是那种不像人过的日子的苦。就在我回北京前几年那么难的情况下,也没有耽误过孩子一天的课。住猪棚后,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我自己也有一辆,是送他们两个外加接送妻子和自己上班用的。十八里店乡到最近的南城边也要近一个小时,而且很长一段路没有公交车。我每天要很早起来,五点来钟就得先送儿子走,儿子再倒换两次车再骑自行车在7点左右到校。我约摸6点来钟回到家后忙吃上几口再带妻子出门,将她送到有公共车的地方让她好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之后我再蹬车上自己的单位。晚上也是这样,先把妻子接回来,再去车站接儿子,每天儿子们回来最晚,不会早于八点钟。我看着孩子很争气,他们从来不吭一声苦,穿的衣服是破的,睡的地方就是猪窝,前面没有门挡,后面的窗没有玻璃,冬天刮风能钻进被窝,夏天最难受,蚊蝇到处都是,蚊帐根本不管用,孩子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嘴巴有一厘米长、身子跟苍蝇那么大的蚊虫。我说我也没有见过,只有在多少年没人住过的野棚草窝里才能见得到。我和妻子反正每天下班后就没什么事干了,可两个儿子不行,他们要做作业。冬天他们只能在猪棚外面的石板上做,你问有没有电灯?哪会有嘛!是人家遗弃的猪棚,不会通水通电的。我们做饭是靠的煤炉,孩子看书做作业用的是油灯,一直是这样。冬天冷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大概我们在内蒙古呆的时间长了。可夏天的日子就难了,猪棚不知有多少年没人用过了,那虫子蚊蝇横行霸道,我们一家就成了它们袭击的惟一对象。每天一早起来,看到孩子们的身上脸上都是红一块肿一块的,我心里又难过又着急,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再新的蚊帐不出三天就被大蚊虫咬穿了,真是苦了孩子们……”
老高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
“唉--日子总还得过呗。”长叹一声后,他继续道,“那些年里,我们全家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路上,孩子上学要比一般的同学多花至少4个小时路程。家里没有钱,所以他们尽量骑自行车,我都记不清到底经我手换过多少副车胎!看到孩子能骑车到城里上中学我感到有一种希望在我心头涌动。我两个儿子非常不易,他们从内蒙古农村的学校转到北京市的学校时,连本书都没有,起初上课时像傻子似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十分努力,也从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你们听起来可能不相信,可在我们家一点也不奇怪。”老高说着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你看我现在穿的,回北京快有10年了,我只添过两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缝缝补补再穿的旧衣服。孩子跟我们一样。我大儿子是在猪棚里考上重点中学的,又在199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语学院,考了534分,这个分那年是可以进北大的。二儿子高岭是在猪棚里考上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我二儿子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孩子,他进宏志班后学习特别努力,这是一个专门为经济贫困的家庭子女们特设的班,来自全市贫困家庭的几十位优秀学生,他们相互之间都在竞争。高岭因为自己路程远而耽误很多时间,又没有一个家而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时写了一篇很动感情的作文,苦诉为什么在这万家灯火、高楼耸立的首都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倾吐了孩子渴望有个哪怕能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的家的心情。他这篇作文让班主任高素英老师很感动,高老师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跟着我儿子来到了我们这儿,她当时看到我们一家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猪棚时,忍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高老师说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穷人家的学生,可像你们连个家都没有、只能住猪棚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和看到。高老师是大好人,她说她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解决房子。她后来带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住的猪棚现场采访,又向市里反映。1996年3月31日,在当时的北京市李市长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全家住进了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四口之家住这么个要什么没什么的简易楼里一间10多平米的房子太寒酸了,可我们全家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总算有个家了。”老高颇有几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一样装饰品--一个我们早已久违了的小管灯,说:“这灯是一个亲戚送的。它的功劳很大,已经把我家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大学!”
老高的二儿子高岭是1999年从“宏志班”考上北京农学院的。我问他现在家庭的情况怎样?他说他比以前心情舒畅多了,因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圆了他多年的梦。“我现在虽然日子过得还很紧巴,我自己下岗了,厂子只给一点社会保险,我和妻子俩人每人每天就有17块的收入,她在赛特那儿刷碗,我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要负担两个大学生孩子的上学费用几乎也是不可能,好在学校能免一点,孩子自己勤工俭学挣一点,加上我们省一点,所以紧紧巴巴这么过着。我这辈子没啥追求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现在都上了大学,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时,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丽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栋像鸟笼似的简易楼上,外面是喜气洋洋的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阵阵歌声、鼓声和踩气球的欢笑声。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机,给老高他们这栋“京城贫民窟”留下一个影,我想以此告诫那些生活在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家以及我们的官员,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应该再想些办法帮助他们。
采访高全根,使我对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据调查,当年知青中真正后来在1977、1978年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时刻,重新进大学又把光辉前程夺回到自己手中的仅仅是数百万知青的一小部分而已,像现在的著名作家陈建功,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著名导演陈凯歌等等社会精英。也就是说,大部分当年的知青由于那场“浩劫”而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辈子改写人生命运的结局。
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悲剧。
或许这也是中国今天的高考为什么越走越让人感到进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对考大学表现出如此的狂热与独一无二的选择。
十年浩劫留下的一代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反而成为加深了此后两代人共同渴求冲进大学门并“决一死战”的情结。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存在。
“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从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彻底沦为贫民阶层。”如今通过自学已在北京市某机关任副处长的崔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得异常激动。
“可不是吗!”他的话像汹涌奔腾的大江之水,一泻而下,“我是老三届的,后来到北大荒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没有参加高考,不能全怪我。当时一方面我们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方面我在团部任领导职务,工作忙脱不开身,把参加高考的时间让给了别人。如果说当时我自私一点,完全可以像别人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复习,去参加高考嘛。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当支部书记,工作还是那么忙,天天都要为几百号人的生存发展着想,还得经常跑外勤,哪来机会去脱产参加这个班那个班?我的档案你不信可以去看看,尽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之类,可在填写一张张先进上报表时,文化程度那一栏一直是高中毕业。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当年在兵团给我手下打杂的人现在个个是教授、局长。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为人家后来上了大学,身怀一张可以敲门的文凭,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张文凭‘水平'高呀--哪怕他读管理学的博士毕业生连最基本的一个车间都指挥不好,人家照样可以比我们早提拔到处级、局级岗位上。而我们呢,就因为没有进过大学,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无关。这公平吗?可有谁能改变得了?”崔兄的一番话听起来像是牢骚,实际上反映的确是当今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读高三,准备参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单位问问,我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先进分子了。我现在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呀,这我心里明白,处长局长也不会说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闲着,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乐得我能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学习上。你问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当然不错了,我希望他圆我的清华梦。现在我和爱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我会觉得自己一直认为的社会对我们这些当知青的不公算是可以逮回了,否则我一辈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约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们一起上他的一个“兵团战友”开的“北大荒”饭店隆重庆贺一番。
“其实我这样的情况不算什么,你要有机会采访采访那些没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那些知青们,他们为了孩子能上大学所付出的才叫人听后感动和受教育。”老崔向我作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后来我从市高招办的工作人员那儿获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长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开始后,我就留意了这样的对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点离我的住处都很近,高考那几天我天天特意往这两个考点跑--我在寻找我要的采访对象。8号那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自己在河北工作看上去已经成了“北方大妈”的考生母亲。这位考生的母亲明显特征是“土”--可以说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北京城里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现在我连小时候一起读书的同学都不敢见了,为啥?就是我现在这个样还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吗!”这位考生母亲一说话就擦眼泪,看着她满头银丝,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怜悯之情。在我保证不说出她的真名后,这位大姐才同意我的采访。
我这里称她为章大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