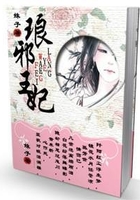自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认为,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而股份制形式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中最活跃和具有社会推动力的先进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几乎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国营集体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股份制经济形式开始被人们渐渐认识和接受。最早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这对当时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在许多年里,“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国这个红色政权的国度里,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剥削阶段的产物”。现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这不能不说是对实行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有集体经济是一场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国人眼里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国,它与当时农村所开展的“分田到户”搞包干一样,是实实在在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与“复辟”和“政变”没多大差别的惊天动地的事。
中国的股份制谁最先搞?忙碌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时间来总结,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又因为缺少实地考察与调查的能力而在书斋上添不出新的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这些文学家来完成实在有些可悲。不过到台州采访,让我再一次感到发现的惊喜。原来,中国的股份制发源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田埂上,根植于台州的农民中间……
现在有据可查的几个史实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区的温岭县社队企业局(那时还没有工商部门)正式发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为“社员联营”的企业营业执照。“股份制企业”是1985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之后才正式可以冠于的企业性质,台州的乡镇企业局当时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由社员合股出资办的企业起的名字为“社员联营”,用后来的名称就是股份制企业。这也是新中国工商企业史上第一个颁发的标明由几个自然法人“联营”的股份制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
目前有据可查的上面两份史料,足可证明台州是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这已被现在研究经济工作的专家所认可。其实,谈到台州的股份制,其开始和发源的时间远比这两个事件要早得多和广泛得多。
在我来台州采访之前,浙江有关媒体上就已经发表了一则令人鼓舞的文章,题为《寻找玉环股份制经济起源》,其中介绍了记者追寻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个“芦浦工艺厂”和那几个敢于最先吃螃蟹的农民。他们创办的这个股份制企业是在1967年,比温岭的那个有“正式户口”的“中国第一家股份企业“——牧屿工艺厂”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这时间正是中国“横扫资本主义”最激烈和严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台州人竟如此胆大妄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引见下,来到玉环的原芦浦乡那个“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旧址现场,并与几位当年办股份制企业的当事人见了面……
玉环是台州的一个县,面积很小,老玉环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后来又将温岭的楚门半岛划归了玉环,但陆地面积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环仍然是台州面积最小的县。可别看这弹丸之地的“海中玉环”,它现在的人均收入不仅在台州各区县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国的百强县中也名列第29位。玉环有数个“全国第一”的产业与产品,这与玉环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有直接关系。浙江籍著名作家叶文玲老师曾经对我说,写台州,绕不开玉环。叶玉玲是玉环人,她最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那天我是怀着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动的心情,跟着几个农民来到玉环芦浦分水村一块田埂上。一位本地农民老汉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闸上破旧的却依然挺立在那里的三间半砖瓦房,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当年办的最早的一个股份厂,当时叫红卫仪表厂……”
“就这个样啊?”我对影响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发源地竟然产生在这么一个极不起眼、极不壮观的地方,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心想:毛泽东当年打天下时,不也就是几根破枪、几把红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别小看这几间房子,当时我们还当宝贝呢!”林友泮老汉说:“这个地方办厂,一是不占集体房子,二是关键这里能上电线,好发动机器做工。”末后,他补充道:“我们办的是仪表厂,需要电动力。”
原来如此。
可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个农民能有这样几间房子办工厂、能在田埂上响起机器的轰鸣声,这在当时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时在农村,能响机器声的,只有集体农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脱谷场上的拖拉机声,除此再不可能有什么机器声响了。林友泮他们能在如此无遮无掩的广袤田野上开动机器搞“资本主义”,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起码是吃了熊胆!
在芦浦镇的镇委会议室里,几位当事人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看法——玉环农民在田埂上创办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果真历经了太多沧桑:
“我们那时办厂,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林友泮是当年办厂的“头头”,也是当时分水村的党支书,他给我解释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厂的第一句话这样说。随后他指指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六十来岁的老汉说:“最早是他颜祜庆出的主意。”
被林友泮点名叫颜祜庆的另一位老农笑了,冲林友泮说:“你是支部书记,我不向你说向谁说嘛!”
林友泮显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被老伙计颜祜庆这么一激,一边抽着闷烟,一边低头瓮声瓮气地说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进海里差点淹死……”
屋里的人顿时哈哈大笑。“老支书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颜祜庆这话让林友泮爱听,老人一个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最早动因确实是我。”看得出,颜祜庆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果然,他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几年兵。“我在部队时当过团部通信员。复员后,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穷,流血流汗干一年,连口饭都吃不饱。于是我就和也是从部队回来的本村社员蔡志昌,还有回乡知青、懂点机械知识的梁华星商量,说能不能几个人凑点钱办个厂,赚点钱。他们都觉得是好事。不过那时在集体之外办厂是件冒政治风险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芦浦一带有影响的支部书记林友泮商量。老林是个好人,用现在的话说,在当时也属于脑子比较开放的人。我们一说办厂的事,他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听我们发誓保证:本金我们几个人自己凑,赔了算我们自己的,赚了也给集体分一点。这样他也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同我们一起合股干。有支部书记跟我们一起合股干,这对我们来说等于借到了天大的胆子,所以后来就偷偷干起来了……”
“其实到底办啥厂,他们几个心里根本没有底。几个人想了几个月也没有拿出个主意来。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维庆,是坎门前台的支部书记。林维庆就建议我说你们办个仪表厂吧,他说他跟上海仪表厂有熟人,好有销路。这样我们才定下来办仪表厂的。”林友泮插话。
“干什么定下来后,就马上涉及怎么个干法的问题。集体的钱肯定不能用,再说生产大队也没有什么钱,即使生产队有钱,我们也不想借,因为一借集体的钱,今后赚了赔了不好说,所以我们商量大伙儿凑钱合股办厂。”颜祜庆说:“我们六个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后来因为买机器设备,钱不够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记得我们六人中有一个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个人合了一股。所以整个厂共有6股,股东是七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义是梁华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颜祜庆的记忆显然比较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有了合股的钱,可办厂仍然困难重重。先是我们想到楚门木器社学习,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里,人家听说我们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让我们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门前台大队的林维庆书记,他那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思想解放一点,所以我们就准备把厂办在他那儿,谁知才办了四个月,造反派武斗,我们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吓得谁也不敢去了。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搬回来自己办吧。这么着,我们又偷偷到温州瑞安去买了4台仪表机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环岛上作放水用的斗闸上的三间房子,算是我们的正式厂子……”
“那会儿,我们运回4台仪表车床跟打仗一样,很惊险哟!”颜祜庆绘声绘色道:“那个年代,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设备查出来,肯定是要没收的,而且我们还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书,认得的人多,也没人相信他支部书记干违法的事,所以我们从温州买回仪表车床后,将设备拆卸成零件,装进麻袋里,然后走的是不会被人查获的水路。开始也没有把设备运回到自已的地盘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门的林维庆那儿。我们几个人先在那里偷偷把操作的技术学到了,然后再把设备运回自己的家乡。”
“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想办合股的私人企业,只能‘戴红帽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响起机器声。”林友泮瓮声瓮气地又插话道。
“什么叫‘戴红帽子’”?我还头一回听这样的词,便问。
“就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办私人的企业。”颜祜庆嘴快说道,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没有发过言的叫娄昌福的人:“你问他,他最清楚……”
娄昌福原是芦浦公社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细地保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芦浦公社(后改为芦浦镇)的全部工业资料。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沓发黄的档案,一边向我介绍:“林友泮他们办的玉环县红卫仪表厂,是1967年在公社登记的。当时林友泮他们的分水大队叫红卫大队,所以他们是以红卫仪表厂名义在我们公社工业办登的记。”
“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我问。
“知道是林友泮他们几个人合股办的私人企业。”娄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们还敢批准他们办呀?”我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已开始, 批资本主义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在农村的最主要任务。
娄昌福笑了,说:“一会儿我再给你讲我们玉环为什么成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制发源地。我先说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为什么说它是戴红帽子,就是因为这个厂的名义是当时红卫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在当时并没有说不让办,虽然也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一些加工小企业还是有的,公社的工业办就是管这些事。林友泮他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办了玉环全县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我算弄明白了。“仪表厂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呢?”我问。
“很简单的螺丝。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产品,纯粹为别人加工的一种用在装订账册的螺丝。”林友泮说。
“可干了几个月后,还没有分一次红,玉环这地方的武斗就闹起来了,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而且这个时候上面刮起了‘打扫地下厂’的运动,我们的厂自然跑不了,只好关门。几个月后,‘打扫地下厂’的运动风吹过了,公社干部看到农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动找到林友泮,劝说他们重新办厂,并且公开同意原来集体所有的、位于芦浦尖山三眼陡门的半门房无偿的借给我们当厂房……”
“就是刚才我们在水闸上看到的那几间房子?”我打断颜祜的话,问。
“是。就是它。”颜祜庆继续说:“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公社领导能出面支持我们办厂,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儿的积极性挺高的。厂子很快重新动起来了。公社这时也要求我们安排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家庭的人进厂,算是交换条件吧。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厂干得很不错,股东们劲头很高,再次出资扩股,增加了流动资金。时候一长,我们觉得有些亏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维庆帮助聘请了一位上海小青年当我们的业务员,让他专门负责跑业务。产品也由单一的账册螺丝,到加工些其他产品。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这样,厂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让再开了。”
“我们不仅没拿到汇款,连手头买货的发票都没法报销,我损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声瓮气地插话道。
“林友泮他损失最多,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块。我们几个股东的损失也大呀!那时大家都穷,谁有几千块钱是了不得的事。本来我们几个凑的钱办厂,现在一下被查封了,损失惨透了。可没法找人说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说,人家说没把你们抓起来送进监狱里算是对得住你们了,你们还嚷嚷什么?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颜祜庆回想当年事,依然愤愤不平。
“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的事当时在我们这儿闹得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敢在‘文革’的风头上办股份制私有企业。”娄昌福接过颜祜庆的话,说:“过了大约两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农机厂,没有钱买设备,就想起了林友泮他们办过红卫仪表厂,所以就将他们的那些闲置设备全部充公到了公社农机厂。颜祜庆他们就闹,说那些机床是他们几个人出钱买的。公社干部一商量,说安排你们几个进厂,抵作你们先前的那些损失吧。老颜他们也没辙,就这么着平息了这事。林友泮是大队书记,后来被安排在公社养殖场工作。”
“这个股份制企业就这样彻底散了?”
“散啦!当时只能是这种命运。”娄昌福苦笑地看着我。我再看看林友泮他们几个其貌不扬、却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农民,不由得赞叹道:“你们都非常不简单,虽然损失了自己的许多,而且今天你们中间也没有人成为富人,可你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载入史册。”
“有你作家这话我们就满足了!满足了!”能说会道的颜祜庆喜笑颜开。而不太说话的林友泮,我则看到他的那双眼里闪着眼花……这位老人让我顿时想起了曾经同样当过生产大队支书的我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同代人,我父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也是为了农民兄弟们能过上些好日子,在苏州地区成为乡镇企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而且因为办了所谓的“黑厂”而下台、受批判,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我们……想到这儿,我不由绕过桌子,双手握住林友泮老人的手,对他说:“老支书,我会在书里写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