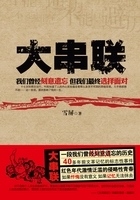卫生间里,做清洁工作的阿姨坐在盥洗台上美美地抽着烟。夏天找她借了一个打火机,和她一样坐到盥洗台上。裙子裂开的声音又出现了,夏天从盥洗台上跳下来,一把扯下那块曾经叫做裙子的布,穿着内裤重新坐回原来的地方接着抽,弄得那个阿姨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广播里,主持人一遍一遍地叫夏天赶紧到主席台去。
"外面找那个夏天干什么?"阿姨问。
"她是今天的主角。"夏天晃着两条光溜溜的大腿毫不在意地说。
"找不到了?"
"她在这里。"
夏天跳下盥洗台,嘴里叼着烟,把那块布围在腰间胡乱打了个结。那块布实在太窄了,围在腰间黑色内裤依旧若隐若现。夏天捏着烟头随意一弹,刚好弹到马桶里。
"阿姨,麻烦了!"
夏天走了出去。
外面的人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分头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夏天三寸高的高跟鞋踏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从大厅这头一直传到那头。人们逐渐安静下来,把目光聚集到她身上。夏天感受到了那些目光,但她谁都不看,走得更加婀娜万分,一条雪白的大腿在人们眼前晃动,细心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那精致的黑色蕾丝内裤是今年最流行的性感款式。主持人看见夏天,长舒一口气,也为她那种自信的迷人气质所倾倒,从台上走下几步伸手邀请她。夏天微笑着伸出一只手,由主持人牵着走上讲台,动作妖娆妩媚,优雅至极。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些艺术品的主人!"主持人慷慨激昂地讲道,并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夏天站到话筒跟前,等待掌声平息。她始终对着台下微笑,笑得那么美,自信迷人。人群足足静了两分钟,夏天才说了一句"谢谢大家",然后讲起了一大堆在场人都听不懂的法语。人们看到这颗刚刚升起的新星流下了眼泪,泣不成声。
所有人都知道夏天那天都讲了什么是她离开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人们只认为这个刚从法国回来的摄影师只不过是在卖弄自己的法文水平罢了。后来很多家报纸都登了夏天在个人摄影展上的讲话、照片。讲话的大致内容是:我一直很努力,我不停地把自己变得很强,很强很强。我以为只要我强了,我就可以赢得他(开始抽泣)......没想到我的好与坏,根本与他无关。他根本就不在意(哭泣中)......我以为今天他会到场,我希望他能为我骄傲,我告诉过他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才做的,他也答应我说他一定会到!我怕他不记得了,刚才给他打了无数次电话。手机开着,但是没有人接(泣不成声)。他不想接!我想他再也不会来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不过为夏天这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留下一点神秘色彩罢了。现场的人真正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了,是在夏天从包里掏出手机将它重重地摔在地上之后。彩色机壳四分五裂,夏天在人们的惊愕中,踩着高跟鞋离开。瘦瘦的布包裹着她的屁股,她几欲跌倒,无法加快步伐,最后索性扯了下去丢在地上。嗅觉灵敏的记者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镜头对准肌肉紧绷的臀部。一直捕捉别人的夏天终于也被别人捉进了镜头,转天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夏天穿着内裤离开的"行为艺术照",各个角度都有。
离开展览馆,夏天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回到住处拿上那部她花了3000元买零件自己组装的照相机,然后到机场买了一张最快起飞的机票,连去哪里都没考虑。她只想尽快离开,越快越好。她不够勇敢,她也不够坚强,那么请允许这个失败的懦夫带着仅有的尊严退场!
后来夏天被飞机带到了这个城市。夏天对自己发誓,她永远都不会用手机,手机是她的灾星。她也永远不会给他打电话。无论发生什么,永远!
"你还要喝多少?"银子尽量克制住怒气问Colin。
"不知道!也许一杯,也许十杯!"
Colin抱着Vodka酒瓶又灌了一口。他的声音很大,醉鬼的德行。银子拿着电视遥控器又换了一个频道。
"你们认识多久了?"Colin问。
"三年。"银子没好气地回答。
"你换来换去地找什么?没有一个频道坚持十秒!"
"看看有没有他们的消息。"
"他们?"
"不是他们,是她!你少喝点行不行?耳朵都不好使了。"银子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他可不想惹Colin这个醋坛子,"是庄美娴!"
"你们认识的时间比我还久,为什么不娶她?"
"你喝多了!"
"因为你喜欢Summer,不喜欢她,所以她才找了我,对不对?"
"你别再喝了!"
"你猜她现在会在哪里?"
Colin突然凑到银子跟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问。银子躲开了。
"我猜啊......"Colin重新倒到沙发上,"她一定在某个男人的怀里!"说完,他嘿嘿地笑起来,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笑得一发不可收拾。
银子厌恶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开始能够理解庄美娴为什么要离开他。如此脆弱的男人,实在不足以支撑庄美娴更为脆弱的神经。两株同样脆弱的植物,依偎在一起,那种照镜子的感觉让他们以为这是缘分,其实不过是加速灭绝。
"你今天好威风啊。"Collin似乎在撒酒疯,却一板一眼地学起银子在天香庄园打电话的样子,有点滑稽,有点戏谑。
我一向这么威风。银子在心里说。
"闹钟的故事是真的?"Colin轻佻地问。
银子像没听到一样。
"你好cool哦!"Colin傻呵呵地笑起来,银子的厌恶升到顶点。Colin识趣地闭了嘴,默默地喝了几口酒,问:"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醉过?从来都没有为女人醉过?"
"如果我爱一个女人,我要把她想要的都给她,不是为她喝醉!"银子恶狠狠地说。
"如果我爱一个女人,我要把我所有的都给她......只要她回来。"
银子看见了两颗泪,在Colin的脸上。
"完了?"萨卡盯着夏天微醺的脸问。那脸真的好美,迷离的美。
"怎么会?"她好像在责怪他,却更像是撒娇。
"异乡的生活并不如想象般简单,那个女孩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一时冲动带来了多大的麻烦。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她总会莫名其妙地伤感。炎热的夏季,她却觉得从心底一阵阵地发冷。她的手总是那么冷,冷得无法再次按下生命的快门。她爱上了站在阳光下,把皮肤变成了流行的所谓小麦色,那样才能让她感觉有一点点暖,感觉她还是活着的。
"其实,在法国那两年她也是这么寂寞的,但她却是快乐充实的。不是因为那里有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美丽的卢森堡公园,午后四点街边的咖啡店啤酒馆全都坐满了安逸懒惰浪漫的法国人,而是因为--她心里有着一个美好的梦,她以为两年的寂寞可以换回一世的幸福。徜徉在美丽的塞纳河边,看着就要重新开放的橘园美术馆,想着可以看到塞尚、雷诺瓦、毕加索这些印象派大师的真迹,作为招牌的莫奈作品《睡莲》......她都无数次地从心底泛起微笑,将来她一定要和她爱的男人来这里!品着美美的波尔多红葡萄酒,说着Je t'aime--我爱你......
"多愚蠢的女人啊!她可曾听过有谁对她这样许诺?她真笨!
"生活逐渐进入了穷途末路,两年的留学经历根本不能帮她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与很多人的经历其实都一样。当你有那么一点本事,当你有过那么一点成绩,当你对自己有那么一点自信,当你对未来有着那么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你不肯为了生存放弃自己的理想,当你想把自己的一切都藏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之大,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萨卡默默地点头,他同意夏天说的话。理想总是与现实背离,我们无能为力。
"后来呢?"萨卡问。
"后来?"夏天脸上又浮现了那种迷离的微笑,"后来女孩去自动提款机提取最后的一百块钱,她惊讶地发现余额显示'100'后面又多了三个零--十万块!如此大的手笔,非那个男人莫属。他有的是钱!"
萨卡屏住了呼吸,他在等待。夏天却笑了起来。先是无声的微笑,接着嘴巴咧大慢慢有了声音,最后竟狂笑起来,笑得肚子疼,笑得弯下了腰,笑得流出了眼泪。她蹲在地上,笑着前世今生道不尽的可笑之处,笑着这从头到尾就可笑的一切。
十万块钱就可以弥补那天的过失吗?她心里的伤可以用十万块钱来治愈吗?她对他的爱只值十万块钱吗?那些日子,她一直把他藏到看不见的角落,任尘土把他掩埋。她欺骗自己,她看不见他,那样她就可以再次欺骗自己,她不曾想他,她也不曾爱过他。甚至,她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他!如今十万块钱却像一把雪亮的刀子直刺她的心房,她终于笑着看见那颗滴血的心竟然还是在为他跳动!讽刺啊!
"女孩取出了100块钱,然后用特快专递把那张银行卡寄到男人的公司。那张卡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当初她向他要来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让他方便地给她汇款,她只是想保留一点和他有关的东西。可是她没想到那张卡竟会成为他侮辱她的方式!她不要他的施舍,她要他永远欠着她的!这世上凡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是便宜的,他欠她的东西永远别想用钱来弥补!
"办完特快专递,女孩的身上只剩75块钱。她对着天上的太阳笑了,阳光刺得她眼睛里再次溢满了泪水,那里面盛满了希望......"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你就是那个女孩?"
"我是夏天。"
夏天睡着了,喃喃中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你还是Summer。萨卡对自己说。你就是你。全世界最伟大的游戏将因你而生!
他把被子小心地盖在她身上。葡萄酒的香甜伴着她的呼吸吹到他脸上,他在她的眼角看到了淡淡的皱纹。那一刻,他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他不希望她老,他不想看到她老,他要让她在游戏中永生!
"嗨!"
"嗨!"
"嗨!"
......
电脑屏幕上的女人不知对呼呼"嗨"了多少次,可她还是一遍遍地"replay"。
漆黑的房间里没有开灯,呼呼听着单调的"嗨",手指在桌面上划动。
她碰到了一样东西,一盘磁带。幸好音响里竟然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功能,她把磁带放了进去,银子的声音飘了出来。
一个开始,因为一个结束
回想走过的那么多年
你还是我一碰就痛的伤疤
我想我们是爱过的吧
不然我的心不会痛到无力自拔
一个电话就可以打破那么多年的梦
我真的以为我们是爱过的啊
只是为什么
分手的话要出自别人的嘴巴
我永远都坚信我们是深爱着的人
我愿意为我们的爱情
蒙上圣洁的婚纱
感谢即使到了最后一刻
你还说着爱我的话
可是我的耳朵再也欺骗不了我的眼睛
你已经变成了和我没有关系的
那个她
伤疤,伤疤?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块伤疤?谁是谁的伤疤?
庄美娴一直昏昏沉沉,摸着她滚烫的皮肤,阿飞知道她在发烧。那只受伤的小野兔温顺地趴在地上,像怀里的庄美娴,无助得可怜。
他最终还是没有吃那只野兔,而是撕下衬衫的袖子给它包扎伤口。它的伤很重,左后腿的骨头隐约可见。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它的造化了,阿飞已经把它当成了战友。
他勇敢地跑到外面摘下几串连着叶子的葡萄,放到嘴里一枚,酸得他脸都扭曲了。可有总胜于无。回到屋里,把叶子递到野兔跟前,它嗅了嗅,终于还是吃了。托起庄美娴,尽可能地挑红一点的葡萄把皮剥了喂到她嘴里。昏迷中的庄美娴不知是什么,竟也胡乱咽了下去。他稍感安心。
他把庄美娴抱到孤零零的钢丝床上。她的丝袜有无数的破洞,她的左脚上还穿着一只鞋子,达芙妮。宁愿化作月桂树,也不愿意嫁给阿波罗的达芙妮吗?阿飞看着她,有说不出的心疼。
天忽然变了,阿飞竖起耳朵听着窗外,不祥的感觉。他把庄美娴抱起来,坐到地上,用背顶着桌子。他在等待,等待所有的厄运来临。
雨更大了。白夹竹桃拼命摇曳。闪电。雷鸣。细远的隆动。近了,更近了。阿飞闭上了眼睛。
"我的鱼缸呢?" 庄美娴醒了,无比清醒地问。
"在这里。"阿飞把鱼缸递到她手上。
"我没有把他放进去,我没有把他放进去。我们还没完,没完......"她把那个小鱼缸死死地抓在手里,脸上竟带着笑的。
阿飞不知道庄美娴的话是说给谁听的,他却轻轻地应和着:"是的,我们还没完!"他把小野兔放到庄美娴怀里,抱起了她们俩,打开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