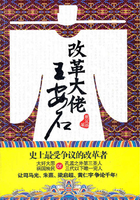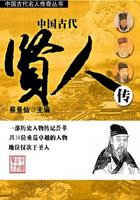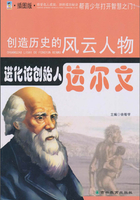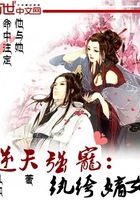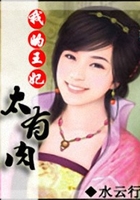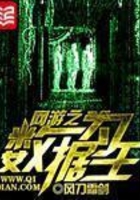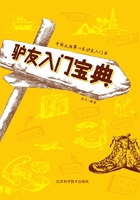"川岛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里,回忆的更详细:"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在那年的11月2日正好是星期天,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周作人、李小峰、孙伏园和我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合,决定出一个刊物,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七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同意了。就请钱玄同先生题签。次日即由伏园去报告鲁迅先生,他表示都同意。后来又由伏园去联系了几位,就写了一张石印的广告,说这个周刊将在何时出版,是由某某十六人长期撰稿,到各处张贴、发散。一个星期后,《语丝》便出世了。"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在1924年11月17日出版。它是一本十六开八页的小型刊物,每周星期一出版。八十期以后,改为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开始,它的地址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实际上并没有社址,只是借用新潮社的屋子做了《语丝》的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后来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了。
《语丝》的广告上,虽然列出了十六个长期撰稿人,实际上也只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等五六个人是真正的投稿者。而未列入十六个长期撰稿人之中的刘半农(当时正在法国留学)、俞平伯、冯文炳(废名)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语丝》于1924年11月创刊,在1927年10月24日被张作霖军阀政府查封了。发行《语丝》的北京北新书局也遭到了查禁,《语丝》后来移到上海,仍由搬到上海的北新书局出版。
《语丝》的发刊辞是周作人起草的。文章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发刊辞强调了以下几点:①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②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③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④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⑤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语丝》是一个以散文为主,兼登小说、诗歌、学术文章的刊物。虽然孙伏园提出过"语丝的文体",但他似乎并没有说明这种文体有什么特征。周作人在《答伏园"语丝的文体"》中概括了它的特点:(一)可以随便说话。(二)大胆与诚意。(三)说自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中,对周作人所说的"大胆与诚意"、"不说别人的话"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并提出:"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
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概括它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确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这些所谈语丝体特色,似乎着重在思想上、立场上和态度上,对于文字特色涉及不多。后来周作人作《〈语丝〉的回忆》才提到了它的文字风格:"《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的。"应该说,不仅是"任意而谈","庄谐杂出",而且多讽刺,多反语,文字是嬉笑怒骂。
1924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先后问世,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北大教授们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个派别,即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按照一般的人情来说,林语堂到北京大学任教,应该与胡适走得很近。这是因为:一是胡适是他来北大的引荐者,二是"吃水不忘打井人",在林语堂留学期间遇到经济困难时,是胡适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林语堂对胡适的主张也是完全赞同和支持的。不仅是胡适,林语堂与徐志摩关系也很好,林语堂最初一些文学作品就是在《新月》上发表的,林语堂也参加过新月社的一些活动,但林语堂最终没有参加《现代评论》活动,而参加了《语丝》的活动。其主要理由是由他的自由主义的人生态度所决定。在林语堂看来,《现代评论》是带有"官"办的性质,而"官话"与"自己的话"相去很远。林语堂"接近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语丝》的几个特点,正中林语堂的下怀。所以,林语堂接近《语丝》,未参加《现代评论》,充分表现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实际上,《现代评论》也是一份自由的刊物。它是1924年12月13日创刊于北京的综合性周刊。初期经理为刘叔和,始终负主要责任的是王世杰。主要撰稿人多为新月社成员,有胡适、高一涵、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李仲揆(四光)等。刊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教育、科学等各种评论文章,兼刊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发表闻一多、徐志摩、胡也频、杨振声、凌叔华、沈从文、丁西林等人的诗歌、小说、剧作、散文和文艺评论等。
在编辑方针上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在"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中,既有揭露帝国主义暴行,揭露段祺瑞军阀主义的文章和支持进步学生的言论,也有污蔑学生,为军阀开脱罪责的言论;既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真实情况的文章,也发表一些反苏、反共、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在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复古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脱离政治。由于该刊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的基本政治倾向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北大教授燕树棠、周鲠生、陈源(西滢)、杨振生、彭学沛和清华教授钱端升等也参加过编务,他们大多都在北大文科任教,又大多数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北京《大同晚报》曾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胡适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林语堂后来在《八十自叙》中说:"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之派,而属于语丝派。""我们都认为胡适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由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我们对他们有几分讽刺)对我很适宜,我们虽然并非必然是自由主义分子,但把《语丝》看做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
当然无论是社也好,派也好,都不能与今天我们说的党派和社团那样来理解,因为它们毕竟是些宽松的组织。
除了以上因素外,林语堂加入《语丝》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林语堂跟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是北大方言调查会的伙伴。他们志同道合,相互切磋,建立了一定的友谊。
四、与鲁迅的交往
鲁迅是1920年8月聘为北大国文系兼任讲师,直至1926年离开北京为止,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他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林语堂于1923年9月来到北大英文系任教。他们两人是否接触过,不得而知,但他们是北大的同事关系却是事实。林语堂与鲁迅的接触,可能是因参加《语丝》开始,并且由同事发展到战友。
林语堂加入《语丝》社后,经常参加该社同人的活动。他们由每月一次的聚会发展到每两周举行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饭庄坐落在中央公园内环坛西路上,主体建筑具有浓郁的古典色彩,庭院内假山、小桥、喷泉、瀑布相互映衬,海棠树郁郁葱葱。当海棠花盛开的时段,漫步庭院中,不时清风吹拂,点点海棠花瓣似风如雪般轻轻飞扬着。来今雨轩始建于1915年,最早由当时中央公园董事会发起成立,轩名为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所定。原址在中央公园内坛墙东南角外,里筒瓦歇山卷棚屋面,南向,建筑面积481平方米,厅前平台周围砌矮花墙,中间独置太湖石一座。厅后西侧堆叠山石,为广东刘姓老人堆砌。建成后本拟做俱乐部,后改为餐馆,由赵升永租来开设了华星餐馆和茶座。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也留下了许多轶事。如著名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就喜欢来今雨轩,不管是春柳含烟、蝶舞莺唱,还是冬雪堆玉、老梅燃情,也不管是秋菊噙香、黄叶流金,还是夏荷出水、翠竹临风,这里都给人一种惆然脱俗的美。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便诞生在这里。
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17年至1929年,鲁迅先后曾27次到来今雨轩就餐、饮茗、交谈、阅报、翻译小说,他翻译的小说《小约翰》便是在这里完成的。
语丝社虽在东安市场开成北楼拟定,但后来的聚会大多是在来今雨轩。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谈到了语丝社活动的情形:"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的茂密的松树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儿一样,声音迂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词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没有人会猜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而能针针见血的。他极受读者欢迎。在语丝派的集会上,我不记得见过他那位许小姐,后来他和那位许小姐结了婚。周氏兄弟之间,人人都知道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兄弟之间误会很深。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从来没打听过。
但是兄弟二人都很通达人情世故,都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巧妙地运用一字之微,就可以陷人于绝境,置人于死地......他们还有一位弟弟周建人,是个植物学家,在商务印书馆默默从事自己本行的学术工作。"林语堂的这段回忆中,有两处是不属实的,可能是林语堂写此自叙时年龄已高(八十岁),记忆有误是难免的:一是语丝社的聚会不是"每两周一次"。据川岛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说说〈语丝〉》一文中说:"《语丝》既没有稿酬,于是先是印了'语丝稿纸'送给写稿的人,后来是请吃饭。大抵在《语丝》出版到十多期之后,每月月底就必有一次聚会,每次一桌两桌不等。这就在一些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从此,《语丝》也就开始有'社'了,但也只在这样的小木牌上有时写写而已。
"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也谈到了聚会的情况:"《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二是鲁迅从未参加"语丝社"的聚会。鲁迅于1923年7月14日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7月19日,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1923年底才购买了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房宅。1924年6月11日,鲁迅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11月17日,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