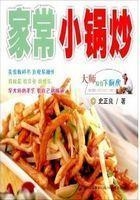非 马
虽然从小就喜欢上诗,1961年我从台湾到美国留学之前,还没真正写过一首诗。在美国的头几年因忙于学业,根本无暇顾及诗。直到取得学位开始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以后,才同台湾诗人白萩取得了联系,在他主编的《笠诗刊》上开辟了一个翻译专栏,大篇幅介绍当代英美诗,开始同台湾的诗坛建立起持久的关系来。
由于白萩希望我能利用地利,尽量多译介一些刚出版上市的带有泥巴味汗酸味人间味的诗集,我因此有了接触了解美国当代诗的机会。从艾略特(T.S. Eliot)到吟唱诗人马克温(Rod McKuen),从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到垮掉的一代疲脱诗人(Beat Poets)佛灵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从意象诗到墙头诗,我一本本地买一本本地读一本本地译,后来又扩大到加拿大丶拉丁美洲以及英国诗人的作品,还有英译的法国丶土耳其丶希腊丶波兰和俄国等地的诗。几年的功夫共译介了将近一千首诗,相信这些译诗对台湾诗坛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但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
在这些诗人当中,马克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1966年出版的《史丹阳街及别的哀愁》及次年的《听听那温暖》使他成了广受欢迎的诗人丶作曲家及演唱家。这两本诗集的销数超过了佛洛斯特和艾略特所有诗集销数的总和。他诗中的抒情丶不装腔作势的自然语调与淡淡的哀愁,同离乡不久的我的心境相当吻合,我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把《史丹阳街及别的哀愁》里大部分的诗译成汉语,在《笠诗刊》上一次发表。我在译后记里说:"一个诗人的对象应该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诗人不再是先知或预言者,高高在上。他只是一个有人间臭味,是你又是我的平常人。罗德?马克温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寂寞与迷失代表了这时代大多数人,特别是年青人的寂寞与迷失。正如一个女孩子所说的:'我们能在他的诗里找到自己,他感觉到我们所感觉的。'" 奇怪的是,美国主流诗坛并不接纳他,我接触到的美国诗人似乎也不把他当成诗人。
一边翻译一边吸收,渐渐地我自己也开始写起诗来。最初的几首诗在《笠诗刊》上发表后,听说还引起了一些诗人与读者的好奇,纷纷打听非马是谁,什么地方突然蹦出这么一个诗风新异的诗人来。
可能因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汉译英比英译汉的工作要辛苦得多。更使我惊异的是,一些在汉语里象模象样甚至外表华丽的诗,一经翻译成英语,却破绽百出,有如翻译是一面照妖镜,把躲藏在诗里的毛病都显露无遗。这当然有可能是由於两种不同的文化与语言的差异所造成的,但也可能是原诗缺乏一种普世的价值与广义的人性,用不同的文字翻译后很难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感动。
那时候聂华玲同安格尔(Paul Engle)还在艾荷华大学主持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都邀请两岸的作家前来参加。为了便于申请,白萩希望我能英译他的一本诗集。那是我头一次尝试着把汉语诗翻译成英语,实在没什么把握,所以在初译以后,便请一位对文学有兴趣的美国同事一起斟酌讨论修改,之后也试着把书稿寄给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回答是:喜欢这些诗作,只是美国市场对台湾诗人没太大兴趣,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诗人则另当别论。多次碰壁之后,我把书稿寄给当时担任《六十年代》诗刊的主编诗人罗伯特 ·布莱(Robert Bly),请他推介一个出版社。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在一张明信片上,布莱说:"我无法分辨这些诗的好坏,因为你使用的有些词汇,我们已经有几十年不用了!建议你找个美国诗人帮忙修改。"后来才发现我那位美国同事对当代的东西不感兴趣,甚至存有偏见与反感,他的阅读范围只限於古典文学,难怪他的词汇同当代接不上轨。
在不是故国的地方写诗,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文化的差异之外,便是:用什么语言写?为谁写?写什么?这些问题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当时雄心勃勃的我,确有用英语写诗,进军美国诗坛的念头,但很快便体悟到,如果思维仍习用母语,那么最自然最有效的诗歌语言应该是自己的母语。用第二语言的英语写诗,无异隔靴搔痒。语言确定以后,自然而然地,华语读者成了我写作的对象。当时美国的汉语报刊不多,刊载现代诗的副刊更少,而大陆的门户还没开放,因此台湾的读者成了我的主要对象,旁及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区。对这些读者来说,美国的题材虽然也许可能产生一点异国情调或新奇感,但不可避免地会有隔阂;写台湾的题材吧,对住在美国的我来说又缺乏现场感。在这种情况下,写世界性的题材成了较好的选择,深层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一向厌恶狭窄的地域观念,普遍的人性与真理对写诗的我更具有吸引力。相信这是有些评者认为我是当代台湾诗人中,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原因吧。
由於用汉语写作,我同美国诗坛几乎没什么接触与交往,但为了好玩,我还是试着把自己的一些诗译成英语,有几首还被选入了一些书名颇能满足虚荣心的选集如《杰出的当代诗》《诗神的旋律--最佳当代诗》等,后来才知道这些可能就是所谓的"虚荣出版物"(Vanity Publications)的玩意儿。无论如何,当时确给天真的我不少鼓舞,特别是有一本选集还用我的名字去打广告。
真正认真把自己的诗翻译成英语,是1993年参加伊利诺州诗人协会以后的事。伊利诺州诗人协会是成立于1959年的"国家州际诗人协会联盟"属下的组织。协会每两个月聚会一次,主要是批评讨论会员所提出的作品,并组织各种活动如到养老院及医院等场所去朗诵、举办成人及学生诗赛等。我发现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些文字上甚或文化上的异同,往往会自动浮现彰显出来,使我对原作(不管是英语或汉语)能采取一种较客观的批评眼光,进行修改。这种存在于两种文字或文化之间的对话,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奇妙有趣的经验。我常劝年轻的写诗朋友们,最好能通晓至少一种外语。了解一个外国作家,或对他表示尊敬,没有比翻译他的作品更好的途径了。
入会不久我便被推选为伊利诺州诗人协会的会长,任期两年。1995年我把自己的英译诗作整理成《秋窗》诗选出版。也许受《芝加哥论坛报》上一篇图文并茂两大版的访问报道的影响,反应相当热烈。一位诗评家甚至把我列为包括桑德堡(Carl Sandburg)及马斯特(Edgar Lee Masters)等名家在内的芝加哥历史上值得收藏的诗人之一。 当然这对只出版过一本英语诗集的我来说未免太高抬了。不久我加入了成立於1937年的芝加哥诗人俱乐部,成为唯一的非白人成员。
在这些活动中,我所接触到的美国诗人都比较保守,特别是在诗的形式运用上。这大概同美国中部的保守风气有关。他们有许多还在热心地写莎士比亚的商籁体或其它押韵的固定形式。有些人是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字技巧训练,也有的纯粹是在怀古。由于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没有太大的传统包袱,我可以比较轻松自由地写我的自由诗。他们都觉得我带给了他们可贵的新鲜空气。前任伊州桂冠女诗人布鲁克斯便曾说过,我的诗里有一种奇特的声音,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特别高兴能从我的诗里体验到中国古典诗的精炼与韵味。当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尤其是对英语这第二语言的体会与感觉。
有趣的是, 1996年在中山与佛山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诗人笔会上我见到了几位心仪已久的诗人。其中绿原先生除诗创作外,还是翻译德国诗的名家。他把仅剩的一本厚厚的《里尔克诗选》送给了我,我则送他我的英语诗集《秋窗》。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我的诗集读完了,说很喜欢。他说虽然知道我这些诗大多先有汉语,但他还是要把其中的一些诗翻成汉语。一方面这是个很好的体验,另一方面他也想从中探究为什么他在当代中国诗人的诗集里看不到中国古典诗的优良传统,却在我的英语诗集中找到。
随着网络的兴起与普及,我自己也制作了一个个人网站《非马艺术世界》,展出汉英两语诗选、评论、翻译、每月一诗以及散文,还有我近年来创作的绘画与雕塑等,同时也在网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网上刊物及论坛上张贴作品,有几首英语诗还被选为"当天的诗"或"当周的诗",交流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甚至有来自以色列的诗人要求授权翻译我的几首诗;日本著名诗人木岛始也从网络上同我取得了联系,用我的诗为引子,做汉、英、日三种语言的"四行连诗",在日本结集出版;一些美国诗人团体及诗刊也来信邀请我担任诗赛的评审或诗评小组委员等等。这些都是网络带来的方便与可能。几年前,伊拉克战争引起了美国诗人们的反战运动,在网络上设立网站,让诗人张贴反战诗,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诗人的响应与支持,我曾义务担任了一段时期的汉语编辑,我自己的一首关于越战纪念碑的诗也被选入《诗人反战诗选》,另一首关于战争的诗则被一个反战纪录片所引用。
除了陆续将我的汉语作品翻译成英语外,最近几年我也尝试着从事双语写作。无论是由汉语或英语写成的初稿,我都立即将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发现反复翻译的过程对修改工作很有帮助。当我对两种语言的版本都感到满意了,这首作品才算完成。在这里必须提一下,我的双语诗同一般的直接互译略有不同。由于是自己的诗,我拥有较多的自由,从事再创作。
两岸的评论家常不知该如何为我定位:台湾诗人?中国诗人?美国诗人?上面提到的那位以色列诗人也曾问过我究竟把自己当成中国诗人或美国诗人。我想为一位作家定位,最简便的办法是看他所使用的语言。前面说过,我认为诗的语言最好是诗人的母语。但如果把母语狭义地定义为"母亲说的话"或"生母"语,那么我也像大多数从小在方言中长大、无法"我手写我口"的华人一样,可说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人。而从十多岁在台湾学起,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国语或普通话,虽然还算亲切,最多只能算是"奶母"语。等而下之,被台湾一位教授戏称为"屁股后面吃饭"的英语,思维结构与文化背景大异其趣,又是在成年定型后才开始认真学习,则只能勉强算是"养母"语或"后母"语了。但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运用,"奶母"语及"养母"语或"后母"语都有渐渐同"生母"语融合的迹象。说不定有一天我能提笔写作,而无需考虑到选用何种语言。
根据我这些年来译诗与写诗的经验,我发现许多优秀的现代诗,几乎都是演出的诗。诗人提供的只是一座舞台,一个场景,让读者的想象随着诗中的人物及事件去发展,去飞翔。诗同小说或散文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它的多义性。一首耐人寻味的诗,往往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如果一首诗只有一个浅显固定的意义,那么在我们读过一两次之后,便显得乏味,很难引起我们再去读它的兴趣了。因此一首成功的诗同一幅隽永的水墨画一样,需有足够的留白,让不同的读者,或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心境下,产生不同的反应与感受。根据各自的背景与经验,读者可把自己的想象与解释加诸于一首诗,从而共享创作的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首诗必须有读者的参与及合作,才得以完成。我常引用美国诗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一首叫做〈场景〉的诗为例:
玫瑰花,在雨中
别剪它们,我祈求。
它们撑不了多久,她说
可是它们在那里
很美。
哦,我们也都美过,她说,
剪下了它们,还把它们交到
我手上。
这首诗给了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比如说,诗中讲话者同那位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他们是夫妇,是否年华老去的妻子因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容不下美丽的东西?或者她是在对喜欢拈花惹草的丈夫做出警告?如果他们是一对情人,那么她是否因为他眼中只有玫瑰花,把她冷落在一旁而气得要把玫瑰花剪掉?或者她只是想在玫瑰花凋谢之前,在记忆中留下它们美好的形象?还有,讲话者为什么要为玫瑰花求情?只是单纯地为了美?或另有隐衷?总之,短短的一首诗,却有许多的可能性。它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舞台与场景。如何去诠释,是读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