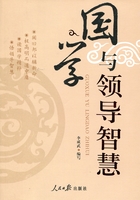遗产的构成必然包括了解释的成分。构造主义者干脆认为遗产不是其他,就是解释;不过,它不是一般性的解释理论,而是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论。比如游客之所以去造访遗产地,其目的之一是去学习和体验。在参观、游历过程中,每一个游客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对遗产进行解释。遗址为到访者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目的地,并使到访者获得身体力行的知识认同、经验认可。这一过程出现了很有意思的解释现象,即同一个遗产物对每一个到访者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在不同的到访者那里所获得的认知和解释则会出现极大的差异。根本原因是到访者加入了各自的认识、解释和互动。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或在推论的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话,便不存在具有相同指喻性的"遗产言说"。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承认有一个具体的遗产物、遗留物的客观存在,但这个"客观存在"只不过是假定排除了任何人为因素的"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说,它的存在并无意义--对人没有意义的东西不可能被"指认"为遗产。反过来,只要是遗产也就必定包含了人的因素:认知、解释、记忆、选择、认同、主观、策略、制造,等等。据此,遗产的构成中必然包括可触及的和不可触及的部分,它们相互作用,组成完整的遗产共同体。
众所周知,对遗产的界定、认识和解释或多或少地会带上时代、政治、权力化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遗产属于"创造的遗产"(creating the heritage)。其中附丽了大量的"次生因素"。具体说来,由于当代大规模遗产运动的作用,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公共价值的"品牌",累叠了许多与遗产"原生因素"不相干、甚至不相容的东西。造成这种情状的始作俑者即是"权力话语"。由于当代社会对遗产的界定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利益性和实践性质,因此,遗产也经常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及国家之间斡旋、协商的平衡物。全球化对遗产工程重视的热潮加速了遗产存续的变化速度,改变了它的行进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大规模的旅游活动成为这一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同时也强化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性。行政管理往往把遗产变成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分配、管理和利用。在此,我们更想强调对遗产主体性的真正尊重,对遗产原生形态的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如果这一前提没有把握好,遗产的命运和后果便令人堪忧,遗产也会改变其原有的性质和特征。
既然遗产属于特殊的存留物,便有各自的存续样态;这决定了其相应的地方和空间背景。《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方面的规定包括:Ⅰ.相同的历史文化组成;Ⅱ.在地理区域特征内的相同类型的遗产;Ⅲ.相同地质形态构成,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并说明其作为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系列遗产不能将其分割开。每一个独特的遗产都具有环境的特质、自然优势以及生态构造。从本质上看,任何物种都是生态性的。生物乃至"文化物种"的多样性离不开其生成、生存、演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所谓"可持续发展"首先也是针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背景和基础的。
按照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要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平衡与适应。它有两个基本特征:对生态环境的保持、保障与保护以及在和谐基础上的创造行为是生态发生学的原旨。所以,严格意义上的"遗产"都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环境的生态性遗物、遗存和遗留。从逻辑上说,任何值得保护的遗产也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与此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世界遗产是一种脆弱的、不可修复(不可再生)的资源,必须受到保护,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并留给后人享用。"人们今天之所以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世界遗产,说明人类的先祖深谙个中道理;也揭示了原始生态的朴素哲理,即如果生存环境受到破坏,人们便无以依靠,遗产便丧失了存在的环境和物质条件。
不言而喻,全球范围内有关遗产的主导价值观念来自于联合国;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遗产政治中隐含了某些殖民化因子。具体而言,全球背景下所推行的"遗产政治"仍然带有"欧洲中心"和"工业历史"的强烈隐喻。只要我们对西方现代史作一个大致的梳理,便不难看出这种判断的历史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一直鼓励对自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所起的主导价值的作用进行总结。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保护"物质遗产"也就成为了一种张扬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成就和物质成果的行动。简言之,鼓励对物质遗产进行历史研究和总结与所谓的工业,或原初性工业文明 (proto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主题有关。在这股潮流的作用下,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主要国家便出现了对遗物历史的兴趣与热情。
许多机构相继成立:英国始于1960年,瑞典始于60年代末,美国真正开始应在1974年,加拿大的魁北克始自于1976年,而法国最早在这方面出现的暧昧态度始于1973年......这一段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人类遗产"的"重组"(reunited)与"西方中心"的政治叙事须臾不可分离。这一"政治叙事"后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大的"官方话语"表现出来。我们不能漠视这一段历史的发生与发展。一方面,我们不能轻视西方发达国家对人类"物质遗产",包括工业技术主义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先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这一短暂的历史之于当下进行"遗产政治"价值引导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这对我们理解"突如其来的遗产运动"颇有助益,也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分清"自己的遗产"的自主价值,避免使之沦为"他者的陪衬"。值得提醒的还有,当遗产成为现代旅游的一个资源性品牌和品名的时候,要格外警惕遗产演变成某种"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副产品。有的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遗产"(postmodernist heritage),并认为其已构成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景观。在这样的背景和"产业化的生产模式"的推动下,一方面,"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商业,这使得在过去曾经出现过、发生过(对遗产的破坏性事件和行为)的社会风气有可能回潮";另一方面,它也在同步地进行着人们对社会认知体系的改造和重建工作。
综上所述,遗产是一笔财产,具有资本性质;遗产是一种表述,具有主观和解释的成分;遗产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经常成为"被劫持"的符号;遗产与技术主义和社会再生产密切关联,并成为"制造"的一个舞台。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和"保护"遗产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妥善解决这一对矛盾不仅考验我们的智慧,也考察我们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