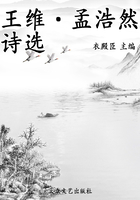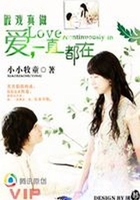引言
当时代迈进1978年,"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在此开始交接,历史语境的重大变化促使文学冲破狭窄的甬道,开始仪态万千地展示其多元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短暂、小范围的批评,浩然面对新时期转折性的时代语境,经过迷惘、痛苦的思考,惜时如金的他很快再次调整自我,重新迈入新的创作生活。然而,从意识形态经典化地位开始蜕变的浩然,在新时期的创作不再一路轻快,以往根深蒂固的文学理念在"去政治化"的时代剧变中,时常与新变革发生冲撞。浩然在开放重生的姿态中难免有些纠结,于是他的创作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如何认识浩然新时期的文学,考察作家创作的延续与变化,即"变"与"不变",开启浩然新时期农村小说的文本意义,并探求作家"写农民、为农民"这一不变宗旨的当下意义,是本章的重点。
第一节 浩然的"去经典化"与新时期的转折
在浩然失去昔日光芒、"去经典化"的过程里,中国文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新时期文学的哪些变化促使浩然走出禁锢与封闭?在一个重新呼唤"人"的文学寻觅期,以意识形态全面覆盖文学的创作必然走向"去经典化"。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代表着新时期文学变革和文艺政策重组的主流意识推进,邓小平代表"拨乱反正"后的党中央作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以下简称《祝辞》)。《祝辞》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文艺的发展成就,肯定了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和成就,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文艺状况给予了肯定,并且明确地阐述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求得解决,要求各级党的领导部门对此不要横加干涉。事实上,《祝辞》以政治领导人讲话的方式正式将"文化大革命"后文艺政策的调整方向、原则等问题明确阐述出来,从主流意识形态重新调整当下的文学语境,确定文学自由的方针。在政治不断松绑的氛围中,文学从各路突围旧意识形态创作理念,势必抛弃十七年政治话语下的种种经典成规。
一、政治意识形态的祛魅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转化期,新旧文学理念的转变并不是抽刀断水。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断逃离、重返的历史过程。社会体制的骤变,也不能阻截思维观念的延续性,在短短十几年间,文学内部其实是缓慢渐变的过程,不管新时期文学出现何种裂变、变异、重组,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步淡化。
从文学史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命名开始,80年代的文学开始走上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怀着巨大的热情批评"文化大革命",对极"左"路线进行反叛。1977-1984年,文学主要承担转型期人们的沉痛反思,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早期政治话语。1977年和1978年分别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接下来,郑义的《枫》、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方之的《内奸》、高晓声的《李大顺造屋》、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短篇、中长篇小说问世,虽然文本延续着政治干预生活的模式,但也体现了反思过往、努力挣脱政治束缚的挣扎。80年代最初几年,文学创作不可能在短时期里告别自己的历史记忆。
1985年,后来被称之为"方法年"的这一年,才决绝地标志着感时忧国的现实主义退潮,迎来文学回到自身的一幕,揭开了当代文学截然不同的一页。随着反思潮流退去,文学如何表达本身的形式主义大潮登陆。寻根文学之后,作家们开始考虑中国文学如何和世界文学接轨,从文化寻根开始透视中国的文化。国外的理论资源重新成为刷新本土文学创作的引介资源。在西方文艺理论启发下,80年代的文学走向形式化探索,文学逐渐成为"先锋"作家笔下的想象,此阶段文学的想象性本质几乎覆盖文学政治话语功能。正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渐行渐远地把文学推向远离政治话语的地方。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后,文学消费意识无以复加地占据了文学市场,政治话语只是久远历史硝烟中的记忆,历史在此完全被政治祛魅。
当我们再具体走进乡村小说这一支独特的文学创作流变中考察,就更能深入体会新时期的变革与浩然"去经典化"的必然性。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从鲁迅提出乡土文学概念到30年代"左"翼作家笔下觉醒的革命乡土社会,或是京派作家笔下幽静的田园乡土,这些小说大都有着描写乡村生活风貌、展示乡村人观念、体现乡土感情的特征。30年代,乡土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不过值得区分的是,"左"翼革命作家理解的乡土已经不同于鲁迅提出的乡土范畴,他们是按照革命思想理解当时的乡村,其目的是为了表现所谓农民觉醒与革命,并未深入刻画农民的感受和乡土特征,"乡土"在他们笔下失去了原有的意味。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里,政治语境中描写亿万农民欢天喜地闹革命的"农村小说"置换了原来意义的"乡土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40年代,乡土小说观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作者群的变化,农村小说的作者已不是当年鲁迅提及的被故乡放逐,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以怀乡之笔直抒胸臆的人了,而是一群生于土地、一直植根于农村,实实在在反映农村新变化、农民新生活的作者,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等。由此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土地在农村小说里是农民生活的实际依靠,不是文人怀乡的意象。农村小说主要围绕几千年土地制度的变革,歌颂共产党,反映此时的农民思想,更重要的是其间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述取代了乡土文学中的文人情怀。
同是描写土地和依赖土地而生活的人们的文学,农村小说和乡土小说从内涵到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在描述从十七年文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乡土文学"被阶级意识置换,隐退不显,直至八十年代"寻根文学"重新开启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可见,"乡土"和"农村"虽有着共同的描写对象,却意指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实际上,"乡土"和"农村"是两个包含不同价值观念的概念,新时期文学重新开启乡土文学的意义,就在于祛除了农村小说内涵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在这样的时代历史语境下,可想而知浩然从十七年主流文学走到新时期祛魅年代的"去经典化"之必然命运。
二、人道主义、人性的回归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80年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的重新发现。新时期批评家何西来在1980年指出:"人的重新发现,是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野中和艺术家创作中消逝以后,又开始重新被提及,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课题。"随之掀起的人道主义探讨和作家人性归复的普遍创作,不断推动新时期走向探索文学本质的历程。
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有关"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从1979年到1980年,全国二十多家报刊共发表关于'人道主义讨论'的文章八十余篇,截止到1983年4月,相关文章超过了六百多篇。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在范围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五六十年代。"1979年,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感》一文中重提50年代曾被批评的敏感话题,王若水、汝信等人的观点也都触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接下来引发的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更是触碰到主流话语的底线。在一系列论争后,周扬对这次论争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种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虽然此报告在1984年第2期《红旗》上遭到胡乔木的批评,但是从中可窥见主流意识形态内部对此问题的松动与不可阻挡的时代冲击。可以说,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主轴展开的,文学实际创作对人性的探索,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人道主义大讨论之后,文学创作转向高标自我、张扬个性,把眼光投向人的价值和尊严。觉醒的个人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曲》等,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青年的觉醒形象,他们的共同点是恐惧于自我淹没在没有特征的群体里,他们开始思索个人独特价值,渴望无拘无束,勇于挣脱所谓的集体观念,面对经典和权威,他们以怪异不羁的行为对群体进行反抗。
这类人物形象截然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人物形象,如果说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同样是热情敢为的青年,他们的个人热忱与集体要求则是合二为一的,个人在集体组织名义下属于无名状态,甚至那个年代人物的性格都是特定的。新时期人的回归,必然让我们反思十七年时期文学对人的湮没。1980年,戴厚英发表《人啊,人》,以血泪控诉唤起人们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压抑已久的人们在这个时期尤其渴望恢复真实的人性,给人以基本的情感自由。张抗抗的《夏》把青年人的个人情感需求推到现实面前,越过集体主义,还以个人的正常生活。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都可以看到人性的需求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破冰而出。在这样的创作整体氛围下,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支撑的经典势必遭到祛魅,浩然创作的"去经典化"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大潮下的观念变革
1978年,这是让每个中国人翻开新生活的转折点。国家新的经济体制很快给人民日常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出现在农村的经济变革是70年代末期的土地承包。土地承包和城市的改革开放很快转变了中国人的思维观念。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的思维观念开始与旧传统理念发生矛盾。新时期的文学及时反映出人们生活中的观念冲突。思想的松动,各种价值观念的混杂,难以再出现十七年文学时期一统化的局面。随着作家们反映生活的不同角度带来的创作纷呈,浩然在一个思想相对统一年代创作的小说,自然走向"去经典化"之势。
以浩然创作所属的农村题材小说在新时期的演变为例,新时期的乡村叙述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变化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针对"文化大革命"带给农村的伤害,对历史进行了反思,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何士光的《乡场上》、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大胆揭示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年代政治运动中农民的曲折经历,沉痛反思中国农民灾难的根源。第二阶段是1985年到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加速,现代化的步伐愈发推进了农村改革。《平凡的世界》、《古船》、《浮躁》等一些长篇小说反映了在农村变革大潮中,农村"新人"孙少安兄弟、金狗等勇闯天下,在新时期为个人奋斗的故事。
大部分此时的乡村小说都对农村变革有更深入的反映。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中期至今,消费和网络传媒推动中国文学走向零散状态,文坛时之久矣的各自为政,使现实主义呼喊再次兴起。在"现实主义冲击波"潮流下,出现了《分享艰难》、《年前年后》、《败节草》等反映农民艰难生活现状的小说。经济时代的变化使如今的乡村很难再比拟曾经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村。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和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化制度,几十年的集体化生产方式并没带给广大农民富裕的生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经济体制变革带来的转折,为新时期作家提供了多元思维视角,面对复杂演变中的乡村世界,一辈子写农村、农民的浩然自然不得不"与时俱进",改变以往的文学风格和创作路数。时代的步伐推动着他在新时期"辞旧迎新",反思过去,重获新生。
新时期政治话语的祛魅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车轮,在浩然失去昔日光芒四射的文学地位的年代里,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去经典化"成为必然之势。"文化大革命"后,经过短暂的、小范围的批评,浩然由最初的抵触渐渐转变旧有观念,开始敞开心怀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开始他在这个时代的新生。
第二节 心灵的纠结与重生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