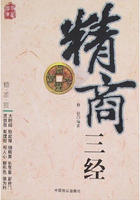尹府西花厅内,精心栽植的几株天丽已经纳粹吐香。
女子伏案捯饬,突然抬起头轻声叹了一口气:“二爷,西郊的廖红花,已经开了呢。”
寂静满院。
云羿回过身,那人蜷在微微摇晃的躺椅里,神色恬淡地睡着了。她似有一瞬间的怔忡,屋子里静悄悄的,仿佛依稀能够听见时光缓缓流淌的声音……
——划开了寂寞。
她悄悄走到了近前,轻手轻脚地为他覆上小软被,喃喃道:“二爷还是要仔细着身体。”
他好似听见了,翻了个身,呓道:“以后这些事,还是让云羿来做吧。佳兰,佳兰,你歇着吧……”
她蓦然呆住!悲伤爬满眉头,眼里的湿润满满地酝酿了起来,漫过荒草一样疯长的杂乱心事。……数月前,也是在这西花厅吧,她知道,这天要有大事发生了。佳兰整日都不见踪影。
——她照旧捯饬着花花草草,却总是心不在焉,偶尔抬头看看窗外云卷云舒,回过神来竟发现手心里沁满了汗。尹楚惜倒是难得的清闲,一大早便跑了过来,此时却在一旁闷闷地抽着旱烟。
西花厅里采光极好,她今日却意外地掌了灯,尹楚惜没问因由,只是盯着微暗的灯光发了好一会儿的愣。
其实她只是……怕那个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若是平时,云羿自然是不担心佳兰,佳兰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有几分货,她比谁都清楚。况且佳兰处事又是相当稳妥的,平素里料理联合会的任务又攒足了经验。从来没有让她费过心。
只是,这次情况特殊,佳兰面对的那个人……是她的情之所归啊。她断然不会忘记,当初道行深厚的姐姐便是栽在了一个“情”字上。
现在想来,依然心有余悸。
线人回报的时候,她紧张地差点把修花剪子砸在了脚板面上。她几是一路跑过去的,那么急于想知道,尹楚惜让查的事情,到底有无眉目。
线人附上她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
尹楚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他心里,无疑也是紧张的。线人也是云羿调教的,他从来不过问。
他料定事情必有蹊跷!云羿煞白着脸,半天没有说一句话。
然后,那个受过严格训练从来临危不乱的女子竟跌跌撞撞地扑到他面前,几近崩溃地嘶吼:“二爷!收回任务!告诉佳兰……任务取消!!取消!!!”
因为。
失踪的情报员“大炮”,就是张承宪,即余均。
那日接头,“大炮”本来已经暗暗与佳兰对上了暗号,却不料……他发现,原来一路都有人跟踪他。大洋商会的人,是后来才来的。有烟雾弹,也有不明就里想一探究竟的人。
他是半路插进商会的,里头的人自然都不是亲信。他身份受疑,如若再露出半点蛛丝马迹,整条情报链必将被一网打尽,事关重大,也许此后将会改变整个上海滩的抗日形势!
他不能错,一步都不能。所以,只能让佳兰错。
那样特殊的身份,让他和佳兰,相见不能相认。那狠心放出的一枪,皮开肉绽的是她,心碎如泥的却是他。
他打入敌人内部,佯充汉奸,忍受万人辱骂,背负着家国天下的重任,为的只是希望有一天,自己绵薄的力量能够给抗日组织提供莫大的帮助,那么,他虽死无憾。
最后一次见佳兰,他知道有人跟踪,却不知道佳兰要杀他。他假作轻佻,大庭广众之下撕裂佳兰的衣裳,费尽思量,只是希望能够在保全佳兰的前提下,把情报安全地传出去——“大炮”搜集的所有重要情报,都藏在他随手扔给佳兰的那件西服的夹层里。
他说,给尹楚惜带句话,他要找的人,一直就在眼前。
“大炮”就在眼前,因为,他就是“大炮”。
不愿明说,不愿让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空费思量,那么,就让尹楚惜去猜吧。就让佳兰,永远蒙在鼓里。错手杀他,她必是悔尽一生,也不肯放过自己。
他说,佳兰,我没有骗你,余均真的已经死了。
余均当然已经死了。要不然,他只能是张承宪。
那个时候,他战地受伤,在野战医院复原的时候,碰到了东北撤离的情报组织的上层,他被说动,从此便干起了情报工作。为了彻底保密,必须重新创造个身份,“张承宪”就只能死去,所以,经原系部队批准,向家乡张家岭发了阵亡通知书。
谁料佳兰那样烈性,竟然生死不离。
若有来生,糟糠敝衣,必此生不负。
青峰石旁,那丛廖红花红的像是渗了人血。
晨光微启时,总有个相貌标致的姑娘一路踩着露水走了来,痴痴地看着那一丛鲜艳欲滴的廖红花,像是被远去的旧日时光攫住了心神。
附近居住的村民看得多了,有时便会好心地喊:“姑娘哟!这边的那块石头上,原先是撞死过人的,你离着远些罢!不吉利哟!”
村民愈走愈进,嘴里还在不停地絮絮叨叨:“听说是个很标致的小姑娘,唉,看对眼的小伙子去打鬼子喽!死啦!都死啦!”
那姑娘不理人,村民好奇地凑过去看,却见她目光呆滞,口里还流着哈喇子,正呵呵地对着村民傻笑。好心的村民像是明白了什么,低声说了句“原来是个傻姑娘”,便转身消失在早晨清凉清凉的雾里。
姑娘笑着笑着,突然流下了两行灼热的泪。
清明的天空,有鸟飞过。扑棱着翅膀簌簌地掠过花丛,远处林子里此起彼伏的叽喳鸟鸣打破了早晨清寂的天幕。原来,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