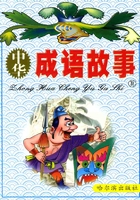仿佛,头顶上那男子的怒意,才是让她开心的调剂品;抬手揪住他半敞的衣领:“想死?亦南辰,我怎么会想死?我还要好好活着,我要睁大眼睛看你这个毫无人性的畜生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亦南辰愣住,这女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没想到,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跟他叫板?
只是,这样有脾气的她让他除了生气,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心底轻轻地流动。
来不及分辩那说不清的东西是什么,又听身下的女子咯咯笑了几声,然后用他从未听过的轻佻语调说:“亦南辰,我知道我欠了你,欠你的,我会还,但,请不要为难那些不相干的人,等我们两不相欠的时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不相干的人?谁是不相干的人?程飞黎么?她到现在还在为程飞黎着想,到现在还在护着程飞黎;那他呢?
谁来安慰他的痛苦?谁来护着他?那个唯一会惜心护着他的人因为她而半死不活地躺在那张床上,他心里的伤又有谁能看得见?
还说什么两不相欠?门儿都没有,他永远不会让她两不相欠;不会放过么?
亦南辰恶狠狠地想,那是他要说的话。
深幽的眸中燃起惊涛骇浪般的火焰,身体略动,宁错错已经被他呈抛物线姿态凭空扔到前方的大床上,不待她起身,亦南辰整个身体的重量便压了过去。
他动作迅速地伸手拉出颈上的领带缠住她的双手,绑在床柱上。
宁错错刚刚恢复一点儿力气,挣扎着就想起身,心下惊恐未过,亦南辰抓住她的纤细脚踝,不知从哪里摸来两根领带把她的脚一并绑在了床尾的床柱上。
直到那个阴森森的眼神,手里捏着一把明晃的小刀出现在她的眼前,平静的眸底,终于开始出现了恐惧,宁错错晃着头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手中的利器,想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但是,以他的变态程度,就算把她分尸,亦是可能。
奈何四肢被缚,她只能不停地扭动着身躯试图减缓他的逼近。
“亦南辰,你这个变态的男人到底要干什么?”
“变态,骂得好啊,那如果我不做一点儿变态的事情,是否,太对不起你的称呼了,宁错错,你永远都不要妄想两不相欠,对了,楼下那只白毛狗是程飞黎送你的么?嗯,我最近听说一种狗肉的新吃法,咱明儿个也试试怎么样?你说,如果和人肉一起,是煎?是炸?或是炖了吃的味道更好?。”
在此时的宁错错眼里,他可怖的面容完全像是地狱魔鬼一样的狰狞,让人惧至心底,心惊胆颤。
她不停地摇着头,不!
不要!蛋蛋不能死,她也不要死,就算要死,也让她选一个死法,她不想被划得面目全非,六亲不识。
亦南辰一步步向着大床靠近,冷意刺骨的小刀在她的瞳仁上逐渐放大,堪堪贴着她的面颊。
“好妹妹,现在想死么?可惜,哥哥我只会让你,生不如死……”
像是非常享受她惊恐如困兽的眼神,亦南辰扭曲的笑了。
终于知道怕了?知道怕了么?他还以为她真的有那勇气要命一条要头一颗了,不是要较量么?不是说不会放过他么?
修长的手指尖轻捏住薄利的小刀在她身上不断游移,一寸一寸慢悠悠在她身上游移额头,脸颊,鼻梁,下巴,锁骨,胸口,小腹,大腿……
错错张着嘴已经发不出声音,她仿佛看见面容可憎的死神正拿着绳索一步步向她靠近,睁大的眼睛里除了绝望和恐惧,只剩下不停涌出的成串的眼泪。
亦南辰微皱着眉头,像是正在迟疑着从哪里下刀比较合适,当那一丝寒意到达她的双腿间时,宁错错终于受不住这样堪比凌迟的恐吓,直接晕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
宁错错在一阵鸟鸣中醒来,外面天已大亮,盯着天花板的眼睛像是被魔怔,愣愣的无神。
房门咔哒打开的声音,她被惊得浑身一颤,庄婶端着一个托盘进来,宁错错像受到刺激一样翻身就扑过去拉着她的手臂:“蛋蛋呢?蛋蛋呢?”
庄婶儿被她疯狂的表情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后又笑道:“少爷说蛋蛋要带去打针,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蛋蛋也会跟他走呢?”
“不,不,不会的……”
他怎么可能好心带蛋蛋去打针?他说过要把它杀了吃掉的,她丝毫不怀疑他能说得出做得到,庄婶说了一大堆什么话她好像也听不懂,只记住亦南辰拿着刀子对她说过要把蛋蛋拿去杀了炖着吃。
他肯定会杀了它的!
宁错错浑身冒着冷汗,一把丢开庄婶儿赤着脚就往楼下跑,可能是亦南辰刚出去,万分庆幸大门还没来得及关。
阿海正在门口擦车,看见错错慌里慌张地往他的方向冲过来连忙绕过车头去拦住她:“少夫人,少爷交待过你不能出去。”
宁错错才懒得理他交待不交待,她一心只想找到蛋蛋,一定要把它救回来。
蛋蛋对她来说是与飞黎爱情的见证,也是那段刻骨的岁月如今遗留下来的唯一念想,相当于自己和飞黎的第一个孩子,更是现在思想空泛的她的一份精神寄托,怎么能让那个人如此血腥地给杀掉了。
她像个疯婆子似的蛮力推开阿海继续往外跑,阿海没想到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她会突然有那么大力,竟一下被她给推开冲过去了,好在他人高腿长的,几步就追到她面前:“少夫人,别为难我,请回去吧,你要做什么我替你去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