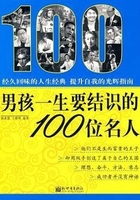让年轻人去玩刀剑、骏马、标枪、狼牙棒、网球、游泳和赛跑吧,把他们的那些丢弃不要的骰子和骨牌留给我们老年人。自然规律本身就把我们赶进了屋子里。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我只能够给自己找一些玩物来消遣,就像对待孩子一样,难怪人们常说老年人又重新变成了孩子。明智和疯狂必须煞费苦心地轮流交替着为我服务,才能够支撑和帮助我度过这个多灾多难的暮年。
同样,我也会去躲避那些哪怕是最轻微的打击,因为有病的心灵是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对于我脆弱的身躯来说,任何打击都会对我造成损伤。以前那些只会伤到我表皮的事情,现在则可能会刺穿我的心脏,尽管我已经十分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脾气去适应各种伤害!
我的理智不允许自己去埋怨和抗拒造化让我承受的烦恼,但是这并不能够阻止我去感受这些烦恼。我愿意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度过饶有趣味、充满快乐的一年安静时光,因为我的人生目的就是要过一种舒适的生活。我并不缺少那种阴沉、麻木的安静,但是它却使我头昏脑胀、昏昏欲睡,我不能够满足于这种清静。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有雅兴的一伙人,不管他们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也不管他们是在法国还是在异国他乡,不管他们是喜欢深居简出,还是喜欢游历四方,只要我与他们性情相投,那么他们只需要打个呼哨,我就一定会前去与他们会合。
人们常说的思想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能够在老年的时候重放光彩。既然如此,我就希望它能够充分地显示这一个特点,如果可能,就让它发芽、开花吧。但是思想往往会背弃我,因为它与躯体犹如兄弟般的亲密相连,它常常会在必要的时候抛下我而去追随躯体。我有心来满足它,吸引它,但却都是枉然。我也曾试图把它从它与躯体的联盟中解脱出来,并向它展示塞涅卡和卡图鲁斯、贵妇和宫廷舞蹈,然而这一切却全是徒劳的。如果它的伙伴患了腹泻,就好象它也患了腹泻似的,就连它所独有和特有的那种活动也不能够激起它的活力。它往往会显得迟钝和麻木,就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是啊,没有轻松活泼的躯体,也就不可能有轻松活泼的精神产品。
古代的思想家在探索精神激奋的原因时,只是把原因归结为神力、爱情、战争、诗歌或酒力,而没有给健康的体魄这一条件足够的重视,他们未免有些失之偏颇。旺盛的血气能够使思想迸发出强烈而明亮的火花,这些思想的火花超出了我们天生的智力,是一种最有灵感,甚至是最狂热的激情。而健康状况的不佳则会使我们变得精神沮丧甚至是呆滞,结果产生出相反的效果,这都是不足为奇的。
柏拉图说一个人的脾气是随和还是乖戾可以显示出他心灵的善良或者歹毒,我对这句话是心悦诚服的。苏格拉底的脸始终如一,始终是明朗的,笑盈盈的;老克拉苏的脸也是始终如一的,但就是从来不笑。
我知道,有很少的一些人会对我的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大胆表示不满,而他们对这些文字表达的大胆思想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顺应了他们的勇气,但是却冒犯了他们的眼睛。只是肤浅地抓住柏拉图文章中的片言只语,而绝口不提他和费东、狄翁、斯特拉、阿盖纳萨之间的来往,这真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做法!不要羞于说出那些我们敢于想的事情。
我十分憎恶那种总是满腹牢骚、愁眉苦脸的人,他们对生活中的乐趣往往是视而不见,但却总是牢牢地抓住生活中的不幸,从哀叹不幸中得到一些满足,就像苍蝇一样,在光洁平滑的物体上是待不住的,而必须停留在粗糙不平的地方;也好像是吸血虫,专找那些不干净的血来吮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