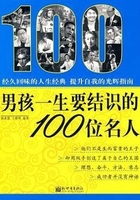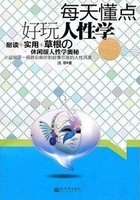“嗯,妙仪是宫中的老人了,教导纪氏礼仪是极好的。太后挑的人向来不错,这次朕看着也很好,只是此番却有些为难。”
如玥便笑着问:“哦,却不知皇上为难些什么?”
延陵澈笑了笑,“原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朕先前答应过昭娘,要让她去教导纪氏的规矩,如今若改了妙仪去,朕只怕会伤了昭娘的颜面。一边是昭娘,一边是太后,朕委实为难。”
说起昭娘,在宫中的地位却是极高的。她是从前延陵澈生母娴妃的陪嫁宫女,配了人后,因顾念娴妃恩德自请入宫做了延陵澈的乳母。多年来悉心照料,两人早已情同母子,是以延陵澈登基后便封了她为二品诰命夫人,有自由出入宫中的特权。如此,便是骄傲如慕太后待她也十分客气。
如玥脱口而出道:“这原也不冲突。谁也没规定教习姑姑只有一个,皇上既应承过昭娘姑姑,便派了两人一同前去,岂不更好?”
延陵澈轻一拍案,脸上笑意轩然,愈发显得眉目温莹如画,“好极。到底是太后跟前的大宫女,聪慧灵敏,比着朕跟前那些粗笨的不知强了多少去。今儿细细一看,如玥你仿佛出落得越发标致了。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可人儿,若非为了大计考虑,朕又如何舍得委屈你这些年为了朕留在太后身边为奴为婢。”
如玥垂头含羞而笑,脸上浮着淡淡一层红晕,“奴婢鄙陋之姿,当不得皇上如此谬赞。奴婢这一生不过是个为奴为婢的命,有幸能得皇上垂青,以一几微贱之身为皇上效力余愿足矣,再不敢再有旁的奢望了。”
一双金线捻绣龙纹如意图案的靴子映入眼帘,仿佛将什么轻轻插入了她的发髻中,“嗯,玉簪配佳人,十分相宜。你只放心,朕并不是那等无情之人,你为朕所做的一切,朕皆了然于心。待他朝大业已成,朕便即刻迎了你回身边封作皇妃,如此才不算辜负了你这些年待朕的情意。”
如玥面上立时滚烫一片,声音愈发低柔:“皇上,这怎么使得?若教太后知道了,奴婢万死难赎。”
男子凑近她耳畔,低沉的声音带着温热的气息袭来,撩得人一阵阵心悸,“怕什么?待到了那一日,她于朕已无任何利用价值,还何须费力敷衍她?不过你既害怕,那咱们此刻便悄悄儿的不教她知道就是。”
便有一股说不出的欢喜甜蜜萦绕在如玥的心头,她不觉用手指绞着帕子,咬着唇,端的是又羞又喜又怯,心里七上八下地打鼓。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抬头看一眼,便在延陵澈含情的目光中红了脸,“呀”的一声跳开。她用帕子捂着脸,嘴角不觉漾开笑颜,跑到门口处却又停下,回头嗔看含笑而立的君王一眼,才转身去了。
如玥一路疾行,到了玉华殿门口却冷静下来,先是将头上的玉簪取下藏入怀中,而后才如常时般进去。行了礼问了安,将延陵澈的意思复述了一遍,可跪了半天膝盖都跪疼了也不见慕太后说话。
她原就心虚,悄悄抬头却见慕太后目光如利剑般直射脸庞,立时惊得口齿不清:“太,太后……”
慕太后咬牙道:“他果然对她有私心,半点委屈也不肯教她受。他待她竟是这样的情深意重,很好,好极!延陵澈,你既这般维护那贱人,便休怨我心狠手辣了!”
如玥听得困惑,忍不住道:“太后的意思,奴婢怎么听不明白?皇上不是应准了太后所请么,他还直赞太后挑人的眼光极好呢。只是先前应承过昭娘,不忍驳了她的面子罢了。太后难不成连昭娘的醋也吃?”
若在平时,她这般插科打诨一番,慕太后也便笑了。
谁知今儿慕太后却如吃了火药般,柳眉竖立,冷声一笑:“好你个死蹄子,他给了你什么好处,竟让你这般猪油蒙心地为他辩解?竟浑忘了谁才是你的正经主子!”
如玥心头一跳,急得眼泪直打转,颤声一再磕头道:“太后明鉴,奴婢对太后一片忠心日月可表,断没有胳膊肘向外弯的道理。只是不忍见太后多心自苦,才多了几句嘴。若太后不喜,奴婢今后只作哑巴,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
慕太后原生了一肚子的气,此刻见如玥吓得颜色尽失倒有些忍俊不禁,挥手道:“罢了罢了,原也不干你的事,是哀家自个儿心情不好,偏拿你当了出气筒。若你真被今儿这一句玩笑话吓住,从此真做了那木头人似的哑巴,哀家跟前就真的连个说笑的人也没有了,这玉华殿也就越发安静冷清了。”
盛势如慕太后,也有这样的唏嘘感慨,倒不由让如玥也生出几分心有戚戚然来。
“如玥。”
如玥连忙道:“奴婢在,太后有何吩咐?”
慕太后不说话,从椅子上起身,扶了如玥的手缓缓走到窗前,凝眸远眺高处,淡声道:“如玥,你看,马上要变天了。”
如玥闻言望去,原先还晴好的天空忽然间乌云密布,如重重山峦般压在皇宫之上,闷雷不时低鸣,电光闪耀,可不是要变天了么?可她也知道,慕太后此刻感慨的,绝非是这天气的变幻莫测,而是帝王的君心莫测。后宫中的女子,生死荣辱皆仰望着同一个男子,即便尊贵如慕太后,也不例外。
若有例外,那人一定会成为后宫女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将是众矢之的的靶子,人人除之而后快。而,那个被慕太后视如大敌的纪芷湮,真的会是皇帝心中的那一个例外么?若她果真是,那要她性命的人里,只怕又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