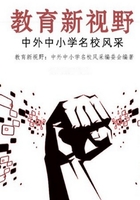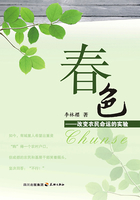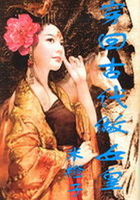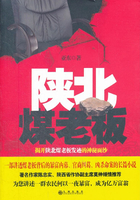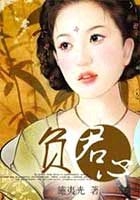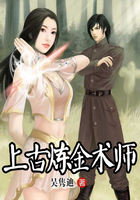管理组批他说,你要什么潜移默化,就是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不要读那么多。于是说不要读“四卷”,读“甲种本”(《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就可以了,“甲种本”只有二十多万字,当相“四卷”的八分之一。后来说,其实“甲种本”都不用读,只要带着问题到《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就可以了。《毛主席语录》只有三四万字,后来又简化到只有三四千字的“老三篇”,简化到只有一百多字“老三段”(《毛主席语录》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三段语录)。从这个趋势可见就是不让这些“反动学生”接触书。这对我这类“痴书者”“迷书者”真是最大的痛苦。其实反动学生有几十人,管理组只有二三人,当然不可能实施有效监督。但他们叫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提倡告密,打小报告,诱以各种虚幻利益。学生大多二十一二岁,没有任何经验,把这些视为正当。这样监督起来起了管理组不能起到的作用。因为管理组成员虽然都是来自高校,但大多是行政人员,文化程度不高。
例如一个学生看穆欣写的《韬奋》,被人发现,组内批判他,一位管理组的来了,只听参加会的这个讲“韬奋”,那个也讲“韬奋”,莫名其妙。但沉默是金,他缄默不语,大家莫测高深。最后他总结会议,用狠狠的口吻说:“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他离开之后,有人差点儿笑背过气去。然而,学生之间的监督,令人不寒而慄。因为彼此心理都差不太多,大体了解,一揭发,立即中的;上纲上线,作诛心之论,这都是管理组人员做不到的。所谓“内行管内行”的可怕即在此。比如我箱底有一本李泽厚的《门外集》(这是李氏最早的一个集子,出版于50年代末)。
有天睡觉时翻一翻,被人发现拿走,后来批判时就拿其中李泽厚论诗引苏东坡《临江仙》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说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单调的劳动外,只能读《人民日报》,其他基本上都不能读,也没有书可读(当时也正是文革热潮中),几年下来,还不退化?那时如有机会我不放弃任何一些有字的纸张。记得北大经济系一同学,把他经济学讲义拆了作手纸,拿来上厕所。我分了半本,每天上厕所撕下一页(相当八开的一张纸),在厕所细读。我这半本是讲“边际效益”(在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不讲这些)的,连续两个月使我有了些这方面的知识。
第三,如果从对读书的限制程度来说,坐监狱都比在南口劳动好,因为监狱主要职责是看着犯人别出事,对于看书则管得不多。在看守所因为对送东西管制较严,所以对送书看得也很紧,但不至于连“毛选”“马列”一类的书都不让送,一般在号子里就有四本“毛选”,随便看,没人敢反对。1975—1976年,我在北京市局看守所K字楼待了一年多,读完了“马恩全集”1—20卷。其中觉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难读。字词都懂,连在一起就搞不清了。为了明白语意,我把重点段落句子加以分解,分清主谓宾,要在书上作标记,划各种符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看守所不许犯人有钢笔、铅笔一类锐利的杆状物。犯人也想出了一种替代物,就是把牙膏皮(那时都是铝皮或铅皮)展开作平面状,然后把牙膏皮用力卷成卷,一端磨尖,即可在纸上画出道道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两卷书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用它纪念我的这一次认真读书,虽然书上的“铅皮”痕迹大多已经模模糊糊了,平时我真是很少如此认真地读过书,大多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到了真正的监狱——北京一监,看书更方便了。因为所在的中队是“反革命中队”,过去的犯人也喜欢读书,有些犯人离监,就把书留了下来;狱中的“小报组”(编辑一种行之于“一监”的《劳改通讯》)也在这个中队,他们那里也有点儿书。这样“一监”的书源远较看守所丰富。另外,家里送书也远较看守所方便,很少被拒。据我所知,仿佛只有鲁迅的书不让送,其他的连线装书都能送进来。民国初年石印本《随园诗文集》我就是在“一监”读的,不知是谁送的。1976年社会上正在搞“评法批儒”,孔老二被骂成臭狗屎,“复辟狂”;秦始皇被捧上天,“千古一帝”。在送书时,只要说一句这是“法家著作”,比说是马列著作还管用。家里给我送的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杜预注的《春秋左氏传》,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都用这个借口拿进来了。其实,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不爱管犯人看什么书,只要不闹事就好。
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里,因为“洋跃进”之故,监狱工厂是塑料厂,面临严重材料不足,犯人没活干,整天在监室读报。那时报纸就一张,翻来覆去地读,有两个小时足矣。其他干什么?弄不好就要闹事。如果犯人自己读读书,监室就安定、安全了许多。个别管理人员爱在读书上较真,目光老盯着犯人读什么书。常常催促犯人买刚刚出版的“毛选”五卷,指定要读报纸上的哪篇文章等(后来《人民日报》老登冤狱平反的事,他才不催促犯人读报了),不让犯人看鲁迅的书等。有一次,这位管理人员还在会上给犯人做思想工作,讲为什么不让送鲁迅的书。他说,“有人家里送鲁迅的书,我让他们拿回去了,说这里不能看鲁迅的书。当时,我只这样做了,没有讲为什么,可能有人心里不服。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了罪,如果你们再读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所以你们不能读鲁迅。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就会口服心服了。”但监狱还是有鲁迅的书,是文革时出版的简装本。可能是这位干部主事之前,犯人的家属送来的。后来犯人走了,此书非珍本秘笈,也就留了下来。
在“一监”一年多的时间里,详读了范注《文心雕龙》,每节都做了笔记。此书后来被一个学生拿走了。用白话翻译《左传》(约三分之一),管理人员认为,“反革命中队”犯人犯的都是“右”的罪行,读读《左传》大有裨益。
犯人当中有些喜欢诗的,《汉语诗律学》被他们拿走了,久假不归,后来我平反了,王力先生那本书逐长留狱中。后来给学生讲“诗律”时,时时念及此书。
往事前尘,转瞬都成过去,现在退休了,谈及人生经历感触最深的还是有没有书读,真是一生所累唯有书。就这点来说,与《博览群书》及嗜书读者还是有点共业吧!
特殊年代的琉璃厂
文革中的琉璃厂是一片萧瑟肃杀,那时还没有现在琉璃厂那些有富贵气、无文化气的牌楼。东西琉璃厂之间各有一个大喇叭,特别是东琉璃厂口更大,仿佛是个小广场。那时汽车也很少,人也少有至者,“小广场”更为空旷,一早一晚显得有些凄凉。有关文化的商店经营的都是“四旧”,自然都要关门。一路商店,大门紧闭,其景象可以想见。大约最早开张的是文物商店(《文物》杂志也是复刊较早的社科刊物),到了1970年已经有几家开门了,然而,买卖还很少。一天,有位老先生非要我陪着去卖清代书法家刘墉的一幅中堂。刘墉字崇儒,号石庵,就是前年火暴京城的刘罗锅。刘氏书法名重当时,可是文革中书法又算什么呢?商店新开门,屋内粉刷一新。天很冷,几个营业员围着烤火。他们打开这幅中堂一看,有位老营业员认识,说:“这是刘石庵的字。”又说:“您这幅字,如果能像我这墙这么白(这幅字已经熏黄了),我给您一块钱。现在这样,我们不收。”可见,当时文物是不值钱的。
琉璃厂旧书店1972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奇怪,那时不是正处在文革中吗?为什么传播“四旧”的旧书店还营业呢?这得从1971年尼克松访华说起。
尼克松访华是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随着他而来的是许多外国记者。当时市面萧条之极,特别是书店,一书架、一书架都是《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这种情景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这是很尴尬的。因为据说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可是为什么市面上啥都没有呢?一般商品还好办,可以东拼西凑弄一点,让商店丰富两天;可是精神产品就不一样了,除了毛著、马列、鲁迅之外都是封、资、修,怎么能让“封、资、修”进入书店,眼睁睁地叫革命群众中毒呢?北京最大的书店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平常里面除了“毛著”外可以说一无所有。在美国总统到达的那一天,我跑到这个书店看它会不会能放出一些“封、资、修”来。
不出我所料,那一天果然放出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书,塞满了书架,还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但都是一般读者绝不会问津的,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等。我买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当我再要买李亚农所著《欣然斋史论集》(这本书我在1963年看过,觉得有新意,当时就想买,但没买到)时,书店店员说:“这是卖外宾的,不卖国内顾客。”大约我们的反资防修精神卫士缺少国际主义精神,不肯保护国际友人,使他们别遭到封、资、修的毒害,而对自己的国民他们是决不会放松保护义务的。我看那些售书员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你稍示不满,就要把你抓起来似的,便赶紧走了。后来,我一连三天都去书店,终于感动一个年轻的店员,他偷偷地卖给我一本,至今我还保留着它。回家后我在书后记录下买到此书的过程。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大约是在1972年春季。
海王村所开放的中国书店(专卖旧书和线装书)分为两个档次。一是西廊,这里只要有介绍信即可,像我这个在农村中学工作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一是北楼,这里要较高层次的单位(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常到这里买书的何其芳拿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北楼。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来说,西廊、北楼没有多大的区别。两处都卖解放前后出版的平装旧书,都卖线装书;其区别是北楼的线装书有不少是善本书,如明万历以后的清康熙间的刻本是很常见的。有一次,我与一书友同进北楼,仅花了二十五元就买了二十五本明刊的《欧阳永叔集》(残本),合一块钱一本。另外,北楼还常卖一些解放后出版的“内部书”(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港版书(如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台版书(如《甲骨文辞典》)等。
一提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凡是北京的旧书爱好者大多都知道孙殿起先生与其外甥雷梦水先生(雷先生已作古)。孙先生的《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研究古籍的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流传极广。雷先生据其卖书的经历写过许多书话,为学人所喜读。我熟悉的海王村中国书店的老师傅马建斋先生,也是一位版本专家,他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所以很少为人所知,其实老先生对于明刻、清刻也是了如指掌的。我在六十年代初认识了这位比我大三四十岁的老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与他很熟了。马先生的腹笥极宽,说起来则滔滔不绝。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书店为了适应旧书业发展的需要,便在新华街南口的“京华大楼”为青年营业员办了个业务学习班,当时已经退休的马先生应邀在那里讲课。我曾到“京华大楼”看过马先生。马先生是个很健谈的人,但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而是与二三友好悄悄地议论。他谈各种刻本的流变,如数家珍,也很喜欢向各种人请教与书籍有关的知识,而且不管对方年龄大小、学历高低,真是做到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他多次与我讨论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诗文作家的生平经历等问题。有一次问我:“朴学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清代才有朴学?”老先生还帮助我找过许多书,现在每当我展玩这些书时,就不由得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