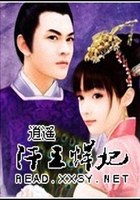一个星期过去,武安的手恢复的很快,往医院扔的那些个银子,没有白花,香颂买来给他进补的粮食,也算物有所值。两人依旧是整天骂骂咧咧,讲不到五句,非得动刀动枪。
周末,阴天,巴黎的天空变得惨白,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闷热,该是快要下雨了。
香颂一下午都坐在窗沿上,缩着身子跟只猫似的,对着天空发呆,手里紧握那枚iphone。
武安撞见她身上这难得的安静,心里别扭,就问“天上能掉下三十万?”
她不做声,只是睫毛往下搭了搭,也不转头看他。约莫一分钟,她才极为哀婉的说:“哎,天上要是能掉下一喜马拉雅,多好啊。”
武安愣住,啊了很大一声,他永远搞不清这个女人脑子里想些什么。
香颂突然转头,望着他,笑了。喜马拉雅,是有个典故的。小学语文老师说以“父亲是山”造个句子,她的句子是:如果天下的父亲都是山,那我爸就是喜马拉雅。从那以后,她就一直私底下管童奕磊叫喜马拉雅,乐了他司机和助理一个月。
“我说童香颂,你这样邪乎,怪吓人的。”武安一屁股坐沙发上,冲她讲。
“我怎么就邪乎了。”她干脆翻了个身,这儿的窗沿特别宽敞,像自己这般苗条的身材,可以睡俩。
这回换他不做声了,只一旁深深望着。其实他也说不出她哪里邪乎了,拿着手机的时候,魂不守舍,眼里的神情是琢磨不透迷离。
见他不语,她也不说话了。然后,又跟只猫似的,眯着眼问:“来巴黎时,我跟我爸闹脾气,你觉得我该主动跟我爸打电话么?”
武安想了想,点点头,“当然应该,你不会每个晚上都在等你爸的电话吧?”
“不算是。”她撇过脸,有种被挫中心事的慌乱。
他朝她翻了个白眼,厉害的教训道:“童香颂,你跟家人也这副狗脾气,看以后谁能受得了你。”
她瞪他,作了一个恶狗发飙咬人前的凶样,“我先打电话给我爸,再来收拾你这妖精。”
妖精是香颂最近给他取的绰号,两星期里,平均每天都有五六个性感尤物跑他家来送东西,一坐好半天,光说话,大有想聊到那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架势。
电话拨通了,她听到了久违的彩铃,“哦爸爸,我要钱,哦妈妈,我要钱,哦爸爸,我需要你的钱”。
那是她高三暑假,给他换的。换了以后,又把司机和助理乐了一个月。
“喂,香颂吧。”
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一清脆的女声,格外刺耳。
香颂似乎听到一声钝响,跟电影里打出的子弹一样,脸上挂着的笑意被打穿一孔,慢慢流逝。她听得出她的声音,wendy,恒基集团的财务经理,性格无比温和的女人。
“我爸呢?”她问的很轻。
“他冲澡,刚进去,不如等下我让他打给你。香颂,你在巴黎还习惯吗?”
“习惯。”抿了抿唇,却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我挂了。”
然后,死死的按下断开连接,指甲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