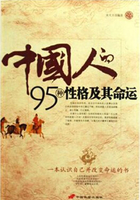回想开工那天,即1909年12月10日,詹天佑在宜昌主持万人典礼,六千多中国员工齐刷刷威武肃立,被中外官民称为中国大地上前所未见的奇观。当时就有外国报纸惊呼:“川路不借贷外款,不雇佣外国技术,现在居然开工了!中国前途叵测,环球列强均当留意!”云云。
几年来,英、法、美、德四强,重又弹起京张铁路开工时的老调子,说“川汉铁路若无外国专家和财政资助,绝难望其成就”,并多次向清廷施加压力,到处宣讲“国家将设立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是政府一大错误”。反反复复,一个目的,就是要威逼晚清再蹈屈辱,出让这条路的承办主权,鸠占鹊巢。
弱国外交无强势,悲剧再度重演于红墙内外:1911年5月20日,清政府不顾川、鄂、湘、粤民众最强烈保路呼声,委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加上新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用两双焦枯之手,与英、法、美、德四国公使,又一次签署了一份泣血合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七十年间,种种不平等条约,到底签署了多少回?
现在,清政府不得不被动地向列强借钱。当年3月向日本借款上千万元,4月,载沣又向四国银行借款高达5000万元。这一次,又借得1600万英镑,算是走到了尽头。皇家能忍,百姓不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合同名为《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直接侵害了川、鄂、湘、粤亿万百姓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借得1600万英镑巨款,怎么还?——两条铁路的归属权便是抵押!这所谓的“收归国有”,实质就是强买强卖,政府出卖了铁路主权。老百姓此前的投资,便即刻化为乌有。
须知筹路之初,四川总督锡良推行一系列融资集股办法,涉及到各阶层人民利益:广大乡绅农户,凡谷十石以上者,强行提取三成精粮折银入股,就是说,你想当股东也得当,不想当也当了;第二种针对大大小小资本家,不管你是老牌还是“新兴”,反正你搞实业总要选项投资,那你就掏钱,认购入股铁路公司吧;第三种才是“官股”,即指国库调拨而言,折五十两为一股。在以上三种不同性质的资金股份中,比重最大的是头一种。据开工前统计,头一种乡绅农户用粮食换来的“租股”资金,聚少成多,占到了川汉铁路首期投资近千万大洋的78%强。川蜀境内,凡有一亩田以上者,全部入了“租股”。换句话说,这川汉铁路公司最大主权,是属于四川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为了国家强盛,更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家园,咱不论豪绅还是小户,啥子都不说了——“每周年四厘行息”,也教人有些盼头;至于大小资本家们纷纷投资入股,那更是“没有利营,不起五更”,斤斤计较实乃商家本分,何况巨额血本呢。
到如今,上头无视川民利益,搞了“国有官办”,一纸卖路合同,路权归了洋人,势必激起众怒,酿发民变。一头骆驼不堪重负时,加一根稻草它即会倒毙;如今把人民逼到这步田地,老骆驼还能站得住吗?
湖南方面首先发动保路事变。信号入川,蜀人沸腾,杀声渐起。恰在此刻,更不可容忍的消息再度传来:盛宣怀和端方于该年6月1日密电川督王人文,命王将川内筑路余款,全部换成国家公有铁路股票。与此同时,那位与詹天佑同事的宜万铁路总理大人李稷勋,居然未经众议,奉命将所余700万两筑路白银,转交端、盛二人,果真化为“国有”了!
可叹中国现代化之初,一头“暴力怒狮”咆哮而出,它那血盆大口,要吞噬一切成果,它将阻断人们前行的道路,让你过不去这阴霾山冈。你绕道,你走弯路,一绕就是上百年。这血腥这暴力,我们却没有躲开。
川汉路之宜万段,款项撤空了,工程停止了,路工愤怒了,骚乱发生了!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的詹天佑、颜德庆和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们,唯余仰天长啸,痛心疾首。
四川“保路同志会”代表全川父老意愿,坚决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归还路权,先派代表赴京请愿,长跪地安门,横遭驱逐。继而,政府新命四川总督赵尔丰,别名“赵屠户”,从康藏地区乘威入川。赵赴任之始,即秉承京都意愿,对请愿川民开枪开炮,无情弹压,造成惨死26人之“成都血案”。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场官民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保路同志会”调动全川枪炮大刀,与赵尔丰官军殊死决战,血染巴山蜀水。湖南湖北即以杀声回应。
特别要指出的是,全川烈火燎原,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驻军,由端方统帅,入川增援,以致武昌空虚,为辛亥革命一举成功造成契机。史载,清军驻鄂共有1.7万人枪,装备精良,此刻端方匆匆调走主力9000兵马赴川参战。其结果,官民大战夏秋两季,“保路同志会”武装集团全面围攻成都,又有陶泽焜团长率敢死队冲杀总督府,生擒赵尔丰——这位皇家军政大员即被新政权宣判死刑,枭首示众;清廷铁路大臣端方,亦被反正的鄂军所杀,血祭保路战旗。
乘此大势,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湖南黄兴大军里应外合,攻占武汉三镇,与成都遥相呼应,同时奏响凯歌,双双宣告独立。很快,上海陈其美,山西阎锡山,战鼓风雷,振聋发聩,纷纷宣告自治。整个中国遍举义旗,大清王朝土崩瓦解。
以保路运动为开端,未出半年,辛亥革命即告成功,千百年封建帝国轰然破碎。保路运动的火把,从川、鄂、湘烧到武昌,又迅猛燎原于整个南方北方,竟然那么快,迅雷不及掩耳。
一场保路运动,川汉铁路宜万段,成为整个燎原革命的炮捻子,书面语言叫导火索,其实质本是经济领域出了问题。
孙中山,在外飘零十六载,终得凯旋。他盛赞保路运动,推动了时代大革命。
毛泽东,便是在这一年,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的文告《救国图存论》。他正是在保路运动那一片杀声中,挥臂削掉头顶长辫的!毛泽东甩掉辫子,拿起了汉阳造步枪,参加了响应革命的长沙新军第25混战旅第50团第一营左队,成为一名列兵。他领取了军中月饷七块大洋,正式参加了“砸烂一个旧世界”的血腥作战。从一条铁路的兴废斗争中,引领出了一位更加震动天地的人物。
这就是历史。与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这样那样的民主革命,不如说这是一场由于新经济与旧政体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而引发的军民大造反。与其说大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不如说,这王朝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推翻的。
鸦片战争以来,大灾大难,八国联军,慈禧西逃,都从未撼动过这座铁打江山,而一场不大不小的铁路主权纠纷,便教山河破碎,王朝倾倒。不值得回味吗?
所谓阶级冲突,民族矛盾,也需要重新分析,具体判断。且看这场保路运动,川中父老同心同德,各阶级分明是一个团结战斗在一起的大整体。因此毛泽东直至晚年还在焦虑地告说天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一个巨人在读懂了中国之后,最深切的体会与表达。什么主义?什么革命?老百姓只要造反,便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至于这造反叫什么名堂,则很不好说。
中国,为什么总是通过造反通过激进通过破坏,才能前进?
晚清时代,也搞过包括立宪在内的种种探索,可惜太迟了太慢了。一切志士仁人的改良,终被暴力“革命”所扑倒,连同限制改良的皇家,一起告别往昔岁月。
只剩下半条幽暗的洞
宜万铁路工地上,早已一片狼藉。詹天佑忧烦失望已到极点:“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或者改行。所有这些难题落在我和我的工程司以及学员身上,尤其是我所处的位置,我须承担一切!”
他最后致信宜万铁路上他的战友,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极大义愤:“颜,督办新任命的总办是谁?……四川铁路的未来,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将予接管,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无任何希望!因此,我们如果再花费心思,那将如修筑空中楼阁,毫无意义了!……所有的好命运均已离开中国人而去!而我们必须甘心居于此等地位——二等地位吗?不!比这还坏。是的,我想我们必须另谋他职——广州现在处于一种激愤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后果,但是我想,恐将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悔恨!”
一场现代化建设,终于转化为一场燎原战火。詹天佑先生不得不选择了放弃。
宜万铁路苍凉败落,三万员工挥泪返乡。他们没有拿到工钱,转而分化开来,一部分人转变为动乱因素,侵乡成匪;一部分人转变为革命因素,先协助义军光复宜昌,然后从工棚搬到军营,扛枪抬炮加盟了宜昌新军。当新军攻打荆州时,有一千名路工成为敢死队员,攻坚最烈。
这段辛酸往事,留下歌谣至今:“辛亥灭满至宜昌,铁路公司光又光,光了也难回家乡!”
川汉铁路宜万段,至此偃旗息鼓。
詹天佑、颜德庆、李稷勋主持修建的晚清宜万铁路,已有一定成绩。这些工程包括:宜昌新码头至小溪塔,建成12公里铁道并铺轨通车;第一标段宜昌至秭归,路基基本完工;还建成了宜昌工程局、第一车站、材料厂、机车库和机务段等基地,已具备机车一台,公务车一台。沿路各标段多处路基、桥梁、隧道、御水大堤,亦具规模。许多新地名,如铁路坝、车站村、铁路小学等,沿用至今。在距离铁路坝二十余公里处,今夷陵区黄花乡一处山坳中,我们尚可探寻到那座昔日隧道工程的遗迹——上风垭隧洞。不知为何,这里不曾被辟为一个旅游点,或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我们赫然看到洞口弧拱顶上,刻有斑驳大字:“上风垭山洞·秀山李稷勋题·宣统二年六月”——这位出生于四川秀山的李大官人,在1910年所题写的这些字,是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沧桑见证。
湖北作家王敬东先生,怀着细细揣摸的心情,深情描绘这项未竟工程:
“走进山坳,远远就看到了昔日宜万铁路的遗址。隧道虽历经百年风雨洗涤,但还是那样牢固。长满青苔的垒壁上,不时可以看到残存着的半圆形的钢钎炮眼的痕迹。在洞口的弧拱顶上,还有着一堵高墙,阻挡着它身后的尘埃。尘埃上杂生着多种植物。我们从一条湿润的小径下到洞口,看到一条伸向远方的完好的隧道,比我们想象中的洞,要高大、气派。这里的每一个砖块,每一方石头,以及砖石之间勾缝的白水泥,是那么清晰可见,轮廓分明,似乎还在意志坚定地等待着什么。有一刻,我们甚至判定它就是处在施工中的模样。再往深看,地面上的淤泥,被人们从洞壁的墙根翻起来,堆在中间,形成一道堤,上面还有人走过的痕迹。它们又分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废弃的隧道。顺着泥堤走向洞的深处,天地一下一下地变得沉浮阴暗起来。深处传出隐隐的滴水声,越来越大,最终响彻了整个洞宇。我们发现,自己走到了堤的尽头。可是,幽暗的隧洞似乎没有止境。我们蹲在堤上,往洞内探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从洞顶落下的水滴敲击声,好像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那历史的沧桑。”
这种“五四”以来白话散文笔法,也是古汉语历经新文学运动的结果,清明而温婉,还有些小资,兼备了翻译作品风味。
总之,一百年前的宜万铁路半途而废,其直接经济损失为650万两至1000万两白银,间接损失无算。前面说了,资金主要来源,是四川乡绅农户以及新老资本家。到1913年6月,即民国二年,工程上所剩余的大批钢轨、枕木和设备,被拆卸搬运到武汉去了,留给湖北人慢慢用吧,川民蜀老,早已在血火中伤透了丹心。
在本章即将结束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示,就是保路运动中人民所一直反对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问题。如今的年轻人会说:经济纠纷难免,铁路基础设施理应国有,清政府强行收回有何不妥?而当时以盛宣怀为尚书的邮传部大臣也正是这样禀奏的。奏折称:“然欲造路,纵横四达,则非国家出以全力,断难办到。”——要回应此议,还需人民。请看四川“保路同志会”上书驳斥,是怎样说的:“果政府有钱,政府自造,不以路权抵借外款,不受外人干涉,真正是国家全力经营,又何尝不好?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以全力夺百姓而送与外人!将来纵横四达之铁路虽能办到,特所谓全力者,非吾国之全力,乃外人之全力耳!”——人民并不反对真正的铁路国有,真相是朝廷出卖主权,剥夺国民物权,这就无怪乎亿万人民要奋起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