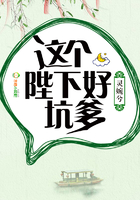我摇头,惊恐地看向她。不可能,月希还在这世上的,刚才若离说她还在的!
那个人影捂着嘴笑了起来,我愈加怀疑。月希她是不可能做这些可爱的小动作的,她只会微笑,浅浅淡淡,也会叫风影,声音婉转低吟。眼前的这个白色人影,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忧伤起来,她说风影,我在这里,已经五百年了。
我震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是月希的精魂,负责在这里守护你。至于明天的那些术士,她的话语停顿在空气中,然后抬头仰望天空。做你应该做的事情,风影。
你是说,让我去杀了那些术士?
她摇头,渐渐飘远。问你自己的心。
我沉默。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只是偶尔一日贪玩越过了这片草地,看到正在变身的月希。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可是整整五百年面目全非地生活,这样的惩罚还不够么?
我还是见到了那群术士,领头的是个女子,披着白色披风,大大的帽子将她遮得严严实实。夜很黑,她手里的魔杖发出灿烂的银白光芒。她身后跟了三个人,披着灰色披风,缓慢且坚定地往前走着。
我蛰伏在草丛里迟迟没有动手,白衣术士,小时候听父亲提过。他说我们生活着的这片大地就是他们在守护着,他们灵力高强降妖除魔。只是他们也有害怕的东西,比如我现在手中的这把碧灵剑,它能吸取所有灵物的灵力,让他们力竭而亡。是若离找来给我的,他要我绝不手软杀了他们,我迟疑,我真的要冲出去么?那个女子,我不是该用生命来感谢的么?
是了,用生命感谢,我低语。怨灵咒在那一瞬间从我的嘴里念出,击打在那个白衣女子的头顶。她的身影瞬间笼罩在一片浅绿光芒里,脸色惨白,她的血正源源不断的涌向我的身体,随即下一刻她举起了手中的圣杖。
圣月,光!
她急呼。另外三个人迅速地围在她四周,双手托起灵力注入她的头顶,嘴里念念有词。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所有的灵力也不过只月希送我的那些,浅薄得很。而我不知道在哪一刻早丢弃了碧灵剑,因为我迷茫的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所以只能选择离去。
月希,昏迷之前我叫空气中的那个幻影。我们一起走,可好?她对我微笑点头,我轻轻闭上眼睛。
睁开眼时看到的是那个穿白色披风的女子,我惊讶且恐惧。你醒了?她轻声说,声音柔和。我却没见她张开嘴过,我瞪大双眼,想起了远古关于精灵的传说。
你是?我问得小心翼翼,担心这又是另一段梦境,或者是另一个异常不堪的结局。
月影,来自精灵国。她果然,不用开口就能说话的。
听到这话我又陷入了昏迷,或许是惊吓过度,或者是别的什么。可是这次梦里我见到了月希,她说风影,你竟然让自己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
我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努力结局都是一样的,碧灵剑能吸收万物的灵力,却唯独只忠诚于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被选为狼人,为什么精灵和术士不干脆杀了我?月希,为什么你同时存在于三个世界里,冷眼旁观我的遭遇,却从不出手搭救或是别的?我丢弃了碧灵剑,是否所有人都惊慌失措了?
我悲哀的笑了。父亲,您让您平凡的儿子从小就断绝与任何灵力接触的机会,您将碧灵剑丢向大洋深处。却原来一个人,真的有命定一说。他逃脱不了做为灵者这一特殊群体所要承担的命运和结果,只是当初若你早知晓,怕是要送我去做术士的吧,也好过做这样一个任人摆布的不知道是人还是禽兽的狼人要好。当年您夺下碧灵剑并驾御了它,这难道就是天谴?您深知它的存在会左右五百年后的这场战乱,于是丢弃。可最终,它还是回到我的手里,我是不是该庆幸那一刻,我几乎与你携手并肩过?
送我回到那片草丛里,我对那个叫月影的女子说。我累了,想休息。她看了我许久,我知道她能看透我的心,所以她点头。你如此固执,就依你。她轻声叹息。
回到那片草丛后月影离开了,她走的时候一直沉默着,可是精灵不是会传声术的么?她只是不知道在那时该表达些什么,我知道,她会留话给我的。果然风中传来她的声音,风影,每一个灵者都该担负起万千生灵的安乐,你不能逃脱。她说就算你觉得两族之战利用了你,相信我,精灵不会逼你做任何事情,一切,都要你自愿才行。
她隔了那么远,可是我仍然感觉她像就在我身边一样。她说风影,什么时候你想通了需要我,就对着月亮叫我,我会听到的。
不知道过了多少日,没有人理我。我一个人如那五百年中的每一天每时每刻一样孤单,我突然想回去看我的父亲,于是我对着月亮轻声呼唤,月影,我有话说。
她在空气里浅笑盈盈,眉眼间有些疲惫,像是刚刚经历过战斗似的。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你没事吧?我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莫明其妙的话语,随即我们都呆在那里。这个女子,她是精灵啊,那样至高无上的族群,我究竟想做什么?
她浅笑,你的灵力果然不浅呢,竟能看出我刚刚战斗过。没事,若离与我早就相识,彼此的那些招数大同小异,每次遇上都只能耗费时间纠缠着。好在你叫了我,我便有理由离开了。她笑得有些无可奈何,接着问得小心翼翼,你打算,回家看看?
我点头,可以的话,请送我回去?
她眼神复杂地看着我,随即口里念念有词。我只觉自己脱离了地面,耳旁有风呼啸刮过,然后一眨眼间我就坐在了自已家的书房里。桌上点着香料,父亲背对着我在擦拭一幅画像,我轻轻走过去打算给他一个惊喜。当我探头要跟他打招呼时,我惊呆了!画像上的女子是谁来着?那么熟悉的身影!
父亲看向我,眼神复杂。洛基,你何时,沦落至此了?
我笑,有何不好?我本是灵者,无论怎样遮掩都逃不掉。当年您封印了我所有灵力,不过只是欲盖弥彰而已。我看见母亲的灵位,走上前去上香,我知道父亲的眼神紧随着我,他在试探我的灵力。狼人与魔兽不同,他们的存在是亦正亦邪的,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与精灵之间的矛盾已如此之深了?
身后有呼啸的风声,我轻轻闭上眼睛。父亲,你仍然走了这一步。他的雷灵咒击打过来,我抱着母亲的灵位迅速闪过。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整个壁橱被烧毁,身后的父亲眼神哀怨。洛基,你不该回来的,我是术士,我们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你明白么?
那么,是谁牵引我走到了如此地步?狼人、术士、恶魔,这本是与我无关的!
父亲沉默下来轻声叹息,然后他背转身去。他的面前是那幅描着白衣锦绣女子的画像,他伸手轻轻抚摸她,眼神温和。一切,就当是梦吧。他低语。
我有些瑟缩,走上前去,我们是两父子,怎么能对立。她,是谁呢?我问父亲。
他转回头,洛基,是我不好,是我当年太过天真。你想做什么由着自己的心,我不能再陪着你,我会将我的灵力全都给你。
一阵白光升起,我被笼罩其中,父亲在我的眼前渐渐模糊,我流下泪来。为什么所有人的付出都是以我为名的,我蹲下身子捂住脸,窗外风雨一片。
月影感应着脑海中那个男子的悲伤,又想起了当年月希离开的那个晚上。她那么决绝,没有回头看她和父亲,父亲的眼神异常冰冷。月影,你要记得,不要陷入俗世里的爱情,精灵族即将要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浩劫,站在哪个位置都会很痛苦的。
那么,那些战争不能结束么?她问得天真。
她还记得,父亲一下子苍老下去的容颜,他无奈摇头。如果我们退却了,这个世界将不会再有任何光明。
于是她开始懂得,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这个世界万千生灵的光明,她想她与姐姐之间若是有一个人能幸福,她也安心。一千年前的那场战争和现在何其相似,不同的是那次是三族联手共同击败魔族,狼族若离曾经站在山巅长啸,后面浩浩荡荡的都是他的子民,她和姐姐陷入到水深火热地境地,看到他深遂的眼睛,无比安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与姐姐走那么近了,携手出现在父亲面前,姐姐那样倔强地要随着他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她用了索魂引。
月影笑得凄凉,看他将姐姐的灵魂挨个招回,装在三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瓶里。她问他,你带走的,就是你想要的么?他摇头。不,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向远方走去,月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企及的愿望和不甘心,而你,就是我的不甘心。
那一瞬她瘫软在地,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来着。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看她的温和目光,怎么会看错?可是他接住的却是月希昏迷的身体,那一刻她深呼吸对他微笑,请你救救她。她轻声说。
月光仍然晶莹,他早已带走了姐姐的亡灵。姐姐那样固执,就只能换她故作清醒。身后有人看了她许久,是人类的术士,他们与精灵王并肩作战,她充满感激。
她转回头看他,他笑得腼腆。你没事吧?他轻轻问她,声音空灵。他该是,有很高的灵力吧,她猜测着。
她摇头,你叫什么?
端泽。公主,我送你回去好么?
她轻轻点头,他不再多语。真是个聪明的人类,即使看到许多不该看的场景心里充满了疑问,也强压下自己的好奇心扶着她一步一步往前走去。他们都没有用灵力,虔诚地握着彼此的手。她侧过头去看他的脸,是个俊帅的男子。端泽,她叫他。
他轻轻嗯了一声,转回头看她,眼神带着询问。她摇头,没什么,只是想叫叫你的名字。
若离带走姐姐后父亲曾郑重其事的将她叫去,要她清楚自己必须担负的责任。她闭上眼睛聆听精灵们在每日清晨吟诵的天簌般的歌声,感觉有什么正从心底慢慢逝去。她鼻头发酸情不自禁的掉下眼泪,听见父亲轻微地叹息。
端泽将她送到族群转身离去,走出几步又回头。公主,你会一直记得我么?无论经过多少世多少时日,你要永远记得我。
她讶异,这个人,在那场战争中他一直走在最前面,至少是在她的前面。有一刻他张开结界保护她,自己却受伤了。她故意不去看他不询问他的消息,其实是想让他忘记。原来一切都是徒劳的,她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于是只有沉默。他深深地看着她,片刻后转过头去,月影,我会一直想念你。
她有时会想起姐姐,她们俩长得那么像,性格却完全不同。月希可以不顾一切的依着自己,曾经这也是她的向往。而她却只能对着天空中的月影,轻轻捂住自己的心。
我终于回到了这场精灵与狼族的战争里,可是我却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说,我是风影。没有人理我,我站在他们中间茫然地看向两边。精灵族派了最精锐的弓箭部队,月影在最前面,穿白色及地连身长裙,优美飘逸,狼族战士遍布四周山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