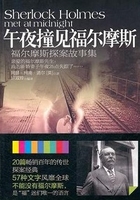第一章 第一章 (1)
Chapter1
盐城是一个中等城市,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博物馆,不仅拥有保存完好的古代井盐业遗址和殿阁巍峨的古代建筑,还拥有着令世界惊叹的神奇而庞大的恐龙动物群化石,同时这里一年一度的盐城灯会也是举世闻名的。那绚丽多彩、内蕴丰富的彩灯艺术,尤为耀人眼目、撩人情思。这里没有一般大城市的张扬喧哗,激烈竞争和生存压力,但它并不缺乏生机与活力,而是充满了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向往,它有一份悠然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轻松快乐的气息。这是一座让人安静,也让人热血沸腾的城市。盐城是安稳的、悠闲的、宁静的,山的丰美和水的灵秀养育了这里一代又一代智慧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这里的女人不仅肌肤似雪、娇美动人,而且精明能干、聪慧灵巧。这是上苍赐给盐城人最好的礼物!冯权裔便是典型的盐城人。
冯权裔是孤单且复杂的,因为她的生命中有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她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从没听她提起过她的父母,也没有人认识她的父母,她像个真空人生活在这里。因为她的孤独与美丽,还因为她的才华与能力,所以在人们的眼里,她不但不可怜,相反是孤傲清高的。
一向的我行我素令冯权裔即使身处繁华,她也是孤独的,而且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也许自娘胎她就承继了抑郁和落寞。有时候,生命便是如此顽强而执著。只有在书的海洋中或山间作画时,她的热情才会被激发,她的才情和狂想才会喷薄而出。
可能是孤独得太久了,她也渴望一个家的温暖。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刘新廷。虽说刘新廷只是个工人,但他相貌俊秀又少言寡语,看起来也是斯文的,冯权裔把自己关于爱的浪漫幻想全部倾注在了刘新廷的身上。
那时冯权裔在读夜大,英俊的刘新廷总是将最完美的表达化为行动,每天按时去夜校门口接她,然后送她回她的单身宿舍,有时还做上一些可口的饭菜给她吃,趁她吃饭的时候又会替她打扫房间,洗衣服。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做,自始至终没有多的语言,冯权裔毕竟是女孩子,因为害羞也很少说话,但是他的行为却一点点浸润着她的心,她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活在情感的荒漠里,不论是友情、爱情、亲情,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刘新廷的温暖与呵护让她重拾了遥远记忆里的温情。虽然他们并没有心灵的沟通,但他对她的爱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冯权裔真的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温暖实在的属于自己的家。从小她就有一种恋父情结,而刘新廷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让她嗅到了父亲般的味道,他比一个最溺爱孩子的父亲还宠爱她。这伟大而无私的父爱像温暖的春风浓浓地围绕着她。
也许是缘于一种对孤独的害怕;也许是感动于刘新廷这份可以吃进胃里、穿在身上的爱;又也许是为了跟某一个人作对——一想到她知道后会气得暴跳如雷,七窍生烟,冯权裔就感到扬眉吐气,一向的叛逆让她决定,就是他了。
她不再犹豫,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刘新廷的求婚,并以极快的速度结婚搬进了刘家。就在新婚之夜,她却遗憾地发现她莫名地全身僵硬,她的身体竟然在抗拒那个几近完美的躯体。在做了无数次尝试以后,冯权裔知道他们的身体不能相容,她失望极了。这时她发现她需要的不是一个父亲,而是一个男人,自己可以去爱的男人,当初她只知道去索取和享受爱,而放弃和忽略了自己的主动权。
她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去享受他给予她的父爱,她把他当做爱人来看待。她尽量去迷恋他那俊美迷人的脸、结实的胸膛、修长的双腿,可是她却惊异地发现,他是那样的木讷,她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完美而呆板的人,她要的是一个就算不美但很生动、有灵气的一个人。可是这些对刘新廷来说要求未免太高了,他那双黑黝黝的大眼睛毫无神采。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这窗户里没有内容。她要怎么与他交流,他又怎么可能走进她的心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呢?她彻底放弃了努力。
刘新廷是很单纯善良的,他不懂她的心,他根本就走不进她的内心,他只是一味卑微地对她好。他因为如愿以偿娶到了权裔而无怨无悔,权裔不仅高贵美丽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她虽只是夜大毕业,但她擅长舞文弄墨又一直是她单位的骨干,而他刘新廷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全心全意地对她,可是她对他只是似有若无的样子,生活于她只是一杯索然寡味的白开水。
一切都如此混乱不堪。婆媳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矛盾,婆婆渐渐对权裔失去了刚进门时的耐性,开始百般挑剔。她的读书作画和不擅家务变得罪大恶极,是可忍孰不可忍。权裔已尽量少去外面写生画画,多待在家,对婆婆也是尽量孝顺,但婆婆仍然有千千万万的借口来责难和辱骂她。
就在权裔对婚姻不满之时,有一个小生命来到了她的体内。不知是来得恰到好处还是来得不是时候,总之她不敢违背上苍的意志,这是跟她生命相连的一个生命,她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他的降临。这是一场宿命的安排吗?她开始有点体悟出母亲当年在不爱父亲甚至是痛恨父亲的情况下却生下她的感受。
当年她曾疯狂地质问母亲:“你既然那么恨他,为什么不打掉我,还要让我来到这个世上,这一切的痛苦和灾难都是你强加给我的。”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初生婴儿小小的脸庞上。他紧闭的眼睛有着长长的睫毛,浓密光润的头发黑而亮,他的肤色是一种象牙般润泽的白,在清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那半透明状的肌肤隐隐透出粉嫩嫩的红,“真是一个天使!”权裔感动了,感动于生命的奇妙,这么美好而充满希望的小生命,给了权裔最大的安慰与快乐。
生活中真是处处充满痛苦,还在月子中的权裔头裹着毛巾,半躺在床上,婆婆喜笑颜开地抱着襁褓中的砚彧,又是摇又是拍着对他说:“乖,小宝贝,给奶奶笑一个,笑啊!哦!笑了,我的乖孙孙给奶奶笑了!宝贝儿!记住啊!你叫砚彧,刘砚彧,你以后好好学习,长大了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你要超过你妈妈啊!哦!又笑了……”
刘新廷走进来,将一张纸递给权裔,权裔看看还给刘新廷说:“这是你们单位给孩子办的儿保卡片,你照着填写就行了。”
刘新廷为难地接过说:“我不会填。”
“照着前言搭后语就是。”
刘新廷咽了口唾沫,有些语塞地说:“我不识字。”
“什么?”权裔惊异地望向他,“你不识字,我没听错吧?”
“我真的不识字,我六岁父亲就死了……”
权裔傻眼了,大脑有一瞬的空白,眼泪就这样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就如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大旋风,权裔仅存的希望彻底成为泡影。权裔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外表英俊、温文尔雅的老公,竟然是不识一字的文盲,老天给她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啊!
Chapter2
转眼间已经六年了,冯权裔早已放弃了对刘新廷更多的奢望。她除了认真工作以外,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儿子刘砚彧的身上。
冯权裔下班刚进家门,儿子刘砚彧就飞扑进她的怀里,搂着她的脖子就要亲吻。婆婆忙紧张地阻止。冯权裔也敏感地推开儿子说:“好了,好了,乖!”她有些疲惫地将手中的两袋食品递给儿子和婆婆,婆婆接过袋子说:“哎呀,权裔你看你,我又不是孩子。”
虽然婆婆有些挑剔但她却给了自己一份亲情和家的温暖,特别是对儿子这样的疼爱与呵护,一丝不苟的照顾,都让权裔觉得孝顺她是理所应当的。她笑着说:“妈,孩子有吃你更应该吃。这桃片糕是你最喜欢的,另外,这个薄荷糖,你晚上咳嗽的时候含一块在嘴里,喉咙马上就会凉凉的,气也不会那么紧。”婆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自己总在新廷面前说权裔的不是,权裔却是每次给砚彧买零食都会给她也买一份,看砚彧还黏着妈妈,她放下东西转身过来伸手接过砚彧说:“砚彧,不要缠着妈妈了,妈妈很累,来跟奶奶睡觉啦!”
权裔抱着儿子用脸亲了亲,说:“乖,跟奶奶去吧,妈妈明天早点回来陪你玩。”
“说话算数?”
“好。”
“一言为定。”
“是,一言为定。”
独自饮酒的刘新廷听着权裔轻轻走近的脚步声,一下就紧张起来,目光有些闪躲地朝她瞟了一眼,埋着头说:“回来了,吃饭吧。”这么多年了,新廷始终没有信心正眼面对权裔,他像个忠心耿耿的仆人一样全心为他们母子服务,对权裔又敬又畏。
权裔看着她的座位上那套与众不同的碗筷,她一下就没有了食欲,她知道这是他们给她的特殊待遇。她只淡淡地说:“我吃过了,我上楼顶看看。”
暗淡的星光下,权裔来到顶楼小花园,她拿起水壶为心爱的花草浇水,看着独自盛放的花朵让她有顾影自怜之感。她细心地捧起地上的泥土,只闻到散发出来的冰凉的泥土味道。知道婆婆本就不太喜欢她,现在自己又得了乙肝,婆婆就更加嫌弃她了。新廷是维护自己的,可惜他既不懂得安慰体贴自己也不会顶撞他的母亲。所幸儿子砚彧跟自己是贴心的,想到儿子,权裔不禁开心起来。
第二天清晨起来,权裔心里就莫名地发慌。她很敏感地跑去儿子房间,砚彧还在甜甜的睡梦中,窗外泻进的阳光洒在他粉嫩嫩的脸上。权裔舒了口气,开心地拍拍儿子的脸:“起床了,小懒猫,太阳晒屁股了。”
勤劳的刘新廷早已做好了早餐等着他们母子,砚彧看看桌上的鸡蛋、牛奶,娇嗔地说:“爸爸,我不吃鸡蛋。”
“问你妈同意吗。”
权裔知道儿子想什么,故意严肃地说:“给我一个理由。”
“好妈妈,乖妈妈……”砚彧装出一副耍赖的样子,拉着权裔的手,“这鸡蛋有问题,我每次吃了都想吐。”
权裔心里好笑,依然装作严肃地说:“这不是理由,把牛奶喝了,待会儿我给你钱,上学的时候自己在楼下买个面包。”
“谢谢妈妈!”砚彧苦着的脸一下舒展开来,端起牛奶一口就喝下去了。
“去把书包整理好。”
砚彧调皮地行了个军礼应道:“yes,sir!”
权裔看着这个可爱的儿子,惬意地笑了。突然,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哭,她身体内的某根神经就抽搐了一下,她觉得好怪,一大早怎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或许是昨晚没睡好吧。一会儿,那哭声又飘了过来,似乎还伴有大声的叫喊,权裔竖着耳朵仔细聆听。
“谁在哭?”
话音未落,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刘叔叔,刘叔叔,快救救我爸爸……”
灾难就这么降临了,只是一夕之间!隔壁的吴宇云就上吊自杀了,那么决然,那么悲怆。也许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他犹豫了好久,可是没人知道他死之前是怎么想的,他的母亲伤心欲绝,这么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竟然这么坚决地选择了死亡。他只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妈,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可你从不对我发火,尽管我无端地冲你大吼大叫,你仍然是那么宽容,对不起……
妈,我知道你这一辈子把我和姐拉扯成人很不容易,我是要报答的,所以我努力工作,可我太认真,认真得让自己一塌糊涂!在这个金钱与权力并存的时代,我竟然想蚍蜉撼树——可悲!
自远惠下岗,我跟丈母娘借钱买摩托车载客,结果钱没挣到还出了车祸,连医药费也是远惠回娘家借的,不得已远惠出外打工还债,可是又一去音信杳无。
原谅我,妈!其实,在医生决定锯掉我一条腿的时候,我已不是你原来的那个儿子了。
妈,我把伟伟留给你,实在是不得已,可我该怎么做,我已经失去了我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而如今,我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废人,以后一家人的生活、伟伟的学费、外面的债……我也无力支撑了,妈,你就让我去吧,对不起!
宇云绝笔
吴宇云就这么走了,他悲痛欲绝的母亲号哭着,他唯一的儿子伟伟伤心无助地哭喊着爸爸,旁观的人们也纷纷流下同情的眼泪。丧事过后,吴妈带着伟伟去她女儿家了,对门从此空无一人,冷清与凄凉久久地围绕着他们,挥之不去。
Chapter3
夕阳西下,桃花山的树枝间跳动着余晖,将潺潺的溪水,寂静的山崖勾勒出层次丰富的光影。黄昏的春风带着一丝暖意扑面而来,让人陶然欲醉。
这里是权裔的世外桃源,她喜欢独自来到这里写字、画画,呼吸最清新洁净的空气。走在这光影里,感受着融融的暖意,望着太阳渐渐消融于远山,她感慨万千,吴宇云是解脱了,六尺男儿瞬间便灰飞烟灭。生活的种种压力以及情感的取舍牵绊,通通由一道浓烟化为乌有。可是他就不曾想过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怎样一种绝望?不曾想过孩子失去父亲是怎样一种痛苦?他轻轻松松的几句对不起就搁下所有的责任,留下老母幼儿又将何以处之?他有勇气逃避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呢?权裔莫名地有些愤怒,这是一个不可原谅却又可怜的男人。
权裔信步走到山崖下,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想着心事。人呐,只要是能活着,该是多么的幸运,况且人生还有那么多内容。难道吴宇云在结束自己的刹那间就不曾后悔?不,他那睁大的双眼,不正代表着他对这世界的不舍和眷恋,他那微开的双唇,不是正在向亲人忏悔和求救?可,生命啊,总是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脆弱!生与死之间只是多口气和少口气的差别。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珍惜这脆弱的生命,权裔这样想着的时候,心情舒畅了不少。眼看渐渐暗下的光线,她起身踏上绿油油的草埂,见草埂两旁被太阳晒得抽了茎似趴在地上的细草,想象着它们朝露后的葱茂。她深呼了一口气,感觉全身无比的轻松,准备穿过桃花树林就回家了。
天空开始降下第一道帷幕,漫天的晚霞只剩下些许余晖。曾林试图捕捉这光与影的韵律,他满怀激情地在画布上涂抹,几近疯狂。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刻,他喜欢这样的时候作画,看着完成的作品,他满意地吹了声口哨。
桃花树林里,飘落的粉红花瓣在微风中跳舞。一个幽灵般飘逸的女子,在那里独自漫步。曾林看着这幅美妙的图画,情不自禁地又拿起画笔,这是一个孤独而落寞的女子,虽似一尘不染却又忧郁满怀。曾林莫名地被她所吸引,不只因为她外形的美,还有那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出尘的气质,有一种神秘的气息慢慢地在空气里萦绕绽放。他激动地描画起来,刚要收笔,见那女子突然要走,他情不自禁扑上前去叫住她。结果很不幸,他连人带画从山崖摔了下去。
权裔是在听到一声尖叫后回过头来的。她猝不及防,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物体。然后这个物体从地上缓缓地爬了起来,竟然是一个人。她就这么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男人,有那么一会儿,她竟像灵魂出了窍般怔怔地。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是多么耀眼啊,一身白色休闲装,虽有些狼狈,但仍看得出他个头挺拔,仪表不俗。可是他的脸,怎么那么亲切熟悉?一时间感觉她跟这个男人之间好像有着某种奇妙的缘分。
曾林狼狈不堪地忍着痛站起来,他看着这个呆呆盯着自己的女子,好像摔下悬崖的是她,他扭着腰说:“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吧?”
权裔这才收回视线,知道自己有些失态,想想又有些好笑,这个人还真是怪,自己摔了还问别人,忙说:“还好,没有吓到我,只是你在崖边做什么,好在不是太高,不然你……”她吞回了后面的话,弯腰帮他拾起地上的画板,不经意地瞟了一眼,心中一惊,迟疑地将画板送还给曾林。
“谢谢!”曾林伸手接过画板,“对不起!你生气了吗?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我最初还以为……”
“以为什么,以为是幽灵吧?嗯……你能画出幽灵的神态还不错。”
曾林有些释怀,但仍有些怀疑地说:“你不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把你画成这样。”
“我本来就是这样。”
“不,你比我的画可要好很多。”
“是恭维还是讽刺?”她看着他笑。
曾林竟然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不,我是说真的,你那种清纯的幽雅,冷傲的气质,还有那种……”他还想找出一些词汇来形容她,但久久呆在那里接不上话。
权裔看着他那认真而又有些幼稚的样子,笑笑说:“你还真有幽默感。”转身欲走,看看他撑着腰的手又问,“你确定自己没问题吗?”
“哦,没,没问题!”
“你确定?”
曾林真诚地点点头:“确定!”权裔朝他一笑大步走了。
“哎!”曾林想伸手去拉她,立即又将手缩了回来,见权裔似乎没听到他的叫声,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便跟了上去。刚迈出一步,腰痛得他冒冷汗,只好站立身子冲权裔喊道:“哎,我叫曾林,一医院胸外科医生,你呢,你叫什么?我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我怎么才能跟你联系?”
“天快黑了,回家吧!”权裔是很想交这个朋友,但想着自己的情况她在心里暗自叹息,然后决然地大步走进桃花树林。曾林不舍地望着桃花树林里飘然而去的权裔。他第一眼见到冯权裔的时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说不清哪一点就牵动了他身体内的某根神经,并且从此就朝思暮想起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连曾林自己也解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