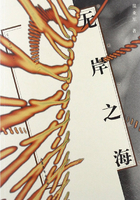“我现在就不担心了?你是成心的,是不是?你巴不得她有个三长两短。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很恨我,但权裔是无辜的。我警告你,要是今晚我找不到她,或是她有任何的闪失,我一辈子都不会饶恕你!”
奶母委屈地说:“我也想天天在家看着她,可六张嘴望着我顿顿要吃,农业社每天到时要出工,趁休息我还要割牛草挣工分,一早一晚还要去喂队上那十几头猪,我一落屋不见她,就跟几个孩子满山遍野地找她,屁股连板凳都没挨一下,我又跑二十里地来找你……”
郑权口气缓和些了:“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也没办法才把权裔交给你,我只要一过了这关,立刻就会带她走。”
奶母难过地含泪说:“你只生了她一个啊?”
郑权恼火地说:“我啥时候没管你们?”
郑权白她一眼,回转身,照着火把极度不安地四处观看着,喊道:“权裔——这深更半夜的,胆子那么小,肯定不会在这儿,你当真其他地方都找过了?”
奶母跟着他小跑着说:“找过了,她平时一跑就是去我们那后山上,还有保管室的树林,跟屋背后那片竹林里,这周围五六里地,我们都找遍了。”
郑权焦心难过地自顾自喊道说:“权裔——女儿!你在哪里?”他望向两步就到的坟地说:“妈,你帮帮我,给我指条路吧,权裔她在哪儿?”郑权话音未落,火把的光芒便照见坟边的权裔,郑权乍地悲喜交加地哭喊一声:“权裔!”忙将火把递给奶母,心痛地跪下,一把抱起权裔,拥在胸口,激动地柔声叫道,“权裔,我的女儿,你吓死爸爸了,宝贝儿,宝贝儿!”
权裔睁开惺忪的眼睛,她借着跳跃的火把光亮,惊喜地望着郑权淌泪的脸,叫道:“爸爸!”
郑权酸楚地说:“是爸爸,权裔,我是爸爸!”
“我是在做梦吗?”
“没有,你摸摸。”郑权捉住她的手,摸向自己的脸,“爸爸是真真实实的,爸爸正抱着你。”
权裔喜极地悲哭说:“爸爸,我们回家啊!”
郑权难过地:“对不起女儿,对不起。”郑权如获至宝般紧抱着她,撑起身,心碎地往回走。奶母暗自妒恨地忙举着火把,领前照路。
权裔紧搂着父亲,甜甜地假寐着,趴在他肩头。郑权跨进家门,站在门口的饭桌边,奶母将手中火把引燃了灶头的煤油灯,把火把插灭在灶门前的灰坑里。
郑权难过地拥着权裔,亲了亲,拍拍她说:“权裔,我们到家了。”
权裔欣喜地睁开眼,直起身,她用眼一望,忙张皇地抱着父亲的脖子,恐慌地叫道:“我不要回这儿,爸爸走,我们走,我不要回这儿,这儿不是我们的家,我要回奶奶那边去,走!爸爸,快走!”权裔大声哭喊着。
郑权哄着她说:“权裔,听话啊!爸爸有事,必须要连夜赶回去,所以不能留下来陪你。等过些日子,爸爸忙完了工作,一定回来接你。”
“我不,我不,我要跟你一起走,带我走,爸爸,我不要再离开你。”
郑权心酸地说:“宝贝儿,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不方便带着你。”
“我会很乖,很听话,我自己走路,我决不烦你,我还能照顾你,帮你做很多事,爸爸,我求你了!带上我吧,随便你要去什么地方,带上我,爸爸——”
郑权无比心痛地想抱紧女儿,突然又硬起心肠厉声说:“你再不听话,爸爸就不要你了!”权裔悲痛地趴在他肩上哭泣着。
灶台边一直沉默的奶母,将灰坑里的火把重新在煤油灯上接燃,她走向郑权。这时,火把的光亮映照出一旁站在里屋门口观看的五张孩子的脸。郑权酸楚地一手接过火把。奶母从他怀里抱过权裔。
猛地,权裔惊号起来,死死地搂着父亲的脖子哭喊:“爸爸——别不要我,爸爸,我求你,你让我自己回家吧,你把我和奶奶埋在一起,我不要留在这儿,爸爸!爸爸……”奶母紧抱权裔,用力将她和郑权分开。
郑权痛心地眼含泪水,一边掰开权裔拼命抓住他不放的手,心碎地说:“爸爸会再回来看你的,听话,权裔,用不着多久,爸爸一定会回来接你,那时,爸爸就再也不离开你了。听话,女儿!”郑权摆脱了权裔,抑制不住泪流地转身夺门而去。
权裔悲号着,奋力要往门口奔,她双手无助地伸向门外乱抓,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爸爸!爸爸!我的爸爸。”
见郑权走远,奶母一把将权裔甩向灶台前的柴草堆上,含满泪水的眼恨恨的,她愤然跨进屋去,不再理睬权裔。
大哥见母亲受委屈,将所有的怨恨转嫁于权裔,他攥紧拳头,怒发冲冠地逼向权裔。他狠狠地一拳就打在她的脸上。权裔放声号哭起来,忙将手肘抱护着脸和头,悲痛地哭喊:“爸爸!爸爸!救命啊!爸爸……”
门边的几个孩子也围上来,大哥越是愤恨地对权裔拳打脚踢,并骂道:“你叫,叫,我让你叫,我打死你狗日的私生子,打死你……”
几个孩子,除老三呆站着,其他几个也仇恨地出脚踢权裔,用手拧她,嘴里咒骂着:“私生子……”权裔被他们群攻着,无处可逃,她哭着往柴堆里钻。
“老大!”屋里传来奶母气恼的喝喊声,“把灯吹了,睡觉!”
顿时,几个孩子拔腿朝屋里跑,老大恨恨地瞪着权裔,跨步去灶台一口气吹了灯。权裔猛然醒悟,忙松开抱头的手,她顾不得鼻孔还渗着血水,惊慌地爬起身往屋里跑去。
老大两步冲跳回屋,“砰”一声关了门。权裔惶恐地全身贴在门上哭喊,使劲敲着门,眼睛惧怕地瞟着黑暗中的家门:“大哥,开门,大哥,奶母,奶母,我错了,奶母,你给我开开门吧,奶母……”
“滚出去!”屋里传来奶母凶恶的声音,“你要跑就跑吧,外面到处都是鬼,正好等着抓你,吃你!”
“呜……呜……”突然,门后传来一阵飘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叫声。权裔吓得惊叫着,“啊——”奔回灶前,逃命似的将身子钻进柴堆。突然,她想到爸爸还没走远,她爬起来就拼了命地往外跑。
权裔追赶了很长一段路,在她筋疲力尽快要失去希望之时,借着皎洁的月光她远远地看见了父亲。她多么想立即冲上去投入父亲的怀抱,可是她不敢,她只好跟在父亲身后四五米远的地方,小心警惕地注视着他。她怕父亲听到她的脚步声,就悄悄脱了脚上的那双破布鞋,抱在怀里,风干的血渍在脸上形成恐怖的图案,她一头大汗地赤脚小跑,与父亲保持着距离。
“权——裔——”突然,后面远远地传来奶母的呼叫声。权裔惊慌地蹲下身,观望父亲。郑权陡然站定,一个猛转身,向后遥望。
权裔警惕地移身向路边轻轻滑下去,她站在排水沟里,身子紧贴路基保坎,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望去,漆黑中,霍地闪出一束火光,接着是奶母又一声喊叫“权——裔——”
郑权迎上奶母,着急万分地带着斥责的口气说:“权裔又怎么了?”
奶母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定,说:“跑了,不见了!”
郑权心急地责怪:“我不是交代过你看好她吗?”奶母惭愧地垂下头。
郑权白她一眼,口气缓和些说:“屋前屋后都找了没有?”
“找过了。”
“奶奶那呢?”
“还没去……”
郑权火冒三丈地喊:“你不去那边找,来追我有屁用啊!这黑灯瞎火的,她一个小孩能跑多远?你是安了心要害我天亮之前赶不回去受罚?看我罪上加罪你心里才舒服?”
这时,大哥忍无可忍地吼向父亲:“是她自己要跑的!”
郑权越发冒火地怒指他:“你给老子闭嘴,你别以为我没看见,就什么都不知道,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你,你的账老子以后才跟你算!”大哥敢怒不敢言地瞪他一眼。郑权忙将手中的火把,在奶母的火把上接燃,又气又恨地冲她斥道:“还不快找!”
郑权举着火把就要往回跑,一边喊叫:“权裔——”大哥恨恨地在他背后冲他空打了一拳。奶母责备地轻拍老大一把,拉着他跟着郑权跑去。
看着父亲着急紧张的样子,藏在路边保坎下的权裔,难过得再也忍不住喊道:“爸——爸——”郑权惊异地戛然止步,返身回望。奶母和老大同时一愣。
权裔急忙地爬上路基站着,悲伤地再次哭喊:“爸——爸——”
郑权不禁热泪盈眶,对冲过来的权裔,他心中不禁一股怨气涌动,愠怒地将火把照向她。权裔一副知错的模样低着头,怀里抱着一双破布鞋,赤脚呆站原地,头发蓬乱,脸上道道血痕。顿时间,郑权心痛如刀剜,他好想将她紧抱在怀里,但又不得不强装出一副凶恶的样子,他“啪”地掴权裔一个耳光,并骂道:“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权裔猝不及防,猛地惊了一下,诧异地望着父亲。
郑权继续骂着:“我白教你了,你才这么大点,就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这么辛苦养你还有什么用?你太让我失望了!”权裔任性地望着父亲,眼中泪水簌簌而落。此时,奶母和大哥也走了过来。
郑权强压着心酸,他唯恐眼中的泪水滚落,昂起头,硬着心肠说:“你走吧,爱跑哪儿跑哪儿去,我不管你了,我也不要你了!”郑权狠心地跨步就走,在权裔身后两步远,他回头望着他心爱的宝贝,悲痛的泪水滚滚而下。
权裔被父亲的耳光与怒骂惊呆了,她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奶母伸手来拉权裔。郑权泪如雨下,厉声说:“她要再敢跑,就把她捆起来,把腿给她砍了!”权裔如木偶般跟着奶母往回走。
郑权心碎地望着权裔的背影,他对奶母祈求地喊道:“二姐!”奶母惊诧地忙回转头,郑权双膝跪下,悲痛地、诚心诚意地对她作揖,磕了三个头,起身大步而去。
Chapter4
权裔穿着单薄的烂棉衣,一条破旧的开衩棉裤,两只不同的烂帮单布鞋,在土埂上边走边抹泪,奶母叫她必须割满一背篼的猪草才可以回家。她到了一大片牛皮菜田前,把背篼放在土埂上,身子瑟缩着跳到土里,用嘴对着满是冻疮的双手哈了两口热气,又使劲搓了搓,然后双手利索地扯了把牛皮菜放在路边,她再度哈气暖手,又一次伸手去菜田中。突然,她不小心碰到了冻疮,顿时,痛得直甩手,咬牙抱着手蹲了下去。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冻疮溢出的血,伤心地轻轻吹抚,冷得牙齿直打战。
“孩子!”身后传来一声心酸而又亲切的叫喊。权裔惊讶地回头,身子一斜,整个人一屁股坐在了土里。
廖秋莲忙扶起权裔,她看着孩子衣不裹体的一身褴褛,干裂红肿的小脸和双手,无比心痛、热泪盈眶地说:“郑权裔是吗?”
权裔愣愣地瑟缩着看她,不解地研究着她眼中的泪,答:“是。”
廖秋莲痛心地一抱拥她在怀,泪流不止地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宝贝,你受苦了。”廖秋莲忙脱下身上的棉衣,将权裔整个裹住。
权裔懵懂地看着她,受宠若惊,眼含泪水地说:“婆婆,你是谁?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我是姨婆,宝贝。我是你的亲人,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权裔诧异地:“家?!”
“是,家!你的家,妈妈的家,外公外婆的家,我的家,我们共同的家!”
权裔惊喜得泪流滚滚,说:“妈妈?外公?外婆?姨婆?我不是狗屎女,不是讨口子?”
“不是,你是我们家失落的宝贝!”
权裔伤心地哭泣:“你要我吗?”
廖秋莲悲痛地抱起她:“我要!永永远远都要!”
权裔被这个称做姨婆的人抱在怀里的时候,她感到好亲切、好温暖。可是突然间她被奶母凶神恶煞地跑来一把将她从姨婆怀里抢了过去,权裔好像美梦初醒,吓得惊恐万状,小便失禁,她放声号啕大哭,无力挣扎,她竭力回头呼喊:“姨婆!”
“啪”,奶母愤恨地用力掴权裔一巴掌,骂道:“叫,你再叫我丢你到河里去!”
“不回去,我就是不回去!”权裔张皇地哭闹,另一只手想掰开奶母的钳制,说,“你放开我,姨婆,爸爸,救命啦……”
“啪啪啪”,奶母发疯般连连扇权裔耳光,吼道:“你还有脸号!你这个祸害、杂种,你要害得老子一家鸡犬不宁,你怎么不死!”
“奶母!”权裔无可奈何地跟奶母奔跑,求饶地哭说,“奶母,放开我,奶母——啊……”权裔跟不了奶母的脚步,整个身子摔到地上。怒气冲天的奶母不依不饶地径直拖着她往渡口奔。码头上等渡和做生意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权裔拼命地想爬起来,想挣扎,一边抓扯着路边的菜茎、花木,手被刺出了血。
廖秋莲迈开步子追了上来,泪流满面地哭喊:“权裔,权裔,可怜的孩子,你放下她,孩子没有罪,你也有儿有女,你这是作孽!”
权裔哭着望向姨婆急忙伸手,大声地叫道:“姨婆,快救我。”奶母置若罔闻地将权裔拖下石梯,直向渡口拖去。
“别怕,孩子!你停下,伤着孩子了,停住手,我求求你了,权裔才五岁,她经不起这般折腾,你放过她吧,放她一条生路……”
“哦——”此时众人吆喝起来。姨婆飞奔过来。奶母一把将权裔用力拖甩向身后。姨婆扑向她与她抓扯。权裔咬奶母一口,奶母疼得松开手,权裔拔腿奔向姨婆。姨婆抱起权裔就跑。
奶母恼羞成怒地追上去,扳过姨婆的手夹住权裔上身往回拉。姨婆慌忙死死抱住权裔的腿,两人你来我往地拖扯权裔不放。权裔吓得大声号哭,双手乱抓。
“哦——”吆喝声愈来愈大,有人在吼,“拖死人啦!”此刻,一直就近旁观的几人出手帮起了姨婆,在众人的帮助下权裔这才来到了姨婆身边,自此过着被关爱呵护的日子。
权裔叹着气,想着自己的砚彧,她又想起了主任的劝说:“权裔,我不知道还能说你些什么?你冰雪聪明,待人宽厚仁慈,但有的事情你又着实固执得很。唉,一个人别太贪心,佛家有言,说‘舍得!’有‘舍’才有‘得’,该舍什么,该留什么,你自己掂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