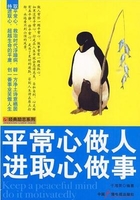刚开始,所有的日子对于玛丽来说都一模一样。每天早晨在挂满绣帷的房间里醒来后,就看见玛莎跪在壁炉前生火;每天早晨她都在毫无乐趣的儿童室里吃早点;每天吃过早点之后她都看着窗外巨大的荒野,它辽阔无垠、似乎一直延伸到天边;每次看一阵子之后她就会想起来,如果她不出去的话,就只好待在屋子里无所事事——所以她就出门了。她不知道这是她的最佳选择,她也不知道:当她沿着小路和大道快速行走甚至奔跑时,她的血液流速会加快;当她与荒野吹来的风搏斗时,她会变得更强壮。她奔跑只是为了取暖,她讨厌咆哮着吹在她脸上的风。那风像是一个看不见的巨人,阻挡她前进。不过,大口呼吸吹拂过欧石楠花的新鲜空气,让她的肺里充满对她瘦弱的身体有益的东西,让她的双颊红晕,让她无神的眼睛明亮起来。对于这些,她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
不过,在屋外游荡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早晨,她醒来后有了饥饿的感觉。她坐在早餐桌旁时,没有像往常那样厌恶地看着粥,把它推到一边,而是拿起勺子喝啊、喝啊,一直把它全部喝掉。
“你今儿早晨觉得粥还不错,对吧?”玛莎说。
“今天的粥味道很好。”玛丽说,她自己都有一点吃惊。
“是荒原上的空气让你有了胃口。”玛莎说,“你有胃口也有饭吃,多幸运啊。我家里有十二个小家伙,他们很有胃口却没东西往肚子里面装。你接着去外面玩,很快就会长些肉,脸色也不会这么黄了。”
“我不玩,”玛丽说,“我没什么可玩的。”
“没什么可玩!”玛莎大叫起来,“我家的小家伙们连棍子和石头都可以玩。他们就那么跑来跑去,大声叫喊,四处玩耍。”
玛丽没有大声叫喊,不过她也会四处看看。没别的事可做啊。她在园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又在小路上闲逛。有时候她去找本?威斯特夫,虽然见过他几次,可他要不就在干活看都不看她一眼,要不就是太古板。有一次她正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拿起铁锹就走开,好像故意似的。
有一个地方她去的次数最多,那就是有围墙的园子外面那长长的走道。走道的两侧都是光秃秃的花圃,旁边的墙上长满厚厚的常春藤。有一段墙上,墨绿的叶子比其他地方的更茂密,看起来好像被遗忘了很久。其他地方墙上的叶子都被修剪过,看起来很整齐,但是靠走道尽头的这段墙上的叶子根本就没人修剪过。
跟本·威斯特夫说过话后,过了几天,玛丽就注意到这个情况,她在心里琢磨着为什么。她刚刚停下脚步、抬头看风中摇摆的一枝长长的常春藤,就瞥见一丝红色,听见一阵嘹亮的鸣叫声。啊,就在那儿,就在墙头,站着本?威斯特夫的红腹知更鸟,它正歪着小脑袋看她呢。
“哦!”她叫道,“是你呀——是你吗?”她跟它说话,就像它一定能听懂、能回答她似的。对此,它一点儿也不感觉奇怪。
它确实回答了。它沿着墙边跳边叫,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像是想告诉她所有的事情。玛丽小姐好像也能听懂它的意思,虽然它说的不是人类的语言。它好像是在说:“早上好!风刮得舒服吧?太阳晒着暖和吧?一切都不错吧?咱们一起唱唱跳跳吧。来吧!来吧!”
玛丽大笑起来。它沿着墙往前跳一段、飞一段,她跟着它跑。可怜的、面黄肌瘦的、难看的玛丽——此刻她看起来真的可以算是漂亮。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她大声叫道,沿着走道一路小跑。她吱吱地学鸟叫,还想要吹口哨,只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吹。不过知更鸟看起来已经非常满意了,它朝她叫、朝她吹口哨。最后它张开翅膀,直冲向一棵大树的树顶,站在那儿大声歌唱。
这让玛丽想起第一次看见它的情景。那时它就站在树顶上,而她站在果园里。现在,她在果园的另一侧,站在一堵墙外的走道上——这墙要低得多——而墙里面还是那棵树。
“它在没人能进去的那个花园里。”她自言自语,“这就是没有门的那个花园。它住在那儿。我真希望自己能去看看那儿是什么样子。”
她沿着走道往回跑,走进她第一天早晨穿过的那扇门,接着穿过另一扇门,然后来到果园。她站在那儿抬头看,果然看见了墙另一边的树,还有树上的知更鸟。它刚唱完歌,正在用嘴巴整理自己的羽毛。
“这就是那个花园。”她说,“我敢保证这一定是。”
她沿着果园的墙转了一圈,仔细观察这道墙,但结果和以前一样——这墙没有门。然后她又穿过菜园,跑到被常春藤覆盖的墙外的走道,从这头走到那头,又观察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门。
“真是太奇怪了。”她说,“本·威斯特夫说这儿没有门,还真的没门。可十年前这儿一定有门,因为克瑞文先生把钥匙埋了起来。”
这让她有事情可琢磨,她开始感觉非常有趣,不觉得来到密塞威尔庄园有多么难过了。在印度她总是觉得热,无精打采的,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正是荒原上的风吹散了她小脑袋里乱糟糟的东西,让她稍微清醒了一点儿。
她几乎一整天都耗在外面。当她坐在餐桌旁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她觉得又饿又困,还挺舒服。玛莎闲聊的时候她也不觉得烦。她甚至觉得自己喜欢听玛莎说话,最后她认为自己应该问玛莎一个问题。她吃完晚饭后坐在火炉前的地毯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克瑞文先生为什么恨那个花园?”她问。
她让玛莎留下来陪她,玛莎一点儿也不反对。玛莎很年轻,习惯于住在挤满弟弟妹妹的农舍里。她觉得待在楼下的用人大厅很无聊。那些随从和上等女仆总是取笑她的约克郡口音,认为她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他们只顾自己坐在一起窃窃私语。玛莎喜欢说话。这个以前住在印度、被“黑人”照顾的陌生娃娃对她来说很新奇,足以吸引她。
她没等别人叫就自己坐到地毯上。
“你还在想那个花园?”她说,“我就知道你会想的。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这样。”
“他为什么恨它?”玛丽坚持问。
玛莎把腿蜷起来,坐得更舒服一点儿。
“听听外面呜央呜央的风,”她说,“今晚要是去荒原上的话,肯定站都站不稳。”
玛丽不知道“呜央”是什么意思,她仔细听了听,就明白了。那一定是说那空洞的、让人战栗的咆哮声。它绕着房子一圈圈地狂奔,仿佛一个隐形的巨人在击打着墙和窗户,想闯进来。但是人们知道它进不来。这让屋里坐在红红的炭火边的人觉得非常安全又温暖。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恨它?”她听了风声之后,仍然问。她想看看玛莎到底知道不知道。
玛莎只好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倒了出来。
“当心哦,”她说,“迈德洛克太太吩咐不让说的。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都是不能说的。这是克瑞文先生的命令。他说他的麻烦不关仆人的事。要不是那个花园,他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那是克瑞文太太的花园。他们刚一结婚她就修建了那个花园,她非常爱它。他们常常亲自去照料那些花儿,根本不让园丁进去。他们常常把自己锁在里面,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里面读书、聊天。她有点像小女孩儿似的。花园里有一棵古老的树。这棵树的一根树枝弯着,像是一个座椅一样。她让玫瑰花开满树枝,自己常常坐在上面。可有一天她坐在上面的时候,树枝断了,她掉到地上,伤得很重,第二天就死了。医生们本以为他也会发疯死掉。这就是他为什么恨那个花园的原因。从那以后就再没人进去过,他也不让任何人谈起它。”
玛丽再也没有问问题。她看着红红的炉火,听着屋外“呜央”的风。它好像“呜央”得更厉害了。
那一刻在她身上发生着一件很好的事情。实际上,自从她来到密塞威特庄园之后,她身上已经发生了四件好事情。她感觉自己好像能理解一只知更鸟而且它也能理解她;她在风中飞跑直到血液变暖;她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健康的饥饿;她知道同情别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正在慢慢进步。
可她在听风的同时,也听见了另外的声音。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因为一开始她几乎没法把那声音和风声区别开来。那声音很奇怪——像是小孩子在哭。有时候风声听起来也像小孩哭,可这一次玛丽小姐十分肯定这个声音就在房子里面,不是从外面传来的。它是在很远的地方,但就在房子里。她转过身去看着玛莎。
“你听见有人哭了吗?”她说。
玛莎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复杂。
“没有啊,”她说,“是风。有时候风声听起来就像是人在荒原上迷了路放声大哭一样。风有各种声音。”
“可是你听。”玛丽说,“这声音就在房子里——在那些长长的走廊那头。”
就在那时,楼下一定是有一扇门打开了,一股强劲的风吹进走廊,她们这个房间的门一下子被吹开了。她们同时跳了起来。灯被吹灭,哭声从走廊远处传来,能听得更清楚了。
“听!”玛丽说,“我跟你说过!是有人在哭——不是大人的声音。”
玛莎跑过去关上门并把它锁住,但在这之前她们都听见走廊远处有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然后一切便安静下来,因为连风也有一会儿没有“呜央”。
“是风声。”玛莎固执地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小贝蒂·巴特沃斯,洗衣女用。她整天牙疼。”
可她的态度中有些别扭、不安的感觉。玛丽紧紧地盯着她,不相信她说的是真话。